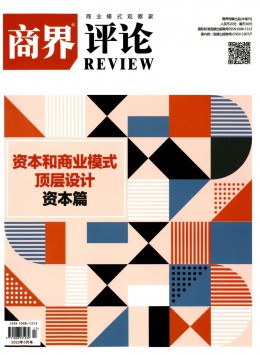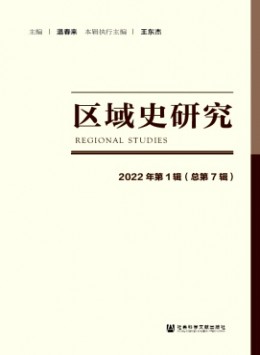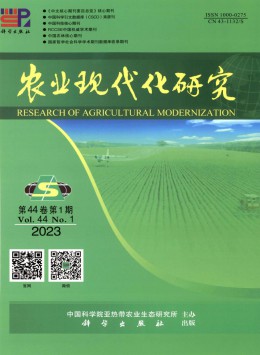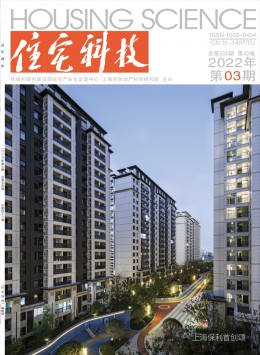微觀經濟分析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微觀經濟分析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1、經濟指標分析對比:經濟指標是反映經濟活動結果的一系列數據和比例關系。
2、計量經濟模型:它是表示經濟變量及其主要影響因素之間的函授關系。
3、概率預測:它實質上是根據過去和現在來推測未來,廣泛搜集經濟領域的歷史和現時的資料是開展經濟預測的基本條件,善于處理和運用資料又是概率預測取得效果的必要手段。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關鍵詞:危機管理;情境模擬;應用
一、情境模擬教學法的內涵及理論基礎
情景模擬教學法是一種仿真訓練方法,它通過創設教學內容所需要的接近實際工作或生活的場景,讓學生在這種場景中分別擔任不同角色,由教師在一旁進行指導、分析,并作出最后總結。作為一種虛擬實踐性教學方法,情境模擬法認為人的主觀心態、努力程度以及問題解決的方式會受制于不同的情境作用,因此,讓組織者與角色參與者對環境保持動態的適應,對于切實改善學習效果、提高實踐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才選拔和課堂教學中廣泛應用的情境模擬法, 是在前人雄厚的理論基礎上誕生的。認識論、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情境認知理論為情境模擬教學法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成果。
認識論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前提出發,認為認識的內容來源于客觀世界,認識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因此在教學中要遵循認識反映論的原理,根據客觀存在對學生主觀認識的作用進行情境模擬教學。通過對事件發生與發展的情景、環境、過程的模擬或虛擬再現,讓學生身臨其境地扮演某種角色或進入某種心理狀態,并和其中的人或事產生互動,以加深感受、深化認知。而建構主義作為一種學習理論則主要是針對傳統教育的弊端提出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更加注重對人的尊重與關懷,對人價值的再發現,強調學習者學習知識時主體認識特點的作用,它認為學生的學習不僅是對新知識的理解,而且是對新知識的分析、檢驗和批判。情境模擬應用到教育領域中正是依托建構主義理論實現教學目標設置。①情境認知理論是與建構主義大約同時出現的又一個重要的研究取向。它認為,實踐不是獨立于學習的。而意義也不是與實踐和情境脈絡相分離的,意義正是在實踐和情境脈絡中加以協商的。知識是個體與環境作用過程中建構的一種交互狀態,是一種人類協調一系列行為,去適應動態變化發展的環境的能力。知與行是交互的,知識是情境化的,通過活動不斷向前發展的,所以參與實踐就會促進學習和理解。②這些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使我們認識到情境在學生專業知識學習和實踐能力培養中的作用,從而啟示我們要明確學習者的主體地位,學習內容的設計要與具體實踐相關聯,通過虛擬人類具體生活實踐的方式來組織教學,并將知識的獲得與學習者的發展、身份建構等整合在一起。
二、情景模擬教學法在危機管理課程中的作用
危機管理是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我國步入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口、資源、環境、公平等社會矛盾的瓶頸約束日益嚴重,并不時引發出各種公共危機,如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1年“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2012年“毒膠囊”事件等。這些公共危機的爆發對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也對政府應急體系的構建和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的應急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戰。
然而,構建全面整合的應急體系、提升危機管理績效,既離不開理論界專家學者的深入探討,更離不開全社會范圍內應急協防知識的普及和對日后從事公共管理的人才的危機管理能力的培養。因此,危機管理課程應以實踐為導向,在重點介紹公共危機管理流程、危機決策模式、危機溝通機制、危機管理主體行為的基礎上,分類闡述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與控制等內容,并結合國外公共危機應急機制的運行狀況和經驗教訓,探討建立與完善我國危機管理體制的制度措施與政策選擇。
為了克服傳統的教學模式“重知輕智”、“重灌輕趣”、“重教輕學”的弊端,使學生重點掌握危機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不同類型危機事件的處理方法,指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危機觀,培養學生的危機管理能力,采取情境模擬教學法對《危機管理》這樣一門實踐性和應用性都非常強的課程,有明顯的優勢:
1、滿足學生的情感需求
現代教學論把學生的發展看作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情感需要為核心的一系列非智力因素,影響并制約著學生的學習與發展。③情境模擬訓練著眼于學生求知活動中的情緒體驗,滿足學生求知過程中的情感需求,強化學生的感性體驗在認知中的作用。通過強烈的現場參與感極大地觸發和增強了學生危機管理理論思維的興奮點,并縮短知行距離、促使知行轉化,使學生在學習危機管理理論知識的同時獲得成功的滿足和愉悅的情緒體驗。
2、激發學生的積極性
大量的研究證明,只有當學生對正在學習的東西感興趣,覺得富有挑戰性并積極地參與其中時,學生的學習才真正有效。情景模擬教學法通過創設危機情境,進而讓學生切實感知危機的突發性、危害性、不確定性。并在約束條件下,以管理者的身份做出危機決策、進行危機溝通、形成應急聯動。這種教學方法下學生所扮演的是一個積極參與的角色,在教師的引導下不僅能夠極大地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更能夠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3、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傳統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比較重理論知識的傳授,而忽視學生對專業知識的理解和運用。因而“高分低能”、學生實踐能力弱化的現象十分突出。通過采用情境模擬教學法,既拓寬了授課教師的教學思路,也為學生打造了一個應用知識、鍛煉技能的平臺。在感知危機情境的基礎上,學生能有意識地將所學危機管理論運用于對典型公共危機事件的分析中,從而更好地理解和運用相關理論知識,提高實踐能力。
三、情境模擬教學法在危機管理課程中的設計與應用
為了確保情境模擬教學法在危機管理課程中的順利實施,前提是創設危機情境。危機情境的創設是以危機的生命運動周期為基礎的。危機的發生和發展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為了有效管理危機,學者們全面分析了危機發展的基本態勢,并構建了危機運動的不同模型。其中,芬克(Fink)的四階段模型、米特羅夫(Mitroff)的五階段模型和基本的三階段模型最為廣泛接受。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危機的發生與發展簡單劃分為三階段:潛伏期、爆發期、恢復期。相應地,危機管理的步驟可以濃縮為預警、應對、善后三步曲。因此,在危機管理課程中,教師可以圍繞危機管理的流程創設不同的危機情境,讓學生分別扮演不同情境中的決策者、溝通者和執行者,讓他們體會危機管理與常態管理的區別,通過多次模擬對比,使學生直接面對在約束條件下不同管理行為的結果和績效。另外,學習該課程的學生畢業后可能成為危機管理的主體,但同時他們也極有可能成為公共危機的利益相關者。因此,有必要讓學生模擬公共危機的受眾,檢驗學生應對不同危機事件的自救和協防能力。
在具體實施中,情境模擬教學包括以下階段:
1、教學準備階段
在準備階段,教師首先要選擇典型危機管理問題,如“毒奶粉”事件、“杭州飆車案”、“汶川大地震”等。并根據所確定主題,細化方案的設計,決定采取分組討論、角色扮演、辯論等方式來進行情境模擬。對于每一主題進行情境模擬教學所需的條件、設備等,教學方案中應予以明確。其次,教師應該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來策劃和準備相應場景,在物質條件配備的前提下,把應急決策、應急演練等情景,在課堂或者實驗室中模擬出來,讓同學們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通過仿真的場景來幫助學生進行角色模擬。最后,教師要根據主題設計角色與分配角色。危機情景模擬的角色主要包括兩類:危機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教師可以安排不同的學生扮演政府應急管理人員、非政府組織人員、媒體人員、危機受害者,讓參與者做出符合角色特點的危機管理行為。
2、教學實施階段
在實施階段,學生要在課前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根據情景模擬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危機事件面臨的管理問題做出現狀分析和判斷,并根據所學危機管理理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實施方法。然后,學生根據事先安排的角色身臨其境地按危機管理職責、危機管理流程等要求進行演練和操作。模擬結束后,由學生自由發言,就情境模擬中各危機管理參與者和危機利益相關者的行為適當性、科學性發表自己的見解。也可請其他學生進行同一危機情境的再次模擬,通過相互比照,尋找問題沖突,進行深層次追問,從而使角色之間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夠更為科學。最后,教師要在學生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進行客觀、科學的總結和評價。對于學生的角色扮演情況,教師要圍繞主題對他們的語言表達、應變和解決問題等相關表現進行整體評價,也可由教師進行危機情境中相應角色的示范模擬,從而讓學生找到不足,并啟迪他們學以致用的創新意識。
3、教學總結階段
在總結階段,教師要充分聽取學生對情景模擬教學法實施效果的建議和意見,不斷修正情境模擬實施方案,創新教學方法。同時,將實施效果較好的典型實例進行總結和歸納,作為開展情境模擬教學的經典實例。學生也要在情境模擬教學結束后,總結經驗和教訓,掌握角色扮演的技巧和要求,以提高教學實效性。相關授課教師也可以在教學研討活動中進行情景模擬教學法專題研究,針對情境模擬教學法在危機管理課程實施中的困境和難點進行探討,以優化教學過程,提高教學能力。
四、危機管理課程情境模擬教學實例
危機管理課程的教學內容包括三大版塊:危機及公共危機管理基本理論、公共危機管理實務、公共危機管理的變革與發展。其中,公共危機管理實務的教學內容是根據轉型期我國公共危機的特點、性質、機理來分類設計的,包括自然災害危機管理、事故災難危機管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社會安全事件危機管理。在社會安全事件管理這一章中,選擇的情境模擬實例是天津艾滋患者“扎針”事件。在這一案例中,存在多個危機管理參與者,包括市長、警察、醫生、衛生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媒體人員、專家等。各參與者在危機管理中的職責、權限、作用是不同的。為了讓學生深入把握危機管理的組織體系,明確各主體的角色定位和行為方式,尤其是厘清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在危機管理中的不同職能,可以讓學生在教師創設的天津艾滋患者“扎針”事件的情境中,進行角色模擬,身臨其境地進行應急決策和應急溝通,以有效處置天津艾滋患者“扎針”事件。具體實施步驟如下:
第一步:設計天津艾滋患者“扎針”事件的情境模擬教學方案,確定情境模擬地點,參與人選、創設應急決策和應急溝通情境。
第二步:學生在熟悉案例資料的基礎上,根據所扮演的角色,收集相關材料,結合所學危機管理理論,分析應急決策和應急溝通的方法、程序,尤其是要把握不同主體在危機管理中的職能定位和行為方式。
第三步: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進行情境模擬,由其他學生發言,就情境模擬中各參與者的行為進行分析。也可請其他學生進行應急決策和應急溝通的再次模擬,通過相互比照,尋找修正各主體危機管理行為的總體思路和可操作建議。
第四步:教師對各位同學的在天津艾滋患者“扎針”事件情境中的角色模擬情況進行評價。并對應急決策和應急溝通的基本知識點及其應用進行總結和歸納,將學生的感性體驗上升為理性認識。
從實施效果來看,在危機管理課程中應用情景模擬教學法,強化了學生對危機管理理論的認知,提高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了思辨能力。當然,情境模擬教學只是一種嘗試,它還存在情境設計單一、教師組織引導能力不足的等問題,有待于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檢驗、修正、提高和完善。
[注釋]
①齊磊.論情境模擬教育[J].學理論,2010(10),221頁.
②程守梅,賀彥鳳,劉云波.論情境模擬教學法的理論依據[J].成人教育,2011(7),44頁.
③吳兆雪.創新思維培養的理論與實踐——理論教學新視野[M]. 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4.5
[參考文獻]
[1]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M].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李程偉. 公共危機管理:理論與實踐探索[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2.
[4]戴子剛. 論情景模擬教學[J]. 中國校外教育, 2008(8).
第3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關鍵詞] 神經外科;重癥醫學;下呼吸道感染;危險因素
[中圖分類號] R181.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8-0034-03
顱腦外傷、腦出血等患者病情危重需要進行特殊的重癥監護救治,患者生命體征的維持和監護需要實施多種醫療儀器進行無創或有創的治療操作,患者意識模糊甚至處于昏迷的狀態長時間臥床,且機體處于強烈的應激狀態,免疫功能紊亂,下呼吸道是重癥醫學科最常見的醫院感染部位,嚴重的肺部感染極易誘發患者呼吸障礙、全身感染、加重基礎疾病和病情,結局不良[1]。本研究對我院重癥醫學科2009年2月~2013年3月收治的743例神經外科危重癥患者進行分析,探討影響患者并發下呼吸道感染和預后的危險因素,為臨床降低感染發生率,改善患者預后提供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09年2月~2013年3月在我院重癥醫學科住院的神經外科危重癥患者743例,男408例,女335例,年齡18~75歲,平均(63.29±10.83)歲,其中顱腦外傷382例,腦出血179例,顱內腫瘤術后82例,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lasgow Coma Scale,GCS)3~8分,平均(5.93±1.29)分,合并心臟病179例、高血壓239例、高血脂159例、糖尿病209例、慢性肺部疾病126例,急診手術307例,擇期手術437例。
1.2調查方法
研究重癥醫學科住院期間下呼吸道感染的發生率及預后,分析相關高危因素與下呼吸道感染發生及預后的關系,收集患者一般資料(年齡、性別、病情、合并癥、GCS評分、營養狀況[2])、治療資料(手術類型、氣管切開/氣管插管/吸痰等侵入性操作、抗菌藥物使用種類、激素使用、呼吸機使用)、住院時間、死亡等。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根據預后分為死亡組和對照組。
1.3統計學處理
數據應用SPSS 16.0軟件包進行相應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方程。P
2 結果
2.1下呼吸道感染發生情況及預后
73例發生下呼吸道感染,感染發生率為9.83%,經治療處理好轉55例為對照組,死亡18例為死亡組。
2.2下呼吸道感染及死亡單因素分析
年齡、心臟病、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營養狀況、侵入性操作、抗菌藥物種類、呼吸機使用、住院時間與患者發生下呼吸道感染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下呼吸道感染及死亡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侵入性操作、抗菌藥物種類是神經外科危重癥患者并發下呼吸道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P
3討論
重癥醫學科收治的交通意外、工傷事故、腦血管意外、顱腦腫瘤等導致的顱腦創傷、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患者往往病情危重,生命體征不穩定,機體狀況極差,各系統功能出現紊亂或障礙,結局兇險,同時發生醫院感染的風險極高,其中下呼吸道感染占比最大,患者并發下呼吸道感染后,加劇身體機能障礙,誘發基礎疾病加重,引起多種嚴重并發癥,直接危及患者生命,給危重癥患者救治造成嚴重影響[3-5]。因而,防范下呼吸道感染是重癥醫學科醫院感染控制的重點。本調查結果顯示,743例神經外科重癥患者73例發生下呼吸道感染,感染發生率為9.83%,與國內其他研究結果相似,其中有18例死亡,說明神經外科危重癥并發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預后差,死亡率高。
本研究中老年患者占比例較高,并發下呼吸道感染率也顯著高于較年輕患者,且死亡組和對照組比較也有顯著性差異,但多因素分析則均不是獨立危險因素,說明單純的高齡并不決定患者并發下呼吸道感染和死亡的風險,而可能與高齡合并多種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更大有關。而合并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在多因素分析中均為并發下呼吸道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對醫院感染的風險被普遍認知[6],而既往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下呼吸道基礎疾病導致呼吸道屏障功能低下,對病原菌侵襲抵御能力低,病原菌感染風險極高,并發下呼吸道感染后,原有基礎疾病可能誘發加重,從而使病情進展更為迅速,癥狀表現更嚴重[7]。心臟病、高血壓等也是老年患者常見合并癥,但在導致下呼吸道感染發生方面促進作用并不顯著,但心臟病在多因素分析結果中為患者發生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心臟基礎疾病被肺部炎癥誘發加重,形成多系統疾病的疊加,導致患者死亡[8]。營養狀況是重癥醫學科需要關注的重要狀態之一,尤其是神經外科危重患者往往處于昏迷狀態,腸內營養難以補充,腸外營養達標也有難度,患者易發生營養不良,進一步降低機體抵抗力,發生感染[9],分析結果顯示,營養狀態與并發下呼吸道感染有關,但不是獨立危險因素,而卻對患者死亡起到了獨立的影響作用,表明保證患者營養達標是危重癥患者救治關鍵,不僅可降低感染發生,還有助于患者機體功能恢復,改善預后。侵入性操作和多種抗菌藥物應用是并發下呼吸道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結果與以往研究一致[10]。呼吸機的使用和長時間住院治療對并發下呼吸道感染及預后的影響與以往研究結果不同,可能是本研究以神經外科危重癥患者為研究對象,多數患者都需要實施人工機械通氣,且住院時間都較長有關。
臨床護理則可依據并發下呼吸道感染的相關因素實施有針對性的干預,重點人群為高齡、基礎疾病多的患者;護理干預的方式則以患者具備的危險因素對癥處理,保證患者營養達標,結合早期腸內營養,恢復患者胃腸道功能,促進身體機能逐步恢復,控制基礎疾病,做好吸痰、機械通氣調整,嚴格遵守無菌原則,保持患者皮膚、黏膜、呼吸道、導管等清潔,達到規避危險因素,降低神經外科危重癥患者并發下呼吸道感染風險,改善預后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Navoa-Ng JA,Berba R,Galapia A,et al. Device-associated infections rates in adult,pediatric,and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of hospitals in the Philippines:Inter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Consortium(INICC)findings[J].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2011,39(7):548-554.
[2] 宿英英,黃旭升,彭斌. 神經系統疾病腸內營養支持操作規范共識[J].中華神經科雜志,2009,42(11):788-791.
[3] Lili Tao,Bijie Hu,Victor D,et al. Device-associated infection rates in 398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Shanghai,China:Inter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Consortium(INICC) finding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11,15(11):774-780.
[4] 沈雅艦,胡銀燕,劉俏俊. 重型顱腦損傷氣管切開術后呼吸道感染的預防及護理[J]. 中國臨床保健雜志,2013,16(1):89-90.
[5] 耳思遠,李卓杰. 早期氣管切開對重型顱腦損傷并發肺部感染的防治作用[J]. 醫學綜述,2013,19(2):377-378.
[6] 郭魁,趙云龍,董全勇. 神經外科重癥昏迷病人肺部感染的防治[J]. 中國臨床神經外科雜志,2013,(1):42-44.
[7] 王鵬,王春生,齊震. 開顱術后顱內感染的危險因素分析[J]. 中國醫藥導刊,2013,(2):242-243.
[8] 溫雅婷,沙麗艷,賈巖竹. 開顱術后發生醫院感染的相關危險因素分析[J]. 中華神經外科疾病研究雜志,2013,12(2):185-186.
[9] Helder OK,Brug J,Looman CW. The impact of an education program on hand hygiene compliance and nosocomial infection incidence in an urba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n intervention study with before and after comparis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10,47(10):1245-1252.
第4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關鍵詞】 微血管減壓術; 發熱; 顱內感染; 原因
Th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at the Patients of Postoperative Fever that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of the Trigeminal Nerve/SUN Yan-chun,LI Ping,ZHAO Chang-di,et al.//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6,13(20):135-139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of postoperative fever of the patients that was implemented of trigeminal neuralgia,hemifacial spasm and 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an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Method:All of cases in our department nearly five years that the trigeminal neuralgia were collected,hemifacial spasm and glossopharyngeal neuralgia 841 patients.All of th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routine use of antibiotics),group B (temporary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group),the heat rate,infection rate were analyzed,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ever,explore treatment strategies.Result: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eat rate(P0.05).Conclusion:There is no obvious meaning that excessive use of antibiot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tra-cranial infection.This is essential for the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ever positive lumbar punctur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laboratory tests.We recommend that early and aggressive use of antibiotics to intervene if you highly suspected intra-cranial infection.
【Key words】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Fever; Intracranial infection; Causes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Ji’ning,Ji’ning 272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20.037
原發性三叉神經痛、面肌痙攣、舌咽神經痛為常見病、多發病,由于其疼痛劇烈,故又被稱為“天下第一痛”[1],嚴重威脅著人類的身心健康。對于其治療,多采用乙狀竇后入路微血管減壓術(MVD)[2],多數患者可取得良好的手術效果;但術后部分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發熱,嚴重者出現可怕的顱內感染,仍需進一步討論;對此,筆者進一步綜合分析其發熱原因,針對不同的發熱原因,探討其防治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1月-2015年12月本科實施MVD術(或三叉神經感覺根部分切斷術)的三叉神經痛、面肌痙攣、舌咽神經痛患者共計841例,其中三叉神經痛患者511例,面肌痙攣患者326例,舌咽神經痛患者4例,其中男396例,女445例,年齡23~79歲,平均57.3歲。將所有患者分為兩組:其中2010年1月-2012年7月的患者為A組(常規應用抗菌藥物組)425例,男201例,女224例,平均年齡(56.9±3.27)歲;2012年8月-2014年10月的患者為B組(臨時應用抗菌藥物組)416例,男195例,女221例,平均年齡(55.1±2.49)歲。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實施MVD術(剔除復發后實施二次手術的病例),均置入滌綸棉減壓(剔除僅實施感覺根部分切斷術的病例),從打開硬膜至硬膜縫合完成,均不超過1 h;另外,對于開放乳突氣房的患者,均采用骨蠟嚴格封閉,隨后應用雙氧水、生理鹽水反復沖洗三遍,以免打開硬膜后造成顱內感染;污染的器械全部更換。A組在常規切皮前30 min靜滴抗菌藥物基礎上,術后常規使用同一抗菌藥物靜滴5 d;B組常規切皮前30 min靜滴抗菌藥物,術后僅24 h之內臨時使用一次抗菌藥物。
1.3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 字2檢驗,以P
2 結果
A組425例患者中,共97例(22.82%)出現發熱癥狀;其中確診顱內感染病例22例(5.18%),其中細菌性腦膜炎20例、腦膿腫/硬膜下膿腫
2例;術后吸收熱64例;皮下積液4例;上呼吸道感染5例;肺部感染1例;泌尿系統感染1例。B組416例患者中,共132例(31.73%)出現發熱癥狀;其中確診顱內感染病例21例(5.05%),其中細菌性腦膜炎20例、腦膿腫/硬膜下膿腫
1例;術后吸收熱97例;皮下積液3例;上呼吸道感染7例;肺部感染2例;泌尿系統感染2例。兩組患者發熱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字2=8.4174,P0.05)。
3 討論
原發性三叉神經痛、面肌痙攣、舌咽神經痛的病因復雜,多數學者認為神經入腦干區域存在動脈血管壓迫,是其主要因素,因此,多數患者實施微血管減壓術有效。本科從80年代開始實施微血管減壓術(MVD),有著豐富的手術經驗,并且曾對MVD術后無效的原因曾予以分析[3-4],但在良好的手術效果之后,部分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術后發熱,甚至合并顱內感染,從而給患者帶來一定程度的痛苦及負擔。
筆者對841例實施MVD手術的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術后常規使用抗菌藥物靜滴5 d,與術后僅24 h之內臨時使用一次抗菌藥物組比較,顱內感染率無統計學差異(P>0.05),術后發熱率存在統計學差異(P
3.1 術后吸收熱 占據MVD術后發熱比例第1位,可分為早期吸收熱、晚期吸收熱兩類;發生時間分別為術后1~3 d、4~7 d;而對于術后晚期吸收熱的正確診斷,至關重要,因為該時間段與顱內感染所致發熱的時間段相重疊,與簡智恒等[5]所得結論基本相同;結合患者的臨床癥狀(如頭痛、頭暈、惡心等)、體征(如頸抵抗、意識障礙、新發的神經系統體征等)以及影像學資料,無法做出正確診斷;應結合外周血常規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計數、降鈣素原檢查,以及腰椎穿刺腦脊液壓力、常規、蛋白定量等檢查,綜合做出診斷;其中,腰椎穿刺腦脊液實驗室檢查是必不可少的項目;但如果患者意識狀態進行性下降,在腰穿之前首先行顱腦CT檢查是有必要的;患者術后一旦合并發熱,尤其對于術后第5天左右出現的發熱,無法排除顱內感染因素時,均應該勸導患者行腰椎穿刺檢查;根據腦脊液及外周血實驗室結果,在排除顱內感染之后,無需使用抗菌藥物,可多次腰穿釋放腦脊液,從而使得患者臨床癥狀(如發熱、頭痛、頸抵抗等)得以逐步緩解。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多采用每日一次腰椎穿刺,釋放腦脊液,同時觀察患者腦脊液性狀、顱內壓力、腦脊液白細胞數目等項目,指導患者臨床恢復及預后,一般每次釋放腦脊液不超過30 mL,腦脊液白細胞數目、多核細胞數目及腦脊液蛋白指標均進行性下降,從而初步估計預后良好。
3.2 顱內感染 術后顱內感染不太常見,但由于它可能對患者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對于術后顱內感染的早期診斷,至關重要;單純依靠患者的臨床癥狀、體征,難與術后晚期吸收熱相鑒別,應該結合外周血白細胞、中性粒細胞計數、顱腦CT或MR檢查,以及腰穿壓力、腦脊液實驗室檢查,必要時需要予以細菌學培養,從而盡早確診、盡早治療;值得一提的是,有時候腦脊液細菌學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有時候難以培養出陽性結果;此時,如果患者的各項臨床數據,無法排除顱內感染時,應該堅持寧左勿右的原則,早期應用抗菌藥物治療;多采用三代頭孢菌素或萬古霉素藥物,抗感染治療;由于顱內感染的危害較大,嚴重時可能危及患者生活,因此,必要時可兩種抗菌藥物聯合使用。
3.2.1 細菌性腦膜炎 如果患者的臨床癥狀、體征以及腰穿腦脊液檢查,均支持顱內感染的診斷,而顱腦CT或磁共振無異常改變,此時應確診為細菌性腦膜炎。對于可能的感染途徑,有助于選用抗菌藥物:呼吸道細菌(如肺炎雙球菌、流感嗜血桿菌、鏈球菌)可能通過腦脊液鼻漏或耳漏途徑感染;而葡萄球菌和革蘭氏陰性細菌,多見于腦脊液切口漏途徑感染。對于腦脊液漏的患者,是否應該預防性應用抗菌藥物,目前存在一定的爭議[6];由于一旦合并顱內感染,將給社會及患者家庭造成沉重的負擔,因此,多采用預防性應用抗菌藥物;在應用抗菌藥物的同時,積極的病因治療必不可少;如果存在腦脊液漏,經保守治療無效,應積極勸導家屬行修補手術。
3.2.2 腦膿腫/硬膜下膿腫 術后腦膿腫、硬膜下膿腫多發生于年齡較大、體質相對較差的患者;可有傷口感染的跡象;文獻[7-8]報道,腦膿腫或硬膜下膿腫的發生,多與革蘭氏陰性需氧菌或皮膚菌群為致病菌;由于腦膿腫、硬膜下膿腫可不與蛛網膜下腔相通,因此,腦脊液白細胞計數可能不會升高[9-10];此時,積極的影像學檢查必不可少。對于腦膿腫的治療方案大致相同:如果膿腫較小,采用有效抗菌藥物治療即可,多采用三代頭孢治療,必要時可聯合萬古霉素治療[11];如果膿腫較大、且局限,此時行腦在患者全身狀況允許的情況下,盡早行膿腫清除術比較適用,術中留取合適的標本行細菌學培養,術后采用有效抗菌藥物治療;待其培養標本回報后,根據結果再調整抗菌藥物。
3.3 皮下積液 術后皮下積液的發生,多是由于縫合技術原因所導致;馬玉召等[12]亦對皮下積液情況進行綜合分析;首先硬膜應該做到無漏水縫合,若術后發生皮下積液,可采用局部加壓包扎、腰椎置管降低顱內壓的治療方案[13],可降低腦脊液壓力、減少腦脊液漏出、促進瘢痕形成等,從而促進硬膜、肌肉粘連、愈合;而術中硬膜的嚴密縫合(必要時可取肌肉筋膜修補縫合),以及肌層的無張力、嚴密縫合,對于預防皮下積液的發生至關重要。另外,如果為了降低預防腦組織水腫而在圍手術期使用類固醇激素,則有可能對硬膜和蛛網膜的愈合產生不利影響[14]。另外,趙杰等[15]通過大量手術證實,對于全腦蛛網膜下腔包括的保護,亦可以有效地減少術后并發癥的出現,并縮短治療時間,減少患者痛苦。
3.4 術中乳突氣房開放的處理 一旦乳突氣房打開,均應采用骨蠟嚴格封閉,隨后應用雙氧水、生理鹽水反復沖洗三遍,以免打開硬膜后造成顱內感染;污染的器械全部更換;另外,由于手術時間因素對發生感染亦可能為重要因素,因此,從打開硬膜,到縫合硬膜完畢,均在1 h內完成,從而減少術野暴露時間,減少感染率。
3.5 上呼吸道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患者發生上呼吸道感染的時機,多在季節交替、氣溫驟變的情況下;患者經歷手術、全麻應激等因素,在全身抵抗力下降的情況下,呼吸道病毒趁機大肆繁殖,從而導致上感發生。患者除了存在發熱癥狀外,亦存在上呼吸道感染的表現,如流涕、咳嗽等癥狀;此時應積極針對性治療。
3.6 肺部感染 上感患者一般情況進一步變差,則有可能發展至肺部感染;該病例亦發生在年齡較大、體征相對較差的患者;對于肺部感染的患者,積極的痰培養、痰涂片,同時行藥敏試驗,從而指導臨床用藥;在藥敏試驗結果出來之前,可應用廣譜抗菌藥物,防治肺部感染;待藥敏結果回報后,根據藥敏結果,及時調整抗菌藥物。
3.7 泌尿系統感染 由于所有手術的患者,需要全身麻醉、術前留置尿管,從而增加了泌尿系統感染率;患者除了發熱外,還可存在尿頻、尿急、尿痛等膀胱刺激癥狀;因此,留置尿管前充分、仔細消毒,嚴格無菌操作,術后盡早拔出尿管,對降低泌尿系統感染率均有所幫助。一旦確診泌尿系統感染,均應盡早拔出尿管,并早期應用抗菌藥物,并囑患者多飲水、沖刷尿道,均對治療有幫助。
MVD術后潛在并發癥很多,而術后發熱的原因眾多,均應積極找尋發熱原因[16-17],無菌性腦膜炎亦是臨床應該注意的問題之一[18];首先盡早排除或確診顱內感染,從而進行相關治療。另外,有學者認為,常規生理鹽水+慶大霉素沖洗,對預防顱內感染有一定的幫助[19];而本科僅采用生理鹽水進行沖洗,對此,筆者下一步也將進行進一步試驗。楚燕飛等[20]亦大量分析了幕下開顱手術并發癥,重點分析了發熱的原因。一致認為,由于顱內感染一旦確診,將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因此,一旦高度懷疑顱內感染,建議堅持寧左勿右的原則,早期積極應用抗菌藥物進行干預,盡量避免出現嚴重后果。
參考文獻
[1] Bennetto L,Patel N K,Fuller G.Trigeminal neuralgia and its management[J].BMJ,2007,334(7586):201-205.
[2] Obermann M.Treatment options in trigeminal neuralgia[J].Ther Adv Neurol Disord,2010,3(2):107-115.
[3]王召平,楊梅,種衍軍.原發性三叉神經痛微血管減壓術后無效的臨床分析[J].中國醫學創新,2011,8(25):34-36.
[4]種衍軍,王召平,陳劍,等.三叉神經痛的顯微血管減壓手術治療[J].中國醫學創新,2010,7(23):12-14.
[5]簡智恒,張喜安,漆松濤,等.神經外科術后炎癥指標的變化及意義[J].中華神經醫學雜志,2013,12(4):415-418.
[6] Rajshekhar V,Chandy M J.Tuberculomas presenting as isolated intrinsic brain stem masses[J].British Journal of Neurosurgery,1997,11(2):127-133.
[7] Parney I F,Johnson E S,Allen P B.“Idiopathic” cranial hypertrophic pachymeningitis responsive to antituberculous therapy:case report [J].Neurosurgery,1997,41(4):965-971.
[8] Rajshekhar V,Chandy M J.Validation of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solitary cerebral cysticercus granuloma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seizures[J].Acta Neurologica Scandinavica,1997,96(2):76-81.
[9] Rajshekhar V,Haran R P,Prakash G S,et al. Differentiating solitary small cysticercus granulomas and tuberculoma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J].Journal of Neurosurgery Publishing Group,2009,78(3):402-407.
[10] Selvapandian S, Rajshekhar V, Chandy M J.Predictive value of computed tomography-based diagnosis of intracranial tuberculomas[J].Neurosurgery,1994,35(5):845-850.
[11] Gupta R K,Jena A,Singh A K,et al.Role of magnetic resonance (MR)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intracranial tuberculomas[J].Clin Radiol,1990,55(1):120-127.
[12]馬玉召,王延偉,孫興,等.微血管減壓術后腦脊液外滲皮下20例治療體會[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13,16(16):3.
[13] Young-Hoon K,Han J H,Chae-Yong K,et al.Closed-suction drainage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leakage following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 a 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study[J].Journal of Korean Neurosurgical Society,2013,54(2):112-117.
[14] Mahanta A,Kalra L,Maheshwari M C,et al.Brain-stem tuberculoma:an unusual presentation[J].J Neurol,1982,227(4):249-253.
[15]趙杰,劉志雄,劉勁芳,等.蛛網膜下腔保護在開顱手術中的應用:附156例手術體會[J].中南大學學報(醫學版),2010,35(10):1112-1114.
[16]陳登奎,莊進學,方宏洋,等.三叉神經微血管減壓術主要并發癥臨床分析[J].中國微侵襲神經外科雜志,2006,11(3):135-136.
[17]豐育功,姜元培,唐萬忠,等.面肌痙攣微血管減壓手術技巧及并發癥分析(附34例報告)[J].中國臨床神經外科雜志,2011,16(11):653-655.
[18]王錫溫,姜紹紅.顱內面神經顯微血管減壓術后并發無菌性腦膜炎一例[J].中華耳科學雜志,2014,12(3):429-430.
[19]常洪波,田增民,盧旺盛,等,后顱窩開顱手術應用不同沖洗液預防感染研究[J].中華神經外科疾病研究雜志,2014,13(1):47-50.
第5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與長江三角洲的發展明顯相反,英格蘭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長期上升趨勢,構成了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改變的基礎,而這的確是經典的由交換而獲利的斯密式增長。在中世紀時期,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趨勢嚴重限制了英格蘭所能養活的非農業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歐洲地區??雖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時期仍是如此。但隨著英國農業的轉變,相對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從而使得養活日益增多的轉入制造業、服務業等非農行業的勞動力成為可能。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早期,英國工業中最具活力的行業??生產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為著重出口導向型的產業,以適應橫貫歐洲的精英們(多為領主)對奢侈紡織品的需求。但在十七、十八世紀,由于人均農業產量使食品變得便宜并使英國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開支,出現了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大眾”制造品市場 (e.g., Thirsk, 1978; Jones, 1967, 1968; John, 1965; Eversley,1967; Wrigley,1985)。
制造業在長江三角洲的興起是通過小農家庭多元化,以紡、織來彌補維持生存的糧食生產中的短缺。與此相反,在英格蘭它是與谷物生產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及對家庭制造業更徹底的放棄相伴隨并受其促進。在同一現象的另一面,制造業在英格蘭典型的不是由農民著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賴于市場的商業性牧人或奶農作為副業、或是資本主義制造商利用中部適于耕種的地區相對較寬松的勞工市場來進行。與長江三角洲小農及他們中世紀的前輩不同,英國制造業者于是傾向于與直接占有生存資料的途徑相隔分開,因此依賴市場并受競爭的制約。結果,英格蘭農村的耕種工業單位被迫通過其生產活動之總和以追求利潤最大化,后果是制造業為應對市場需求與比較成本的增長與變化而擴展、變化,而不是如長江三角洲那樣是為了應對小農盡管回報率日益下降仍需生產棉布并將其售往市場以彌補其糧食短缺以確保生存。
最初,工業生產主要集中在英格蘭西部與東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約克郡,其成長與這些地區的養羊業與奶業密切相連。相應地它不見于(雖非完全)中部糧倉地區。但因為農業勞動的地區分工由新作物與技術引進帶來的比較優勢而倒轉,也即過去的牧區與墾區交換工業的地點也相應地發生轉移。工業生產現在與牲畜飼養和奶業一道移往中部與北部,而離開東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產日益專業化及對勞力使用與之相應的農業區(Jones, 1968)。
從十七世紀前期某一時間開始且持續到十八世紀中葉,農業生產力的增長與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相結合最終導致了谷物價格的相對下降,交換率向有利于工業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動,以及最終導致實際工資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與9; John, 1965)。消費者于是發現他們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漸減少,并因此能夠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開銷上。因此而發生的制造業需求的增長將其相對于農業產出的回報率提得更高,最初工業與牧業或奶業相結合的地區不斷放棄農業而完全專注于制造業生產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別是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不僅有越來越大且復雜的工業區,通常采取按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謂的與某一特定工業相聯系的多種互為補充行業的專業化模式。而且出現了發育完全而繁榮的主要制造業城市。在適當的時候,這些城市??伯明翰、曼徹斯特、謝菲爾德、里茲??將成為工業革命的基地。
綜合而言,英國農業勞動力在1500年僅只養活占總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萬人以上的城市勞力以及可能總共18.5%的城鄉非農業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農業人口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為農業長期轉化的體現及由于農業生產率不可阻擋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萬人以上的城鎮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農業以外。1800年時這些數據分別達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蘭從真正意義上說已不再是農業國。
經濟演化結果
彭慕蘭相信直到約1800年時長江三角洲與英國經濟追求的發展軌跡基本相似。然而事實上長江三角洲的馬爾薩斯式路徑導致的是衰退與危機,而同期英格蘭經濟則遵循了亞當斯密式軌跡。
長江三角洲
很遺憾我們不能贊同彭慕蘭的觀點。長江三角洲經濟演化在十八世紀已經表現為日益增加的馬爾薩斯危機癥狀。如果不是十七世紀內朝代更替的戰爭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脹而使長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與其在1620年時相同,這很可能會發生得早得多。彭慕蘭忽視了這一巨大的對人口增長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對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于是得以從更有利的角度描繪十八世紀的經濟。但此抑制顯然賦予經濟以本來不會有的空間;也因此有一個在勞動生產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驅動下的膨脹過程,在時間上延長至不可能達到的程度(見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實是,在整個十八世紀,盡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麥,長江三角洲人均糧食產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見表三; 亦見張仲民, 1988: 163, 表4.3)。農業確實馬上就會陷入困境,無論如何追加的勞動力也無法再提高產量,表明人口已達到或接近頂點。人口增長在長江三角洲于約1750年時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這是一個經由溺嬰、向外移民及預期壽命不斷下降所帶來的趨勢。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長率壓低了大約75%,從1690年至1750年間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間的每年0.18%(見表二)。
在這種情況下,被迫越來越依賴市場而從事家庭制造業以勉強維持生存的長江三角洲農民別無選擇,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區域外邊緣地區運來的糧食。這樣邊緣地區有一個受人口增加推動的集約增長過程,與在核心地區經由人口驅動的勞動集約形成的集約增長型式相平行。通過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糧食,這在長期內有助于在長江三角洲減緩人口壓力。然而由于這些邊緣地區的經濟演化大致追隨人口增長、與長江三角洲核心地區相同的軌跡,即人口增長和勞動生產率下降,他們滿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斷下降。
自明中葉起,中國農民開發了長江中上游地區、西南(云貴)、西北、東北(滿洲)、臺灣島、以及包括長江三角洲自身在內的各處閑置的山坡、丘陵(郭松義, 1990)。在開發并占有大塊土地之初,他們即有大量的剩余糧食出售并能以較有利的條件提供糧食以交換長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和長江三角洲一樣也經歷了田產規模與單位勞力投入糧食產出無可阻擋的下降,并最終象長江三角洲一樣需要轉入原始工業生產。從十八世紀開始,這些趨勢因人口增長加快及殖民步伐達到空前高峰而加劇。到了該世紀最后四分之一時間,曾是長江三角洲主要糧食來源、占其總量高達三分之一的長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劇削弱,而這正是長江三角洲陷入馬爾薩斯危機之時(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類似的發展也可見于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當地糧食剩余下降了多達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張國雄1993,45,表; 蔣建平1992, 55-56)。的確,把全國作為整體來看,每人糧食總產從明到清前期看起來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糧食總產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該數字繼續下降至19世紀,亦即長江三角洲陷入馬爾薩斯危機的同一時間(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義 1994,47)。
長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長導致勞力集約的發展途徑達到極限的表征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換條件急劇惡化,與之相伴的似乎是邊緣地區糧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義,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糧食的成本越來越高,長江三角洲小農盡其所能來增加棉布產量。但所導致的棉布供應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糧的價格下降得更低。長江三角洲明顯已進入彭慕蘭非常恰當地指稱的“原始工業的困境”。
彭慕蘭認為長江中游家庭安排婦女勞動力到家庭原始工業上是繁榮增長的象征,對他而言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過接受婦女勞動力的低回報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織”社會模式的能力;我們則認為,農民對因土地資源遞減而導致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及因此直接生產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應。彭慕蘭聲稱“雖然參與任何一種出口品的勞動的物質回報不斷下降,原產品價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夠使繼續專業化比多樣化報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織’勞動分工是一種有時會被現實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見它是一種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當長江中游在十八世紀后期變得更富庶時更多的家庭會愿意采用。(很有點象在某些西歐國家有些時期當男人掙的錢足夠可以把婦女限制于只做家務那樣)”(2000:249)。很難相信長江中游地區的婦女會比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婦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業相對于稻作的低回報。除非在人口壓力下分田產及隨之而來的農業對家庭勞力需求降低、同時為勉強維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業中家庭勞力需求的情況下被迫如此去做。這樣,整個十八世紀兩湖地區農民將大部分精力投入糧食生產,而在手工業及其它非農生產上只花極少時間或根本不花時間(張建民1987,58; 蔣建平1992,56),湖南農民則似乎直到十九世紀還沒有大量從事棉紡織業(Perdue 1987,36,246-47)。很遺憾我們不能贊同彭慕蘭的觀點,可是當這種轉移的確發生時,它所表現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識選擇,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英格蘭
當長江三角洲以農民為基礎的經濟陷入馬爾薩斯式危機時,英格蘭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步入自我持續的增長。在前近代時期,曾嚴重困擾中世紀經濟并在早期近代時期歐洲大部地區繼續產生作用的生存危機被拋在后面。同時,結婚年齡提高與獨身率提高的結果是生育率增長減慢,有助于資本積累與消費的增加。
彭慕蘭懷疑有機經濟“同時繼續擴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費、和增加一地工業的專業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個半世紀里,英國經濟所達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農業外勞動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實際工資增加約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這是一個同期歐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聯省部分地區外)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成績,并且為更大的發展作了準備。下面將會看到,1750-1850年間雖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業與服務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還會持續增加,生活標準及人均收入將更為提高。
古典工業革命時代(1750-1850)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的經濟
1750年后一個世紀內,也即大致為古典工業革命時代,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演化必須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為是它們此前發展道路的延續。與彭慕蘭所聲稱的正好相反,長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嚴重的馬爾薩斯式危機表明了其在整個十八世紀業已顯示的衰落趨勢已達到頂點。同時,盡管彭慕蘭試圖縮小此期內英格蘭農工業的進步,英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的確是革命性的。
工業革命時代相反的經濟軌跡
長江三角洲:馬爾薩斯式危機與生態危機
古典工業革命時代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型式是十八世紀期間業已顯示之趨勢的延長及其達于頂點??即農業生產率衰退、農業中由勞力集約提高產量從而彌補低生產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業中勞動集約以彌補農業報酬迅速遞減的能力下降。約在1800年或更早,長江三角洲似乎已達到了追加勞動投入不再能夠增加農業產出的臨界點。正如白馥蘭在談到整個中國時所說,“所有可耕地到那時都已開墾,靠傳統生產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產力的任何明顯增長”(1984:12,亦見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認為1780年以后,中國農業產量從整體上開始下降(亦見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結果是經濟急速陷入馬爾薩斯式危機。其標志是制造業產品相對糧食的交換價格下降及隨之而來作為農民維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業發生危機;那些截至當時向長江三角洲提供糧食的新近開墾的較邊緣地區的土地陷入生態衰退;預期壽命的持續下降;以及地主和佃農之間為土地和剩余的爭端劇烈化。
長江三角洲的馬爾薩斯-李嘉圖式擴展途徑接近最終極限在該地區的主要輸出物棉布交換條件的急劇惡化上表現出來(張仲民, 1988:206)。彭慕蘭承認長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糧食購買力在1750年至1800年間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從實際上講,這意謂著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農家為維持相同的糧食消費水準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時間,一個世紀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時間。可以斷言,因為幾乎別無選擇,原始工業家庭勒緊腰帶、延長了工作時間、并試圖最大限度提高棉布產量。棉作帶的農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紡織,被迫通過提高棉布產量來彌補其相對價格的下降,而這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達到,直至棉布成為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一行為過程只不過是加劇棉布的過剩并增加價格下降的壓力,直到有時(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張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農民開始生產劣質紡織品以通過欺騙商人而增加其邊際利潤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況下,農民開始生產能得到較高價格的精致棉布,但這要求比一般標準大得多的勞動投入。男人也轉入織布、接管織機、并只讓婦女紡紗 (Bray, 1997: 225)。通過從外地購買較貴的原棉從而進一步降低其邊際利潤,或通過減少糧食種植面積并接受更低的綜合勞動報酬,松江農家得以獲得足夠的原棉去延長其棉紡織的時間以維持生存。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小農甚至開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錠紡車來尋求提高總產,因這一方法縮短了紡紗時間而使更多勞動力可被用于織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隨著婦女用新錠紡紗、男人接管織機、以及購買來自華北已軋的棉花,一個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內所織之布的總匹數并因此確保生存。但為了繼續用這種方式維持生存,農民在棉花產品交換價值惡化的壓力下被迫減少高價大米的消費,而日益大量地以來自該區之外的粗糧為生。與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對照,到十八世紀末粗糧在一般長江三角洲農家糧食消費中占達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長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馬爾薩斯式危機。
當十八世紀接近尾聲、農業與工業中的勞動集約所產生的回報均趨于消失時,長江三角洲隱然更加依賴于從邊緣地區的輸入。但不僅是通過勞動集約和農業向新土地主要是長江中游地區拓展以確保進一步輸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趨向終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獲也不斷顯示是以地區生態穩定性為代價取得的。十八世紀中期邊緣地區低地被填充意謂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在此后轉向丘陵與高地。農民們首先用盡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們即在其土地上種植玉米、土豆及藍靛,由于這些作物迅速耗盡土壤肥力,農民們除了放棄已有土地另行開荒外別無選擇,可預見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壞隨之而來。隨著森林覆蓋層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層消蝕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與灌溉系統不可避免的淤塞,這又開始導致下游水稻產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趙岡等, 1995: 136-42)。生態破壞在十九世紀初期長江中游地區顯得最為嚴重,也擴展到長江下游與三角洲地區,損及浙北及長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況尤其嚴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總之,十九世紀完全體現出來的生態危機不僅有其十八世紀的根源,而且應被視為是該地區經濟的集約與廣泛性增長的整個過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積產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預見,始于1690年而長達一個世紀的人均糧食產量下降、1750年以后對原始工業生產者而言不斷惡化的交換條件、以及截至當時為止長江三角洲主要糧食來源的地區陷入生態危機,都造成長江三角洲的農村人口損失。這種趨勢導致農民逐漸放棄價格上漲的米類而依賴于粗糧。明代,江南農民的主食主要依賴于米飯,至十八世紀中期,1/3主食被粗糧及薯類所代替(洪煥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個跡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頓的人口,它看來部分可以解釋為溺殺女嬰的增加,及農民迫于在日益惡劣的環境下維持糧食消費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機制。由于進一步分產明顯是越來越不現實,農民終于不得不開始嚴格控制其家庭規模。權衡確保家庭生計的當務之急與養老的長期需要,農民夫婦必須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選擇,以減少分家??即把兒子趕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數量以求減少分家。長江三角洲的溺嬰與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蘭暗示的代表了為支持經濟專業化與擴展而行的“最優化抉擇”,而只是在長期的人口膨脹過程達到頂點時出現的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水準的反應。
最具有表癥意義的是,十八世紀下半葉(也許更早)時預期壽命下降。在長江三角洲各處,十五歲男性的平均壽命從世紀中葉之后下降了22.3-29.6%(劉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沒有試圖估計從出生開始的平均壽命)。 [3] 在邊緣區安徽,男性預期壽命自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前三分之一期間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個毗鄰長江三角洲的類似的“繁榮”區,相應地從十七世紀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紀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紀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災難期間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總結說,“我們可以將男性平均壽命的持續惡化視為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清代中后期兒童與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上升……平均壽命下降與嬰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來在太平浩劫推動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經形成”(1990: 133; 亦見Liu, 1995a:120)。
最后,隨著地價與糧價在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急劇上升及平均田產規模下降至維生水平以下,長江三角洲的地主與中國許多其他核心區一樣尋求“重新談判”租佃條件,他們在削弱佃農土地安全性的斗爭中尋求政府的支持以便從谷價上漲及農民對土地需求增長中攫取更多的收益。從十八世紀中后期的某一時間開始,長江三角洲太湖地區的地主特別成功地削弱了??盡管從沒有廢除??佃農對田面權的擁有權利。雖然地主從未確保隨意辭佃的法律權力或能力,他們成功地減少了田面權擁有者將其出賣的權利、抓住了此前歸田面權擁有者與售出者的賣田費、并強化了他們自己在驅逐欠租佃農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從佃農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過壓榨那些因田產縮小到低于生存的水準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勞力去支付較高地租的小農,而得以獲取更多的農業剩余。事實是這些所得存在時間很短,因為在1860年對江蘇的完全控制從根本上毀滅了新出現的狀況,并留給佃農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蘭:工業革命
彭慕蘭主張,如果英格蘭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產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與木材,而且如果其國內沒有煤資源則英格蘭也會不可避免地遭遇與拖跨長江三角洲相似的勞動集約、勞動生產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態危機。但他的論點無法令人信服。這是因為,首先,與彭慕蘭所說相反,所有證據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個世紀里,事實上英國農業繼續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內得以供養農業外和工業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之高為任何(至少規模與英格蘭相當)其他地區無法比擬、其人口增長率可能也是史無前例的。其次是因為,不存在生態危機的證據。因為英格蘭并沒有潛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蘭所說,它可以從歐洲內部通過貿易獲得足夠的基本原料供應??因此無法將其視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國農業的成就
彭慕蘭關于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瀕臨轉向勞動集約生產之論點的中心是他認為英國農業“很少……繼續開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國農業生產率看起來在1750年至1850年間沒有太大變化”(2000: 216),結果“英國自己的糧食與肉類總產變得不足”(2000:217-18)。但這種斷言毫無根據。事實上,英國農業支持整個此一世紀英國狂熱的工業化過程的能力??包括總人口與其中非農業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長??或許是工業革命第一階段也即經典階段的標志性成績。
1750年至1850年時期對英國農業的要求之大是無以倫比的。英國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長,此期內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脹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從控制前近代時期的低密度人口體制到一個全新的高密度人口體制的歷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初變得普遍的較低的結婚年齡與更強的結婚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內能靠常規工資雇傭過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長,這一現象本身則是雇傭工作總額中工業和服務業比例上升的結果。在日益易于由工業與服務業的工資勞動而獲得撫養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紀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之間,女性結婚年齡從約26歲下降到23.5歲,而獨身率(不結婚的比例)則從約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時,在1750年至1840年間,農業外人口/勞力占總人口比例從約55%增加到75%。最后,盡管有由人口增長與非農就業增加所含的勞力過剩的巨大趨勢、以及由歉收、爆發戰爭、及歐洲范圍的人口增長(特別是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間)所造成的糧食價格上漲的龐大壓力,名義工資仍能在此期間保持與生活費用同步增長。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實際工資增加約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上升。1750年至1850年間,當長江三角洲農業陷入危機時,英國農業中每工人平均產出增長了60%,而單位土地總產出(單產)則至少增長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結果,至1850年,英國勞動生產率水平據估計已經是歐洲大陸各國勞動生產率的兩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見表5下)。
表五 1750年與1851年間歐洲農業生產率水平比較
國家|1750|1851
英格蘭|100|100
法國|52|44
德國|36|42
荷蘭|96|54
比利時|79|37
資料來源:1750年的指數來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數來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盡管自1750年以來人口增長了一倍且非農人口比例從55%增加到約65%,進口到英格蘭的小麥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計。即使到了1837-46年間,進口小麥也只占總消費量的12%。而且這一進口量中約三分之一來自愛爾蘭、三分之二來自俄國與普魯士,基本上沒有從英屬美洲進口小麥。換句話說,在英國成為完全現代農-工業經濟的工業革命經典時期,沒有統計數字基礎來支持彭慕蘭的如下中心論題:一、英國農業有不足之處;二、由于農民生產者為生存的生產導向以及其農業更趨向國內市場,“歐洲大陸沒有不斷增加的剩余出售給英格蘭”(2000:217)。事實上,一直到1860年,普魯士與俄國的農民雖然無疑比美洲奴隸處境略好,可能而且確實被迫生產了幾乎英國所有的進口糧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蘭把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經歷了日漸嚴重的食品短缺這看一事實看得很重。實際上,隨著谷物法在1846年被廢除,英國經濟鼓勵糧食進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業中的競爭優勢。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競爭性的工業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糧食進口畢竟是其經濟強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顯然如彭慕蘭所強調的那樣,英國不能與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進行糖貿易。幾乎所有英格蘭的糖消費都依賴于從西印度群島的進口,而且極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為糖的供應地。但正如彭慕蘭自己指出的那樣,糖只占英國食品總消費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總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許要附加說明的是糖是一種可能有負營養價值的消費品。假如糖的供給被斷絕,英國人毫無疑問會失去一項其極為喜愛的食品。但英國通過結合國內生產與海外進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養自己的能力不會受到絲毫影響,因為從面包確保供應一定數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證供應1000卡熱量的面包價值為1.32克白銀,而用以保證供應同樣熱量的糖價值為其兩倍以上,達3.0克白銀(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號給羅伯特·布倫納的個人通信; 參Allen, 2001: 431, 表7)。
資本積累與技術變遷
除英國工業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國內煤供應所得優勢之外(見后),彭慕蘭 (2000: 44-67)主要通過極度縮小英格蘭對中國的純技術領先,來試圖貶低英國工業在約1800年之前相對于長江三角洲工業可能擁有的任何優勢與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認已發生的突破(如在棉紡織業中)的廣泛意義,聲稱其中含有大量幸運因素,并堅持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使英國領先于中國工業的發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術優勢。但這種爭論方法沒有抓住要點。使英格蘭工業比長江三角洲工業及歐洲工業具有優勢的并不是它的技術創造性,雖然這在事實上相當豐富,而是它在技術進步發生后有能力去實行。
英格蘭對長江三角洲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優勢因此首先是表現在其工業的敏捷反應、及其快速連續采用來自任何地方的發明的能力。在長江三角洲,棉業擴展主要出自農民在小塊田產上直接以農業生產維持生存能力的不斷下降,及隨后盡管其相對于農業的回報低仍必需進入家庭制造業的推動。在這一情況下,由于整個經濟日趨貧困,工業單位無法超越棉業,且很少有進行投資的資源。他們因此在生產日益過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勞動接受更低生活標準為基礎而承受更低的回報以求生存。這是一種對新近發展的技術吸收能力最為有限的環境。
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英國工業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是對因可支配開支額上升而增長的需求作出反應而擴展。這使得工業回報率特別是與至當時為止一直與之相結合的農業生產相比上升(見前述)。由于其開始即依賴于市場,工業單位于是僅憑其在競爭壓力下確保獲得滿意利潤的能力得以繼續生存:通過從一個行業換至另一個行業以取得最佳回報、將剩余再投資、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產效力的技術。結果是高度多樣化的工業部分,其特點不僅表現為非常高水平的技藝,而且表現為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資本積累率與技術變化速度。來自國民收入的投資率由1760年的6.8%上升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與此同時,與彭慕蘭暗示的相反,重要變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幾個行業內,而是橫跨廣闊的范圍,常常是經由采用首先在歐洲大陸形成的發明??不僅發生在棉花、鋼鐵以及能源技術行業,而且在機械工具制造、制陶業、玻璃制造業、造紙業、及一系列化學品制造業領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態危機
正如1750年后一個世紀內英國食品供應沒有出現潛在問題一樣,那里也沒有由開始出現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態危機。這里彭慕蘭完全錯誤領會了瓦格利的觀點。與古經典經濟學家相同、瓦格利認為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人口增長所加在土地上的壓力遲早會將英格蘭的無機經濟帶進停滯的狀態。換一種方式說,瓦格利認為如果沒有向無機經濟(煤、蒸汽等等)的轉變,英格蘭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樣的人口增長又取得其在整個十九世紀所達到的人均總產增長。瓦格利沒有試圖證明的是,因為沒有證據來支持,??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格蘭處在原材料短缺的邊緣,如果沒有斷斷續續增加煤的使用,這一短缺原本將會迫使英國走上勞動集約的途徑。彭慕蘭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實的假設??即如果沒有煤,英格蘭就不會有它確實經歷了的向無機經濟的轉變??而將其變為他自己的論點,即是英格蘭在十九世紀前期急劇增加對煤的使用將其從經濟內卷或生態危機中挽救出來 (2000: 218-19, 263, 276)。與彭慕蘭之說相反,1800年英格蘭遠未“瀕臨[與長江三角洲]同樣的懸崖”(2000:12)。
當然,無可否認,煤確實如實際上發生的那樣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蘭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煤在整個前近代時期的英國經濟中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確實比在其它任何經濟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剛好與彭慕蘭的相反:英格蘭利用煤達到向無機經濟的轉換不是代表一個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勞動集約度與內卷轉化的非連續性發展,而實際上它本身表現的是英格蘭基于此前幾個世紀的、穩定增長的工業能力。這不僅體現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使它擁有更好且更廉價的獲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機的出現(至十八世紀早期英國幾乎所有的大煤礦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現在對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廣泛的工業行業產生的對煤成本的負擔能力。瓦格利自已認識到了此點,他承認向無機經濟的轉換并未等待工業革命而是始于他稱為“有機經濟的高級價段”亦即英國經濟獨一無二、迅速發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紀(1998:34-57,特別是54-56)。人們只要留意長江三角洲可資利用的巨大的煤礦資源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尚未得到認真的開發就可以對這一點有極徹底的理解。 [7]
無論如何,不管對瓦格利關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觀點作如何解釋與評價,都很難看出它能夠支持彭慕蘭獨特的關于美洲作用的論點。彭慕蘭斷言英格蘭“利用源自礦物能源而來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種新大陸資源的流入”(207)。但他從未解釋通過什么方式或為什么會是這樣,更不用說提供證據了。事實上的確難以看出怎么可能會是這樣。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實是,1750年至1850年間,英國經濟成功地沿著十七世紀較早時就開始的途徑前進,從根本上加大了其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距離。當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在馬爾薩斯式危機與生態危機中陷得越來越深、并且人口膨脹結束時,英國經濟繼續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盡管急劇加速的人口增長對其構成巨大的抵銷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幾乎高三倍,GDP則可能增長約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結果:生活標準問題
考慮到英國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歷程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極為不同,如果它們在生活標準方面沒有歧異的結果則反倒真會令人驚奇。
消費的商品
彭慕蘭其實作了許多努力,以明確或暗示的方式承認了英格蘭生活水平較高,盡管他最后卻斷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蘭對肉和奶制品的消費高得多。畢竟,中國農業中幾乎沒有畜牧業,而這也反映在中國全為谷豆的繕食結構中(在二十世紀早期的長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攝入量來自非肉及非奶資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蘭也承認英國以及整個歐洲的住房質量比長江三角洲或實際上全中國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爭辯說中國的水質量較好,但結果他的證據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對明治日本水質的描述)及某種程度上的東南亞 (2000: 36),根本不是中國或長江三角洲。 [8]
彭慕蘭的確號稱在一系列他所謂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費上在兩地水平相當。但他自己的證據反駁他的觀點。據彭慕蘭自己承認,1750年英國人均消費的糖是同時代中國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國人均茶消費量已比1840年代中國人均消費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國人消費的茶比中國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們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數字而非彭慕蘭所引施堅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數字,比較之下英國人均茶消費量更大。事實是,1800年英國人人均茶的消費比中國人在1980年代末還要大(Note?)。茶與糖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蘭承認荷蘭在十七世紀可能就有比中國1930年代還精致的家具,而英國在約十八世紀后半期就已超過荷蘭的生活水準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蘭提出英格蘭的人均布產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與 Cole 1962) 與長江三角洲的人均布產量相當,并暗示這可能轉化為相同的消費水平(2000:138)。然而,為了使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的人均消費水平相似,彭慕蘭必須得出長江三角洲棉布總產達到(3億匹)的結論,這一數字要比此問題上的權威學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億匹的數量估算高三倍,而他們的估算已經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數字7.8千萬匹(1998,30)要多出2.2千萬匹。要達到彭慕蘭所估計的數字,江南所有年齡介于10歲與50歲的婦女每年要紡織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倉、蘇州北部之外棉紡織業并沒有達到彭慕蘭所說的這樣普及。即使江南紡織中心,遲至十八世紀末,棉紡織業才達到如此繁榮水平(張仲民,1988)。彭慕蘭自己對人均消費的估計甚至假設所有三角洲所產棉布都就地消費了,盡管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該地不得不大量輸出所織之布以換糧食維持生計(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蘭承認,如果將棉布輸出考慮進去,江南的消費水平將非常可能會比英格蘭的消費水平低。而長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費的確是低于英格蘭。彭慕蘭還大大低估了長江三角洲用于種植糧食的耕地面積,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種棉花的耕地面積,因此也過高估計了可用于紡織的原棉數量。在水稻栽培面積的計算中,彭慕蘭未能將糧食生產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慮進去,而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時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種子、肥料、牲畜等項的部分。總和起來,地租和生產成本將使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面積有相當大的增加,并相應地降低他對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均棉布產量和消費的估測而使其更為低于英格蘭的水平。
最后,彭慕蘭只選擇了極少數的消費品進行比較。1770年英國的制造業經濟為工農業中的消費者生產了種類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屬制品、陶瓷器、鏡子、蠟燭、鞋、鈕扣、帶扣等等,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當數量的這類商品。雖然彭慕蘭提出歐洲的消費激增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還限于狹窄的領域,他不能也沒有對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蘭用同樣的觀點。工業革命前(1625-1725年間)的英國工資勞工與小農場主已經極常規性地擁有桌子、壺與鍋、白蠟器皿及陶器,以及較少常規地擁有書、鐘、圖畫、梳妝鏡、餐巾桌布、窗簾、瓷器、甚至銀器。自耕農更經常擁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還加上圖畫、刀叉及喝茶之類熱飲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對這些及許多其它物品的擁有在英格蘭變得更加普遍,它們已深深地進入人們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紀在煙草、肥皂、蠟燭、印花織品、烈酒、廉價布、鈕扣、陶器、帶扣、燭臺、釘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帶、假發、鞋、衣服、燉鍋、青銅與黃銅廚具、椅子、桌子與桌布、門把手及門環等方面消費興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這一“消費革命”的基礎??正如我們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開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終是建立在食品價格不斷下降與實際工資持續上升的基礎之上,這些又有賴于農業生產率的長期增長。
預期壽命
最后,彭慕蘭被迫將其十八世紀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生活水平相當的論點幾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壽命的基礎上。他爭辯說,任何英國在消費上超過長江三角洲的明顯優勢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國人“更健康、長壽、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況下才能被接受為真正的優勢。在彭慕蘭看來,情況并非如此,因為中國人的壽命跟英國人一樣長。
彭慕蘭引用的研究顯示中國人預期壽命在安徽從39.6歲降到34.9歲 (Ted Telford)、在東北是男子35.7歲與女子29歲(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員的40歲(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對這其中的一些數字的意義作限定,因為它們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個月(滿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無論如何,除了皇族外,作為其基礎的人口記錄是相當不完全的,即沒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嬰孩。二十世紀有關預期壽命的數據更為可靠,而所得出的數字明顯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發現在華南40%的嬰兒與幼孩在滿五歲之前死亡,50%的嬰兒與兒童在滿十歲前死亡,并且總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歲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臺灣更好的數據顯示十歲以內的死亡率為40%(Barclay, 1954:172,附錄)。 [9] 這些高嬰幼孩死亡率轉化為很低的預期壽命。Barclay和Coale(1976)對1929-30年中國農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預期壽命為24.6歲,在華南為21.5歲(620,表12),而當時長江三角洲的農民擁有比十九世紀時更多的土地。就臺灣來說,Barclay發現甚至在日本統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預期壽命在1906年還是27.7歲。 [10] 日占以前的預期壽命當然要低于27.7歲,因為到1906年它已經上升相當快,1909-11年達到32.4歲、1921-30年達到34.5歲。只有在日本殖民當局大規模介入衛生與學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讓大量的孩童登記入學——及持續經濟增長——1910年至1940年間總產增長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況下臺灣的預期壽命才出現急劇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當然,用這一時期的數字去說明十八世紀的情況會有一些問題,但考慮到1920年代臺灣肯定較好并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很難想象十八世紀的長江三角洲怎么可能會有相同或更高的預期壽命。
總之,很難看出十八世紀后期長江三角洲自出生時計算的預期壽命能夠大大高于30歲,而1800年至1810年間英格蘭自出生時計算的預期壽命是44.8歲(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釋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紀中葉棉價太低以致一個長江三角洲婦女70天紡織所得僅夠買一石米(見Huang, 2002)。這暗示自1750年起購買力全面下降了約60%(參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過長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區的墾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縣份均依賴糧食進口。為增加當地糧食供應,某些移民或 ‘棚民’ 開墾山地種上紅薯與玉米,但開墾山地造成水分損失與土壤侵蝕,并因此常被政府與當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劉翠溶有資料的九個地區(總共49個家族)中的每一個地區,在整個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早期預期壽命均下降 (劉翠溶, 1992; 亦見Heidjra, 1998: 437)。在長江三角洲的江蘇部分,15歲男性的預期壽命在1600年至1800年間從54歲下降到38歲; 在長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歲男性的預期壽命則在1700年至1825年間從46歲降到31歲(劉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與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長江三角洲的地區(紹興府)發現了類似的下降(Harrell與Pullum, 1995:148)。彭慕蘭不接受這些發現主要是因為技術問題,家譜記錄中漏掉了的資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補 (2000: 37)。這樣家譜中前幾代預期壽命當然會有偏于上升的趨勢,但五代左右之后這種偏向看起來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結果是相當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蘭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現出來的預期壽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蘭注意到預期壽命從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時下降得更厲害、降至31.1,亦即總數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從這里爭辯的觀點出發,則英格蘭在(大致的)中世紀、早期近代、工業革命時代分別成功地從農民占主導轉換到依賴市場生產者為主導、到工資勞工為主導地位的人口體制。
[6] 英國的情況當然與長江三角洲通行的情況完全相反,長江三角洲類似的以越來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換邊緣地區的糧食,因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來越多的農民勞力以購買任何既定數量的糧食。
[7] 美洲當然提供了工業革命在棉花生產上所需的原棉。但在這樣做時,它并沒有滿足任何嚴重的、且曾拖英國經濟后腿的纖維短缺;因此難以看到它與彭慕蘭觀點的相關性,彭認為美洲在讓英格蘭克服“土地制約”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蘭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幾乎所有英格蘭的原棉之需的事實當作英國市場沒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國棉市場對美洲的準壟斷完全表明沒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國南部一樣如此有效或廉價地生產原棉;它并不表明沒有其它地方能夠提供原棉。毫無疑問生產成本會高些,價格因而也會高些。但考慮到棉花制造業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這種降低經由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遷得以保證,難以相信市場沒有能夠吸收終極產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價格。例如紡棉的價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間下降了90%,反映出紡棉所需操作時間的減少:紡一百磅棉花的時間從用印度手紡車所需的50,000小時(十八世紀)到Crompton精紡車所需的2,000小時(1780年)、到動力驅動精紡車所需的300小時(約1795年)、到羅伯特自動精紡機所需的135小時(約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蘭自己指出的那樣,在1861年,隨著美國內戰開始,盡管美國棉花仍能有辦法到達英國市場且仍占該市場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價格上(仍有限)的增長(超過1860年價格),突然向英格蘭出口接近美國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內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數基本上是通過把“已經存在”的、否則會銷往其它市場的棉花轉運到英國市場(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東南亞的情形也不是決定性的,證據表明在人口湊密的地區水質量很差,只有煮開后才能喝(Reid, 1988:37)。
[9] 如果晚期帝國人口研究的發現是對的,我們就可以得出十八世紀死亡率可與1920年代早期臺灣(日占后二十五年)的死亡率相比(約每千人二十五人死亡)的結論。
第6篇:微觀經濟分析法范文
關于績效的概念,OECD(1994)認為績效是有效性,既包括實施該項活動的效率、經濟性和效力,還包括活動實施主體對該項活動過程的遵從度以及社會公眾滿意度。普雷姆詹德(2002)認為績效包含了節約、效益和效率等方面的內容。陸慶平(2003)認為績效實際上是一項活動實施的結果,這種結果包括投入資源的合理性、結果的有效性,以及實施這項活動所投入的資源與獲得效果的對比關系。叢樹海等(2005)認為績效是效益、效率和有效性的統稱,包含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兩個層面的內容。就行為過程來說,主要是指投入是否最小化,過程是否合規;就行為結果來說,主要是指產出與投入相比是否有效率,行為的結果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行為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和社會影響等內容。
預算績效管理是以績效指標和事業成本為核心,以績效目標、績效撥款和績效評價為基本環節的政府理財模式。預算績效管理突出強化了政府預算為民服務的理念,是預算改革和深化的必然要求,目的在于切實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它強調了政府預算支出的責任和效率,要求在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的全過程中要更加關注預算資金的產出和結果,要求政府部門不斷改進服務水平和質量,盡可能地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努力地向社會公眾提供更優質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切實做到政府行為的務實、高效。
二、預算績效管理理論基礎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 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化,需求也變得多樣化,社會公眾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也在不斷增強,時代變化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一種突破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學科界限,把當代西方經濟學、政策科學(政策分析)、政治學、工商管理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原則、方法及技術融合進公共部門管理的研究之中,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論便應運而生。該理論尋求高效、高質量、低成本、應變力強、響應力強、更健全的政府運行機制,遵循“顧客導向”、“市場導向”和“結果導向”三個原則。“顧客導向”的原則重新界定了政府與納稅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市場導向”的原則強調政府應該多運用市場機制,利用企業管理的方法,提高政府效率;“結果導向”的原則強調對于政府的考核,應該改變過去過多關注過程控制和監督的理念,應將更多的注意力關注到政府活動的結果和產出上,以克服政府工作的僵化,更加靈活地提供公共服務,不斷提高政府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變革,在政府制度設計、運作方式、理財模式方面都深深烙下了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烙印。可以說,預算績效管理,既是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推動新公共管理理論轉化為實際制度安排的重要工具。
(二)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在政治領域中,政府公務人員和市場領域的主體一樣,同樣也是“經濟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選擇理論將應用于市場領域的“成本—效益”這一微觀經濟分析方法,引入到政治決策過程中。公共選擇理論指出,政府存在政府失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將政府行為經濟化或市場化是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客觀選擇。根據這一思路,政府公務人員的身份是“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的 “顧客”或“客戶”。 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衡量和考慮的是政府應當花多少財政資金提供某項公共勞務,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需求。將政府行為經濟化,這既是市場經濟關系在政府行為中的體現,同時也是解決政府失靈問題的最佳方案。實施預算績效管理,不斷強化政府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觀念,關于預算資金的產出和結果,提高財政支出效率,恰恰是公共選擇理論在財政預算領域的最好應用。
(三)財政支出的邊際效用理論 財政支出效率與財政資源配置職能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財政支出是否有效率,衡量的標準是:財政支出所取得的各種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總和,是否大于在聚財過程中對經濟所形成的代價或成本,也就是說要取得效益剩余或凈效益。如果凈效益值越大,則說明財政支出越有效率。社會資源是在財政部門和民間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實現社會資源在財政部門與民間部門的優化配置,按照邊際效用理論,就必然要求用于財政部門的資源使用的邊際效益等于該資源用于民間部門時所取得的邊際效益。如果財政部門資源使用的邊際效益大于該資源用于民間部門的邊際效益,這就說明財政配置資源是不足的,可以增加財政部門對資源的使用,以便獲得更大的效益;反之,則應減少財政部門的資源配置規模。當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滿足了上述條件,則不僅資源配置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的,而且此時財政預算決策也是最優的,財政支出也是最優效率的。根據此理論所形成的財政支出項目“成本—效益”分析法,已經在政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中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應用。
三、推行預算績效管理意義
(一)推行預算績效管理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是以人為本。公共財政是民主財政和服務財政,在財政管理中,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要實現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要節約而又有效地用好稅收,向社會公眾提供高效的公共物品和服務。要想做到這一點,在財政支出的活動中,必須要充分注重績效,推行預算績效管理,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把納稅人的錢用好,使得支出能夠產生實實在在的社會效益,充分發揮公共財政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等方面的職能作用。
(二)推行預算績效管理是實現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進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事關財政事業的健康發展,是新時期財政工作的迫切需要。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必須要依靠財政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推行預算績效管理,對于實現財政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具有重要意義。在理念上,預算績效管理體現的就是財政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通過對財政支出活動的績效評價,把績效評價結果作為安排預算的重要依據,從財政資金分配的源頭上進行規范,促進財政資金的合理安排,體現的是以結果為中心的理財理念。在操作層面,推行預算績效管理,通過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和特定方法模型的運用,衡量、監測、評價支出活動的經濟性、有效性,為財政支出決策提供依據,提高財政管理水平。
(三)推行預算績效管理是建設“高效、責任、透明”政府的客觀要求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公眾越來越關注政府的績效情況和納稅人的資金的使用情況。要大力推行行政權力的公開透明,建設“責任政府”和“陽關政府”,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以此來促進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預算績效管理關注產出的效果以及目標的實現程度,理應為“高效、責任、透明”政府建設盡份內之責,同時也是“高效、責任、透明”政府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四)推行預算績效管理對于化解地方財政困境具有現實意義 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后,由于財權層層上移,事權層層下移,導致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地方政府財政面臨困境。再加之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實施以投資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財政收入的增長難以跟上對財政資金需求的增長,從而造成了強勁的財政支出壓力。有限的財政資金在分配上也缺乏科學合理的決策機制,在各級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爭預算、爭項目的現象,預算資金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財政部門和預算單位的博弈來進行的,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最終導致了預算資金的平均分配,難以實現財政資金的有效率使用。目前,在財政體制沒有辦法進行大的調整的前提下,不斷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是化解地方財政困境的一個重要途徑。推行績效預算管理,強調財政支出的效益,將支出控制的重點從投入轉到了產出或結果,從根本上改變“重分配、輕管理”格局,制定科學的財政資金分配決策機制,從而達到“少花錢、多辦事、辦政府應該辦的事”的目的。
四、預算績效管理目標與評價指標設定
(一)預算績效管理的目標定位 公共財政的本質是市場經濟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化的市場主體組成了競爭性的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凡是市場能夠辦得了的和辦得好的,就不應該交由政府承擔。公共財政應該把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組織國家財政活動的基本著眼點,公共財政的職能在于提供必要的公共性基礎條件,維持公平、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增進社會公眾福利,這是財政運行的基本取向,同時也是國家財政活動應遵循的指導性原則。因此,預算績效管理的目標定位,不能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要更多的評價財政支出成本既定的條件下所產生的政治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二)預算績效管理目標設定依據 預算績效管理目標的確定是預算績效管理的起點和核心內容之一。預算績效管理關注的重點在于財政支出的結果和效果如何,也就是政府花了錢,老百姓最終得到了什么,而不是政府的錢夠不夠花,怎么花。在實踐中,設定績效目標有不小的難度,必須要有一定的依據。一是績效目標的設定要與部門的戰略目標有機的結合起來。部門的戰略目標是部門績效目標的基礎,根據部門戰略目標的階段性,并將其分解到每個預算年度,并在此基礎首先提出本部門的績效目標,在總體上,確保績效目標與部門的戰略目標的一致性。二是績效目標的設定要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方式。在設定績效目標的時候,由于不同部門的戰略目標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就存在著如何兼顧可比性和獨特性的問題。此時,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方式設定績效目標,確定一個總體上相對一致的而且又能充分體現部門個體特征的績效目標原則,就顯得比較重要了。三是績效目標的設定應當采用部門申報和財政部門組織審核相結合的方式。第一步,績效目標首先由部門申報,在申報的同時提交項目可行性方案以及項目資金使用的績效目標。第二步,由財政部門對部門提交的可行性方案進行嚴格的審核,一般項目按照例行程序進行審核,重大項目要組織專家進行評審。
(三)預算績效管理中績效評價指標的設定 按照公共財政的思想,財政支出的目標就是為了提供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但是社會福利水平很難量化,在實踐中必須要找到能夠量化的特定概念和具體數值,以衡量、監測和評價財政支出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即績效評價指標。績效評價指標對于績效評價活動的實質性開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其具有的強烈的價值取向,對于評價對象未來績效的改進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認為,建立科學、完善的績效評價指標是進行預算績效管理的核心環節。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在實施預算績效管理實踐中,由于財政支出的類型繁多,不同類型的財政資金的績效評價指標又各不相同,導致在績效評價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集中在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上。在預算績效管理工作中,如何設計層次齊全、類別豐富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是擺在各級財政部門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績效評價指標的劃分,可以從兩個層面上來展開。一是從評價對象的適用性上來劃分,可以分為共性指標和個性指標。共性指標是每個評價對象都要采用的指標。具體包括預算執行情況、資產配置、使用、處置、財務管理狀況以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等衡量績效目標完成程度的指標。個性指標是根據評價對象的不同特點和目標,通過了解、收集相關資料、信息,來設置特點目標。二是從績效評價的目標和全過程方面來劃分,可以分為初始指標和終極指標。初始指標具體包括投入類指標、過程類指標、產出類指標以及效果類指標。投入類指標,用于反映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時,所投入的各種人力、物力、財力等指標;過程類指標是用于反映政府部門在提供公共服務工程中,質量控制和執行預算計劃的程度等指標;產出類指標是用于反映政府部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數量或完成的工作量等指標;結果類指標是指用于反映一項計劃或一種工作達到預期目標的程度的指標。終極指標包括經濟類指標、效率類指標以及效果類指標。經濟性指標,主要用于反映財政支出項目的成本是否最小化。這主要通過投入類指標、過程類指標和相應的標準進行比較得出。效率類指標,是用于反映一定的財政資源投入是否獲得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最大產出,它往往是通過投入類指標和產出類指標進行比較得出。效果類指標,是反映財政支出項目的產出結果滿足和實現社會公眾的需求、偏好和價值觀的程度。它要求政府不僅要做正確的事,并且做的結果要與社會公眾的預期需要相符合。
五、預算績效管理制度構建
(一)強化認識,樹立績效評價理念 作為一種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績效評價在我國起步較晚,目前仍然處于探索階段。建立與公共財政框架相適應的預算績效管理制度是一個復雜的、漸進的過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各級政府、各部門都要樹立績效理念,重視預算績效管理,并把績效評價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改變原有的“重投入、輕產出”,“重分配、輕管理”,“重數量、輕質量”的粗放式發展方式和管理模式,樹立“要錢不能隨意,花錢要講績效”全新的財政理財觀念。財政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開展對績效評價工作重要性的宣傳,讓財政績效評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讓政府應履行的職能和履行職能的效果為納稅人所了解,努力打造讓社會公眾滿意的“責任政府”和“陽光政府”。
(二)建立專門的預算績效評價機構 要使財政績效評價成為一個經常性、常態化的工作,必須要有專門的預算績效評價機構。結合財政管理的實際情況,建議將財政監督檢查機構改設為財政績效管理機構,承擔績效評價的具體工作。各部門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在部門內部設立專門的績效評價機構,組織開展本部門、所屬單位以及財政支出項目的具體評價工作。同時,為了便于績效評價工作的順利開展,還應該賦予績效評價機構和人員在信息查詢、資料獲取、獨立取證以及行政處罰建議等方面賦予必要的職權。
(三)建立健全績效評價結果應用制度 為了避免在以往績效評價工作存在的為評價而評價的弊端,發揮績效評價工作實效,必須要建立健全科學的績效評價結果應用機制。總體上,要科學制定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管理辦法,具體規定評價結果的運用目的、運用范圍、程序以及權限等內容,從而對政府各項財政支出活動進行指導和規范。具體包括:一是要建立績效評價結果公示制度。有關績效評價結果要提交人大、政府等部門,以供有關領導決策時參考。同時,還應在一定范圍內予以公開,接受監督。二是要建立問題整改機制。各部門應根據部門的績效目標和績效評價結果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和優化本部門未來年度預算支出的規模、方向和結構,提出整改措施并報財政部門備案。三是要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實現預算項目與事業發展目標完成情況掛鉤。對績效優良的,在下年度安排預算時給予優先考慮;相反,對績效差劣的,在下年度安排預算時要從緊考慮。
(四)探索建立預算績效管理信息體系 由于財政績效評價涉及面廣,數據信息量比較大,時效性又比較強,在推行預算績效管理的過程中,就對預算績效管理信息體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是保證預算績效評價工作有效運行的技術基礎。結合我國財政管理的現狀,預算績效管理信息體系的建立要盡快適應財稅信息化發展的要求,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以金財工程為基礎,開發、完善進行預算績效評價分析的系統軟件。二是建立健全預算績效評價的數據庫,并要做好數據信息的分類管理。三是要建立績效評價信息庫。這包括專家信息庫和中介機構信息庫,實現績效評價工作所需信息的資源共享和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