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學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青少年心理學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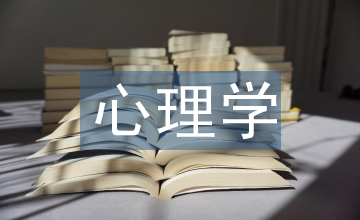
第1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1.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特點
(1)政府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社會支持,并且起步早。
美國政府部門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非常關注。在國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美國就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進行了全國性的探討,2001年美國衛生部提出了青少年信息健康教育的辦法。針對當時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從而可以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并且能夠對已經產生心理問題的青少年進行及時地治療。
(2)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范圍廣、規模大
經過數十年的反戰,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規模已經非常大了。美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分會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最大分支。該分會在學校、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機構中都有他們的工作崗位,很多學校都安排了專門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社會支持的心理學專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機構從學校發展到了社區和家庭。
(3)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手段先進,形式多樣
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非常關注手段的現代化,在為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服務時,通常采用具有較高精度的神經科學研究儀器,比如,腦電記錄儀等。美國為青少年設計了許多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動,比如,學校生活適應、情緒波動不定、人際關系緊張等,利用以上活動能夠有效地治療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并且能夠將學校、家庭、社區緊密地結合起來。
2.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特點
(1)對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目前,中國的經濟不斷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也不斷深入,社會競爭越發激烈。一方面,勞動力的重新組合、過去的社會支持網絡的下降,引起了青少年不同心理應激因素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生活環境的變化和經濟條件的改變導致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不佳、青少年自殺現象明顯增加等問題。中國產生心理問題的青少年不斷增多,而中國心理健康研究相對美國比較晚,目前,我國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給予了非常高的關注,并且將其作為了中國急需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
近年來,有關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學術論文和專業書籍不斷增加,一些教育類期刊或醫學類期刊紛紛開辦了心理教育版。另外,中國各級政府都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社會支持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中國政府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三級甲等醫院設立心理科,大、中、小學設置心理咨詢中心,并且聘任具有專業資質的心理咨詢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工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青少年心理素質具有較大的提升。
(2)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內容不斷豐富
目前,中國并沒有像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一樣的心理健康研究機構,但是我國中科院心理健康國家重點實驗室在心理健康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貢獻。他們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情緒抑制對青少年的環境適應影響、診斷和干預等等,除了這個機構,中國還有許多其他有關心理健康研究的機構。
針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主要研究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①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研究;
②青少年心理健康測量表的編制和借鑒,比如,心理健康測查表、心理健康量表等等。
③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模式的相關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
④青少年腦-認知-心理健康的相關探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學者希望能夠利用核磁共振等先進的技術分析腦的機制,從微觀的角度來進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社會支持。
⑤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疾病的預防。重要通過轉變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來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從而能夠有效地防止青少年心理問題的發生,并且對一些有心理問題的青少年進行及時的治療。
二、美國和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及社會支持比較研究
為了更好地了解中美兩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以及社會支持狀況,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對策,從而提高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我們采用心理健康狀況自評量表和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對中美兩國青少年進行調查,并采取隨機選取、網絡發放的方式進行,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738份,回收698份,其中有效問卷為690份。有350位美國青少年參加了問卷調查,占50.7%的比例;有340位中國青少年參加了問卷,占49.7%的比例。問卷結果利用SPSS11.5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結果如下:
1.美國和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各因子得分的差異比較
分析結果顯示,美國青少年和中國青少年在人際關系敏感、抑郁、強迫、焦慮和總分上存在顯著的差異(p
2.美國和中國青少年社會支持及支持利用度的比較研究
分析結果顯示,在主觀社會支持、客觀社會支持以及社會支持總分上,美國青少年和中國青少年存在著顯著的差異(p0.05)。通過比較不難看出,美國青少年在出現心理問題時能夠獲得較全面的幫助,這和美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的資金投入、心理健康教育機構的完善等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國,心理健康教育還處于初級階段、心理健康教育機構還不具規模,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資金投入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因此,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社會支持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地加強。
三、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對中國的啟示
1.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應不斷提高其社會支持水平。
相關職能部門應加大力度,采取多種途徑,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從而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更具專業化應為今后發展的主要方向,這有利于提高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效率。
2.加大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機構和其他機構的溝通與合作
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應充分地體現職業性、合作性和廣泛性。中國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很多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機構僅僅是形式。隨著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不斷深入,應該意識到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環境健康以及生活態度健康都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應該不斷增強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3.青少年應該增強自身心理健康意識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工作過程中,應該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應該關注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素質,有效地避免青少年產生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重點是使學生能夠清楚地認識自己、善于調節自己,學校、社區和家庭可以聯合起來多組織一些心理健康教育活動。
中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正處于發展階段,還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地解決,中國應該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先進經驗,不斷完善學校、社區和家庭的社會支持系統,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社會支持的力度,從而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質。
參考文獻
[1] 婁文靜,李義安.人格特點影響大學生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的路徑分析.中國學校衛生,2009,30(2).
第2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自我。
分類號 B848.9
1問題提出
心理學關于自我問題的研究始于19世紀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詹姆斯。他在其1890年出版的《心理學原理》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系統的自我理論[1]。20世紀初,Cooley提出了“鏡像自我”的觀點[2]。之后,Mead發展了Cooley的思想,強調社會經驗在自我形成中的作用[3]。而后,由于受行為主義思潮的影響,自我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相對緩慢的時期。到了20世紀中期,自我作為人格的重要研究內容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在各種理論的指導下,自我概念的理論模型及測量工具作為了解自我的主要手段不斷得到完善。比較有影響的有Coopersmith的自尊測量問卷,Piers-Harris的自我概念量表等。但它們多是建立在單維理論模型基礎上,對自我的理解過于簡單,問卷結果很難全面地反映復雜的自我內容。Shavelson等人提出了一個多層級的自我概念模型[4]。在這一模型中,一般自我概念位于最頂層,一般自我概念可分成學業自我概念和非學業自我概念。這一理論對Marsh[5]等產生了巨大影響,在Shavelson多層級自我概念模型的基礎上,Marsh及同事編制了分別適用于青春期前學生、青春期學生及成人自我概念測量的3個自我描述問卷SDQⅠ,SDQⅡ,SDQⅢ。這3個問卷,特別是SDQⅡ成為后來自我測量的主要工具。
我國心理學界近二十多年來對自我問題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并在國外理論及方法的本土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黃希庭、石蓉華、沈德立等人都對自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6~8]。概括起來,自我主要包括自我認知、自我體驗、自我控制三方面內容,它與人的心理健康有著密切得關系。在這些思想和理論的指導下,張靈隱、邊玉芳、曾向等編制了測查自我的量表[9~11],但多是對自我成分部分內容的測量。江光榮從自我與心理健康的關系角度提出了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心理健康素質相關自我結構”模型[12],并據此理論模型編制了自我測量量表。此量表較全面地反映了自我的各方面內容,且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在華東、華北、中南、西南、西北、東北等不同行政區域所屬的23個省市、自治區選取了51399名青少年為調查對象,以同時滿足年級、性別、專業、家庭來源、家庭收入、學校性質等15個背景變量為標準進行嚴格篩選,獲得有效樣本44063(有效率85.70%)例。其中男性21245(48.20%)人,女性22818(51.80%)人;來自城市20569(46.70%)人,農村23494(53.30%)人;重點學校15737(35.70%)人,一般學校28326(64.30%)人;獨生子女19626(44.50%)人,非獨生子女24437(55.50%)人。平均年齡為15.39±2.74歲。調查對象年級分布如表1所示。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江光榮等編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調查表?自我分量表》[12]。在自我一級階層下是包括自我認知、自我評價、自我調控3個維度的二級階層。其中,自我認知由學業自我、身體自我、社會自我、情緒自我4個因子組成;自我評價由自尊和一般自我效能2個因子組成。各因子包括數量不等的條目,量表共有35個條目。被試根據自己的情況對每個條目做出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較符合、完全符合的4級判斷,分別記作1分、2分、3分、4分。各因子得分為所屬各條目得分之和的平均分;二級階層的3個維度得分為所屬各因子得分之和的平均分;自我總分為各二級階層維度得分之和的平均分。對于處于同一年齡階段的個體來說,分數越高,個體的自我越積極,其心理健康素質水平越高。
自我三級結構各維度、因子的α系數分別為:自我認知(0.81)、自我評價(0.76)、自我調控(0.59)、學業自我(0.72)、身體自我(0.70)、社會自我(0.59)、情緒自我(0.62)、自尊(0.66)、一般自我效能(0.65)。以Piers-Harris兒童自我意識量表為效標檢驗該量表的效度,總分相關(0.76)、學業自我―智力與學校情況(0.61)、身體自我―軀體外貌與屬性(0.59)、情緒自我―焦慮(0.59)、自尊―幸福與滿足(0.54),相關系數均達到了p
2.3施測及數據處理
問卷調查使用統一指導語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主試為專業的心理學工作者。使用SPSS 13.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3結果與分析
3.1青少年整體自我得分的分布特點
對44063份有效問卷進行人數分布情況統計得知,青少年整體自我得分在1.05~4.00之間,平均分(M)為2.867,標準差(SD)為0.373,整體自我得分的置信區間(95%)為2.864~2.871。人數分布基本為正態分布形態。偏度值為0.099,峰度值為0.164。分布情況見圖1。
從表中可以看出,整體自我得分大于3.61(M+2SD)的有1340名,占有效調查樣本的3.04%;小于或等于3.61(M+2SD)、大于或等于2.12(M-2SD)的有41948名,占有效調查樣本的95.20%;小于2.12(M-2SD)的有775名,占有效調查樣本的1.76%。
3.2各年級青少年整體自我水平及年級差異
各年級青少年整體自我得分的統計結果見表3。
從表中可以看出,青少年整體自我的得分從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一年級下降明顯,高中階段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略有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89.791,p
3.3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認知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自我認知得分的平均數為2.777,標準差為0.376,青少年自我認知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773~2.780。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認知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4。
從表中可以看出,年級變化表現為從小五到高一下降明顯,高一到高三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略有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136.285,p
3.3.1各年級青少年學業自我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學業自我得分的平均數為2.555,標準差為0.530,青少年學業自我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550~2.560。各年級青少年學業自我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5。
從表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學業自我得分從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一年級下降明顯,高中階段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略有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321.546,p
3.3.2各年級青少年身體自我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身體自我得分的平均數為2.725,標準差為0.564,青少年身體自我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720~2.730。各年級青少年身體自我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6。
從表中可以看出,各年級青少年身體自我得分波動較大,小學五年級、初中三年級、高中三年級得分較高,初中一年級、高中一年級得分較低。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8.842,p
3.3.3各年級青少年社會自我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社會自我得分的平均數為3.019,標準差為0.464,青少年社會自我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3.015~3.023。各年級青少年社會自我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7。
從表中可以看出,青少年社會自我的得分從小五到高一表現為明顯下降,高一到高三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略有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12.632,p
3.3.4各年級青少年情緒自我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情緒自我得分的平均數為2.808,標準差為0.594,青少年情緒自我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803~2.814。各年級青少年情緒自我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8。
從表中可以看出,青少年情緒自我得分從小五到高三下降明顯,只在高三到大學階段有一定程度的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114.141,p
3.4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評價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自我評價得分的平均數為2.845,標準差為0.461,青少年自我評價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840~2.849。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評價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9。
從表中可以看出,自我評價得分隨年級的增長明顯下降。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39.280,p
3.4.1各年級青少年自尊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自尊得分的平均數為2.841,標準差為0.563,青少年自尊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836~2.846。各年級青少年自尊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10。
從表中可以看出,青少年在自尊得分上的年級變化情況是,從小五到初一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從初一到高三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再次有明顯的下降。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28.226,p
3.4.2各年級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得分的平均數為2.848,標準差為0.510,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得分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843~2.853。各年級青少年一般自我效能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11。
從表中可以看出:一般自我效能得分隨年級的增長下降明顯。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39.139,p
3.5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調控水平及年級差異
青少年自我調控得分的平均數為2.980,標準差為0.520,青少年自我調控平均數的置信區間(95%)為2.975~2.985。各年級青少年自我調控水平的統計結果見表12。
從表中可以看出,自我調控的年級變化表現為從小五到高一明顯下降,高一到高三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有一定程度的回升。方差分析表明年級的主效應顯著,F(7,44055)=60.030,p
4討論
4.1青少年整體自我的分布特點
整體自我或可稱之為自我,它由自我認知、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構成。整體自我水平的高低意味著自我的整體功能的差異。整體自我水平越高不僅表現為主體自我對客體自我的認識和評價越真實,與客觀評價越一致,而且表現為對自己的把握和控制也越強。對同一年齡的個體來說,整體自我分數越高,個體的自我越積極,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以均值加減兩個標準差來區分的高、中、低得分水映了自我發展在真實性、客觀性和控制性上的差異表現。從調查結果上看,中間以上水平的人數居多(98.24%),說明絕大多數青少年的自我發展是不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的自我因素是好的。在肯定這一情況的前提下,對分布在兩個極端的少部分對象必須給以足夠的研究和關注。其中對位于平均數加兩個標準差以上較好的(3.04%)那一部分有必要進行進一步探究,找出有利其發展的因素,為提高心理健康素質提供依據;而對那部分較差的對象(1.76%)應給與更多的關注,及時查明原因,及早進行干預,以避免更為嚴重問題的出現。
4.2青少年自我的年級特征
青少年時期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此階段個體的身心發展不僅快速而且其社會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作為人格核心內容的自我,它的變化特征是個體身心發展的整體規律在自我方面的具體反映,是生理、心理的內在因素與特定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調查結果表明,整體自我、各維度、各因子(除身體自我因子外)的年級變化特點具有普遍的一致性,總的看來具有先隨年級增長下降,大學階段有所回升的特點。這種變化特征的出現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它反映了個體在整個心理發展過程中的一般規律。青少年個性的發展,思維水平的提高,社會角色的改變等與自我的年級變化特征是協調一致,相輔相成的關系,自我的年級變化特征是與其它心理機能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小學五年級階段的兒童對自我的認識多來源于外部,老師、家長甚至同學的標準起著重要作用,這種評價帶有明顯的不成熟、不穩定的性質,自我控制能力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盲目樂觀地看待自己,評價標準的易變,較少約束的內外在環境,都可能是高自我得分的原因。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增加,社會交往的擴大,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認識標準,思想也日趨成熟、穩定,到了大學階段應該說基本形成了客觀、穩定、成熟,以內在標準來看待自己的認識和評價,對自我控制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且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雖然青少年自我的年級變化特征中小學五年級得分較高,但自我的“他律”特征明顯。隨著心理機能“他律”向“自律”的變化,青少年自我的年級變化特點與其一致地表現出“自律”的特征。分數的差異只是量上的表現,正確理解自我的年級階段特征還必須從質的角度加以分析,進行橫向的比較,這樣才能夠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自我變化情況;另一方面,自我結構的年級差異可能是這種趨勢的又一個內在原因。隨著自我研究的日趨深入,自我在年級間的結構差異、學科差異、性別差異等問題得到揭示[13~15]。不同年級間自我構成成分的不同或權重的改變,不同學科間自我水平的差異,不同性別間的不同變化特點等都可能造成自我在整體、各維度、各因子的不同變化規律。正是在這樣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過程中,青少年的自我的年級變化表現出了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特征。
5結論
青少年自我的整體表現是好的,對極端個體的自我狀況應當給以進一步研究和關注;青少年自我的年級變化特點表現為,小學五年至高中一年下降明顯,高中階段變化平緩,高三到大學階段略有回升。
參考文獻
1 James W.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Harverd University. 1890
2 Cooley H C.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2
3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2
4 Shaveson R J. Hubner J J. Stanton G C. Self-concept: Validation of construct interpreta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6, 46: 407~441
5 Marsh W H, Byne B M, Shavson R J. A multifaced academic self-concept: It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8, 80(3): 366~380
6 黃希庭, 鄭涌. 當代中國大學生心理特點與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7 時蓉華. 現代社會心理學.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
8 沈德立, 馬惠霞. 論心理健康素質. 心理與行為研究, 2004, 2(4): 567~571
9 張靈隱. 初中生學習自我控制特點的研究. 博士論文. 指導教師: 黃希庭教授. 2001, 6
10 邊玉芳. 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編制與應用. 博士論文. 指導教師: 金瑜教授. 2003, 3
11 曾向. 青少年身體自我及其與自我價值感關系得研究. 碩士論文. 指導教師: 黃希庭教授. 2001, 6
12 江光榮, 胡博.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調查表》自我分量表的編制. 心理與行為研究, 2006, 4(2): 95~100
13 Shapka J D, Keating D P.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elf-concept during adolesc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2005, 37(2): 83~96
14 Liu W C, Wang C K, Parkins E J.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udents′ academic self-concept in a streamed setting: The Singapore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2005, 75: 567~586
15 Hewitt M P. Self-evaluation accuracy among high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instrumentalis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2005, 53(2): 148~161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A STUDY OF
MENTAL HEALTH-RELATED SELF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DOLESCENT
Zhou Tiemin, Yin Guo′e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cademe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300074)
Abstract
第3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寄宿制 青少年 依戀 心理健康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2-0204-02
1.以往對父子關系與心理健康關系的相關研究
國外關于父子關系比母子關系更具預見性[1]這個問題從以下幾個角度有研究:(1)行為問題,(2)個性和心理調適能力發展問題,(3)物質濫用問題,(4)心理障礙問題,(5)品行不良問題,(6)心理健康問題。另外,耶魯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表明,由男人帶大的孩子有更好的學習成績,智商更高,在社會上更容易成功[2]。國內郭文斌等人的研究認為:父親撫養組的子女行為問題總分最高,其撫養下的子女行為問題因子檢出率所占的百分比最高項目最多[3]。李丹等人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4],兒童同伴游戲的豐富性水平與父親所報告的鼓勵成就成正相關,兒童同伴游戲的豐富性水平與父親所報告的鼓勵的獨立撫養方式成正相關。陳會昌等的研究結果顯示[5]:在控制了主效應后,父親的拒絕和控制可以負向預測兒童的助人行為而父親的接受性能正向預測兒童的焦慮-抑郁行為。從上研究中可見幾乎沒有父親依戀對寄宿制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所以本論文主要從這個方面進行一些研究。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從某普通初中、高中、大學選取寄宿制學生451人集體問卷調查,被試的年齡在12-20之間。
2.2研究工具
父母與同伴依戀問卷(IPPA)中文版,師生依戀問卷,心理健康臨床癥狀自評量表SCL-90。
3.研究結論
3.1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心理健康的回歸分析
表1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軀體化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2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強迫癥狀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3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人際關系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4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抑郁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5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焦慮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6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敵對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7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恐怖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8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偏執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9寄宿制青少年依戀對精神病性的多元回歸分析
由以上表可知,寄宿制青少年中進入回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量都有父親依戀F(1,415)(p
4.討論與分析
對以上研究結論進行進一步分析,我個人認為形成原因有以下幾點:
4.1中國的家庭文化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一般家庭都認為父親應該主外,母親應該主內,父親是子女的人品、人格、理想、規范的化身,母親主要負責子女的物質保障、情感滿足、飲食起居等,所以寄宿制青少年把父親作為自己的生活的導師,人生規劃師,父親的存在對子女的生活方式、性別角色規范、態度和價值觀具有重要影響,父愛的存在為孩子心理發展、個性發展提供了積極平臺。
4.2性別差異
男性與女性相比絕大多數男性身才高大魁梧,皮膚網結構比較粗大,體毛比較多,做事果斷干脆,性格開朗活潑,具有男子漢陽光之氣,從外形以及性格表現上就能給孩子們安全感,能給孩子們積極的心理支持,所以如果父親能在寄宿制孩子們生活中給予鼓勵,給予安慰,給予溝通,對孩子們心理發育有相當的益處。
4.3經濟來源
對于寄宿制孩子們來說,他們很多家庭都是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在家料理家務,他們的個人消費甚至整個家庭的經濟主要費用都來源于父親的勤勞的勞動所得,所以孩子們認為父親就是家里的天,家里的支柱。所以父親帶給孩子們心理安全感那是母親代替不了的。
4.4父親的心理素質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父親一直被認為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以及精神支柱,在他們心中他們自己也認為就應該努力掙錢讓家里人過上好日子,讓別人認可他們的社會地位,更希望得到家人以及社會的肯定,所以他們的壓力遠遠大于母親,他們絕大多數沒有時間像母親和老師那樣耐心教育孩子,即使他們努力不在孩子面前表現,但孩子對父親這種狀態有一種神奇的融合和感知,這也正好反向預測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父親們自身也得提高認識,改變觀念,清楚自己對孩子心理發育的重要性,再忙也要抽時間陪孩子,耐心的教育孩子,別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4.5父親的文化素質
在中國家庭結構模式中,男性還比較大男子主義,在擇偶時都愿意選擇不如自己文化水平高的女性,所以絕大部分家庭是父親的文化素質高,他們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很高,他們也積極的教育子女,希望他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相反,母親文化素質較低,她們沒有更多的文化知識去很好地教育子女,這也能正向預測父親依戀對孩子的心理健康影響。
所以,在以后要指導或告誡寄宿制學校多鼓勵父親來學校開家長會,多鼓勵父親與孩子溝通、談心,多給孩子做正面榜樣,這非常有利于孩子在以后成長中心理健康發育。
參考文獻:
[1]周波.美國兒童發展中父親影響作用研究綜述[J].當代青年研究.2004,2.
[2]朱啟勝.家庭教育方法探斷[M].東方出版中心.2001(1) 67-68.
[3]郭文斌等.家庭中的親子撫養方式對子女行為問題的影響[J].甘肅社會科學.2002(1)69-70.
[4]李丹,崔麗瑩等.6-8歲兒童同伴互動及與父親教養方式的關系[J]. 心理科學,2004,27(4):803-806.
[5]陳會昌等,父親教養態度與兒童在4-7歲間的問題行為和學校適應[J].心理科學,2004,27(5):1041-1045.
第4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性,悄悄地影響著人的心理健康,伴隨著人的一生。
性意識的覺醒,始于青春期。當身體的變化浪潮般涌來的時候,給心理帶來的沖擊是可想而知的。這個浪潮有時來得太猛烈了,使得心理無法駕馭這種生理變化。有多少個小心靈或惶恐不安,或快樂歡欣,或害羞躲避,或羞愧難當。他們開始留意自己的長相、儀表、一舉一動,他們渴望得到異性的關注和肯定,對自己喜歡的異性更是渴望身體上的接觸。對生理變化滿意的青少年,會產生自豪、積極、健康的心態,反之會產生自卑、消極、不健康的心態,對以后的心理發展影響深遠。有一個高一男孩子,因為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及人生發展教育,沉迷于性中無法自拔,逃學,曠課,在網吧看,夜不歸宿,學業一塌糊涂。來自老師的搖頭嘆息、放棄,以及同學的側目,使他無處安放的青春更加孤獨和困惑,為了尋找快樂和存在感,他變得更加沉落。還有的青少年因為生理變化而產生的過于敏感和自卑,導致內心異常脆弱,一旦有導火線出現就會爆發出各種心理障礙或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抑郁癥、強迫癥等。
過了青春期,性與心理的浪潮雖變得平緩,卻更加深厚。有對中年夫婦猶豫要不要離婚,離婚的理由是不愛,心里不接納對方,性生活幾乎沒有。猶豫的理由是因為孩子。問及既然不愛,當初為何結婚生子?答曰那個年代男女授受不親,很少接觸,為了體驗性的快樂而擁抱在一起。后來懷孕了,不得不結婚。結婚后才發現所謂男女之愛不過就是那么回事,想回頭,卻發現青春已逝,何況有個孩子拖累。
第5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人物檔案
袁茵,副主任醫師、高級心理咨詢師、四川大學精神病與精神衛生碩士、四川省醫學會精神專委會委員、四川省心理學會醫學心理專委會委員,現任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科教科副科長,成都市汶川地震災后心理重建辦公室負責人,成都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詢中心副主任。2008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部局授予“抗震救災醫藥衛生先進個人”,2007年度被評為“第二屆四川省未成年人保護先進個人”,2007年度被評為“2004―2008年度成都市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
苦行僧?樂在修行中
7:00 出發上班。
8:00 與夜班值班醫生進行工作交接。
8:15 整理辦公桌,打掃辦公室,進行就診前的準備。
8:30―12:30 開放門診,進行心理咨詢和科研工作。
14:00―17:45開放門診,進行心理咨詢、巡房、科研工作。
20:00 看書充電,繼續進行科研工作。
這是袁茵普通而又充實的一天。袁茵家里沒有安裝光纖,因為她幾乎從不主動看電視,所有的信息都來源于網絡和書籍。比起電視,她更樂于沉醉在書籍或主題電影里。“電視會讓人上癮,忘記時間概念,我現在的工作狀態和生活狀態不允許松懈,必須有目的有計劃地一步步實踐。”工作日里一天24個小時,除了午休和晚休,袁茵所有的時間和神經都圍繞著“工作與科研”打轉。在香港刑偵片和各類懸疑美劇里泡大的80、90后們,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個“心理學達人”的夢。從弗洛伊德到榮格,心理學被渲染出神秘和高端的氣氛,但并非看完一本《夢的解析》或幾本《心靈雞湯》,你就真的進入了這門學科。學習心理學的過程漫長而辛苦,就像袁茵的工作表一般。
“選擇心理學,喜歡自然是誘因。但真正走上了這一條路,才發現僅有喜歡是不夠的。你必須具備一定的基本素質,細膩的分析能力和敏銳的洞察力,一定的情感表達能力,堅持的耐力,抗枯燥的毅力,特別是永葆學習狀態的動力。”在心理學這條路上走了14年的袁茵,猶如印度文化中的苦行僧,一面抵抗著枯燥和漫長的修行,一面享受著感知和進步的喜悅。坡曾在《與侄孫元老》里寫道:“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即使已經發表了數篇心理學論文,屢次獲得市級、省級醫學科技獎,但袁茵仍然執著于修行,在枯燥學習與平凡生活中,保持著超然自得與不改其度的統一。
白衣天使?對每一個病人微笑
在很多人的意識里,提到成都的四醫院,便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感覺:精神病院,閑人免進。這種意識更多地表現在對精神病人的誤解上。“這絕對是偏見,極大的偏見。”袁茵激動地提高了語調,“為什么只看到他們精神上的問題,卻忽略了他們病人的身份呢?精神病人與其他的各類病人一樣,都是弱勢群體。在他們發病時,是有可能傷害到其他人,但實質是,他們是急需要關注和關懷的病人,是病人!”
在袁茵以及四醫院每一個醫生的眼里,每一個精神病人都像孩子一樣,需要更多的愛心和耐心去幫助他們戰勝病魔,重獲新生。身體的痛楚可以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快痊愈,而精神的痛楚,卻不似自然界里秋天落葉,春天發芽那樣在生機中循環復蘇。“精神的概念極廣,所思所想,甚至信仰,都屬于精神范疇。你可以通過手術修補傷口,但精神的創傷,更多需要愛心和情感去治愈。”
5?12大地震發生的一瞬間,袁茵也曾陷入極大的恐慌,然而數秒時間內她便反應了過來。在這樣的時刻,神經敏感脆弱的病人們,更需要得到幫助和保護。劇烈的搖晃中,她飛奔下樓,和同事們一起開始疏散病人,有條不紊地將病人一個個帶到安全的院落中,來不及給家人打個電話,只顧著繼續安慰病人,平息他們的恐懼。
“社會在進步,人們對精神病人的觀念和態度也有了轉變。排除遺傳因素,從根源上減少正常人心理問題的途徑,還是人文關懷。試著對你身邊的每一個人微笑,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努力為家人創造溫馨和諧的生活環境,這不僅是心理醫生的工作,而是每一個人舉手之勞的義務。”
心理醫生?治愈三步曲
第一步: 換位思考,站到對方的角度,理解對方的處境。
第二步: 恰當的時候做引導性的建議,讓對方說出心里話,建立咨詢關系。
第三步: 采用合適的技巧進行引導,逐步實施引導計劃。
三步曲,看來簡單,卻是最體現心理醫生功力的部分。目前袁茵的工作主體,并不是參與已確定病癥的精神病人的治療康復,而是進行“提前防御”工作,即心理咨詢。因此,研究并實踐這三步曲是她目前最核心的工作。迄今為止她壓力最大的一次挑戰,便是汶川大地震后進行危機干預的“精神重建”工作。
地震發生后,大量的傷員從重災區轉移到成都的各大醫院,由袁茵領隊的心理咨詢隊開始深入到各個醫院和各個災區,對病人進行“危機干預”和心理撫慰。一個截肢女孩和一個失去雙胞胎女兒的母親,令袁茵尤其揪心。
截肢的小女孩在手術完的前幾天,表現出了異于常態的安靜和鎮定,甚至會主動去安慰其他傷者。在普通人眼中,這當然是一個積極的好現象。而袁茵則敏銳地發現,小女孩的表現是極力壓制內心痛苦的反應。她特別提醒主治醫生注意女孩的情緒變化和日常舉動。果不其然,僅僅幾天之后,女孩便承受不了強大的心理壓力,以暴躁的形式極端地爆發。脾氣乖張,不再與任何人交流,開口便是謾罵,憤怒地砸碎了身邊所有的物品。面對情緒失常的女孩,袁茵并沒有直入主題,而是從問詢她之前的生活情況,討論她的興趣愛好開始,任由對方不理不睬,袁茵時而溫柔,時而緩慢:“我明白你的感受,每一個正常人遭受這種災難,都很難接受。所以,你盡管發泄你的痛苦,但我會一直陪著你。”伴著女孩一陣撕心裂肺的痛哭,袁茵知道,她心中的苦痛開始用淚水的形式發泄,這便是第一步的成功。“女孩哭了很久,抓著被子埋頭痛哭。不久,她向我說出了心中最大的顧慮――前途與未來。”自然,袁茵許不了女孩一個切實的未來,但卻給了女孩重新憧憬未來和正視生活的勇氣:“你可以放棄,你可以發脾氣,但是如果你不努力,沒人可以幫你。”
簡單而樸素的語句,因為把自己與對方放在了平行線上,便有了直入心靈的力量。面對截肢女孩如是,面對失去雙胞胎女兒的40歲母親,同樣如是。一個被拐賣到四川的女人,和一個外地農民工結婚后生下的可愛的雙胞胎女兒,在地震中雙雙遇難。不幸發生后,老公一去不回,家里只剩下她一個人。拒絕救援,拒絕交流,拒絕參加社區活動,孤立無援的女人處在身體與精神的崩潰邊緣,一會兒暴躁地謾罵,一會兒傷心地痛哭,始終不肯對袁茵開口。袁茵仍然從生活入手,只字不提災難,親切地噓寒問暖,更拿起了一雙孩子的照片,微笑著撫摸著那些定格的容顏:“真的很可愛。”僅一句話,失控的母親突然安靜下來。她開始不斷地翻出女兒的衣物、照片、生前的各類用具,并主動給袁茵講起了孩子生前的故事,一邊說,一邊泣不成聲。整整3個小時,女人哭干了眼淚,也真正冷靜了下來。“這位母親的遭遇,是地震中千千萬萬家庭的縮影和寫照,這個時候一味地給他們描述美好未來,是不明智的。只有先解開心結,讓她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才有基礎說以后。”
孩子王?永遠懂得多一點
袁茵所在的青少年心理咨詢中心成立于2005年,彼時的中心還設在醫院門診的二樓。整個構造和布置,都出自袁茵的創意。兒童咨詢室里,彩色的桌椅別添樂趣,一些常識的心理問題也以卡通人物的形式掛在1米高的位置;發泄治療室里,大紅的墻壁,一個大沙袋懸掛在房間中央,極具“挑釁”意味。如今的心理咨詢中心已經被改造成一座獨立的三層小樓,設置了一個心理測評中心、4個一對一的咨詢室和一個團體咨詢室。每一間獨立咨詢室,都被設計得安全、安靜而典雅。而團體咨詢室里,兩個大沙盤,和書架上擺放的各種玩具模型,尤其引人注意。
“沙盤引導法是目前較先進的心理治愈法,當孩子不愿意開口或年紀太小無法表達內心的想法時,我就讓他們選擇喜愛的玩具,通過在沙盤上擺出各種圖案的方法,去認識和了解他們。”在袁茵受理的各類青少年心理問題咨詢中,最普遍的便是“親子矛盾”。每一天,咨詢中心要接待10余名青少年,逃學、自閉、逆反、人際交往障礙、離家出走……多數誘因都來自于“親子矛盾”。“最近某網站的小組搞了一個‘80后反父母’活動。并且,有一個小組的成員的家長全是小學教師,而那些孩子們卻在網上說盡了父母的壞話。”作為一個17歲女兒的母親,袁茵對自己表現出了高度的自信,“因為我懂得孩子的需要啊!”
叛逆、自閉、暴躁的少男少女坐在袁茵面前,不用多久便蛻變為“話癆”和乖寶寶,情不自禁地把不愿意和父母交換的心事,一股腦告訴這個比自己大了30多歲的不像醫生的醫生。“通常情況下,面對孩子的反常態度和行為,家長只會站在監護人的角度說‘NO’!但我會對他們說‘YES’!認真聆聽他們的所有不滿,并且做他們強大的后盾。”讓孩子不排斥你,第一步便是學會聆聽和鼓勵。但要讓孩子信任你,接受你,尤其接受一個年齡差距巨大的醫生的建議,那就需要更多心思。
“我隨時保持著孩子喜歡的我知道,并且還比他們多懂一點點的狀態。”與女兒打成一片,成為袁茵探尋“青春秘密”的最直接方式。不愛看電視,但絕對要抽時間陪女兒看電視。快男快女、偶像劇美劇、音樂頒獎禮、明星演唱會都會關心,絕對掌握一手火熱資訊。袁茵曾在一次講座中,以周星馳的搞笑照片作為結束語,這便被她歸功為陪女兒看電視培養的潮流感。網絡更不用提了,“80后反父母”網上活動怕是很多80后本身都還不知道的新聞呢。而袁茵最享受也是最獲益良多的方式,還是看電影,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的青少年成長電影。《歌舞青春》三部曲,宮崎駿的動畫片,袁茵是絕對的達人。而一些普通家長排斥的灰,諸如《大象》、《戀空》和《朱諾》,則更是袁茵的心頭好。“越是現實得可怕的電影,越是國內家長不能接受的故事,越能讓你有危機感和具備超前性。”當某些少年以“懷疑自己的性取向”為理由來尋求幫助時,袁茵的一句:“你知道它的全部意義和表現特征么?”便讓對方啞口無言。而當袁茵滔滔不絕地拋出理論與故事融合的各類事實、事例和數據后,坐在對面的少年蹭地站起來:“啊!我正常得很嘛!我好傻哦!”兩人頓時一起大笑。
第6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心理成熟;表征;內隱化
縱觀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國內有關青春期心理的論述,“閉鎖性”作為青春期的重要心理特征的論斷幾乎比比皆是。我們不妨將此類觀點稱之為青春期心理特征的“閉鎖說”。它不僅在心理學專業領域內有較大的影響。而且還波及到對青少年研究及有關實際工作的諸多方面。這種現象固然有社會文化歷史的因素,但也應看到我們對于青春期心理研究還存在著某些不足。對于青春期心理成熟現象重新審視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青少年的教育和社會工作乃至家教都不乏現實指導意義。
一、對于心理成熟表現的誤解及其由來
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世界最早提出“閉鎖說”的是德國教育哲學家斯普蘭格(Spranger·E)。他在其1924年出版的《青年心理學》中提出了“閉鎖性”是青春期心理的主要特征。他將青春期的這種特點表述為:人們到了青春期有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不再像兒童時期那樣直爽、率真,即使對最親近的人也很少吐露真情,表現出顧慮重重,不愿與他人多接觸。國內諸多相關研究及著述在涉及青春期心理特征時對此基本予以認同。此類的表述如:林崇德主編的《發展心理學》在論及成年初期心理的兩極性中將“閉鎖性和開放性”作為青春期心理特征之一;鄭日昌主編的《中學生心理診斷》中對此的陳述是:“心理學家大多把‘閉鎖性’看成是中學生時期最顯著的心理特征。中學生不再像孩童時代那樣天真,毫無顧忌地向父母或師長敞開心扉,這種‘閉鎖性’是中學生的‘成人感’和‘孤獨感’以及認識能力的提高聯系在一起的。”呂靜等編著的《兒童發展心理學》也將“閉鎖性”作為青春期的重要心理特征;《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卷》對于青春期的心理特點的看法是:“一方面會產生反抗情緒,渴望被人理解,另一方面又企圖把自己的內心閉鎖起來,引起白相矛盾和協調困難,等等。”楊麗珠主編的《兒童心理學綱要》在將“閉鎖性”進行了解釋:“所謂閉鎖性是指人的心理活動具有某種含蓄、內隱的特點,它相對于人的外部行為表現與內部心理活動之間的一致性而言。”
實際上,青春期的孩子們并非與世隔絕或封閉,只要看看他們與此有關的表現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傳紙條.發短信,如醉如癡的上網、頻繁的約會、廣泛的交友.這些人際交往活動在青春期表現出空前的活躍,就連“閉鎖說”的依據之一記日記實際正好表明這個時期的孩子們有交流的需要,怎么能說青春期的孩子們的心理是“閉鎖”、“隔絕”呢?最先提出“閉鎖說”的斯普蘭格本人也承認:“在人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像青年時期那樣強烈的渴望被理解的時期了。”
其實,斯普蘭格在提出青年心理閉鎖性的同時,也看到了與此相矛盾的事實,即青年強烈的交往和交流的愿望,但是,斯普蘭格沒有對此進行正確的解釋。實際上這正是心理活動缺乏相應的圖式才出現的現象,這點已經為后來的認知心理學的有關研究所證實。但是當時心理科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似乎還沒有出現足以解釋這種現象的范式,于是,“閉鎖說”作為心理學發展的歷史局限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對于閉鎖性的認識過程
對于閉鎖的認識,人們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首先,由于人們社會知覺中刻板印象的影響。當孩子們的心理發展出現成熟時,很多成年人對此仍然視而不見,心目中依舊用過去形成的固有印象來認識變化了的對象,仍然將他們看作是小孩子。正是這種殘留印象如變色鏡一樣使人們不能正確科學地認識青春期時孩子們身上所發生的積極變化。進人青春期的孩子們所表現的不愿與人隨意交往不再天真坦率,并非什么“閉鎖”或自我封閉,而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心理現象。
刻板印象很容易帶來溝通障礙。青少年由于自我意識成人感的出現而希望自己被接納為成人或合格的社會成員很反感繼續將他們當作小孩子看待。于是,成人們就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力將溝通障礙推到孩子們身上,“逆反”、“閉鎖”“反抗”等都是這種情境的典型用語。
其二,“閉鎖說”的出現來源于對青春期心理現象的非科學解釋,將青春期孩子們的正常心理發展現象視為系統的“噪音”、“偏差”。基于這種邏輯前提,對于青春期心理特征的認識存在五大誤區。
1.對于青春期交往對象、內容和方式的變化缺乏正確的認識。實際上,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們是非常渴望與人交流。但正如許多研究指出的那樣,此時的孩子們交友與以前大不相同:對于朋友標準、交往方式、交往內容等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既是他們心理上成長的表現,也是心理成熟的需要。
2.不能正確認識青春期孩子們對于外部評價的關注。進入青春期,青年們不僅對外部世界有了更加廣闊和深刻的認識,而且還發現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與自我意識密切聯系的自我評價也相應發展,體現為青春期所特有的以至于對后來一生具有重大影響的自尊。這種對于外部評價的關注,使青春期的孩子們心理活動呈現為閉鎖性。
3.閉鎖性是青春期個體建構自我所必需。進入青春期,孩子們身上出現了艾里克森所主張的“自我同一性”危機。自我同一性是指個人對自身的本質、信仰和一生前后一致的比較完善的意識,反之就是角色混亂,表現為個體對生活中的角色的迷失與困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解決危機的最主要方式是主體通過反思或反省等心理活動對自我重新建構,而認識自我的有效方式就是將視線轉向自己的內部世界。
4.對青春期的獨立意識的誤解。獨立性的出現是社會和心理成熟的標志之一,表現為試圖擺脫成人的監管,獨立地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對于他人的建議,不再無條件地接受,但這也并不意味著一味地拒絕。實際上,青年們對于那些經過思考后認為有道理的意見或建議還是愿意接納的。
5.對于社會成熟的誤解。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們已經對社會現象有了一些認識。按照心理學家班都拉所指出的“觀察學習”觀點,此時的孩子們已經或多或少地明白,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主張和觀點不能不經考慮不區分地對別人講,做事必須考慮可能帶來的后果,表明責任意識的發展,這是社會適應成熟的表現。
心理活動的這種相對于外部活動而言的含蓄、內隱的變化及其中的矛盾現象反映了青春期孩子們對于適應內外環境的努力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其心理和社會適應成熟的表現。因此成人和社會應當正確理解并給予他們必要條件以促進其正常發展。其實在心理學界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
第7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家長劉女士:
孩子有了自己的秘密
42歲的劉女士是一家公司的會計,女兒16歲,今年上高一,學習成績還不錯。
“女兒是個乖乖女,是全家人的寶,以前孩子在學校有什么新鮮事總是和家人訴說,現在孩子上高中了,個子也一下子長高了,慢慢有了自己的秘密,不愛和家人交流了,高興時能和你聊聊身邊的事,不高興了問什么都不多說。去年,女兒看到好多同學都有了手機,也非常想要,和她爸和我說了好多次。我們做家長的也覺得孩子還小,正是學習的時候,要手機沒什么用,就沒有滿足她,沒想到孩子因為這件事還和我們慪半天氣。今年我們就和女兒承諾,要是能考上重點高中就先給她買個手機。女兒很爭氣,通過努力考上了重點高中,于是暑假我就給女兒買了個手機,不過女兒有了手機后,把手機設上密碼,QQ也換了密碼,房間的抽屜也上了鎖。我真擔心孩子因為這些分了心,更擔心為此影響孩子的學習。不過孩子還是很聽話的,不讓她做什么,雖然很不情愿,但是很少頂撞我們。開學前一天,同學約她出去玩,她爸爸知道后,不讓她去玩,讓她準備迎接開學。她雖不高興,但也沒有出去玩,氣得一天也沒有和她爸爸說話。”
“這些可能都是孩子青春期的表現吧!孩子學習壓力大,逆反心理也很強,我們做家長的要好好引導,讓孩子健康成長!”
孩子毛毛:
想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毛毛乖巧伶俐,在家不僅得到家長的寵愛,在學校也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采訪毛毛,她卻不好意思地在玩弄手里的小熊。
“我是家里的小公主,每天快快樂樂,什么事都是爸媽給安排好的,不過每逢節假日,爸媽給我報的各種特長班是應接不暇,加上學習的壓力,看到別的同學玩,心里也怨恨過爸媽。不過我對特長班還是比較感興趣,學什么也學得比較快,爸媽對此還是比較驕傲的”。
“不過慢慢地我不愿意主動和爸媽交流了,有時候他們會強迫我去按照他們一些想法去做,我也想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自己的空間。像人家外國的孩子,有什么想法總能得到家長的支持和鼓勵。”
“尤其上了初中以后,我愿意和同學們交流,因為我們有共同語言,和爸媽有代溝。同學們都有了手機,平時用手機交流,還可以促進學習,他們卻怕我有了手機會影響學習。真是郁悶!不過平時我還是挺害怕我爸媽,也不想讓他們為心。總之,我長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也會安排好我的學習和生活,開心快樂地過好每一天,讓所有愛我的人放心。”
專家簡介:
王宏,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山西省心理學會會員,太原十二中心理教師,曾近20篇,其中獲國家級論文二等獎兩篇,其它論文獲山西省一等、二等獎。在四川省汶川發生地震后主動到什邡市洛水鎮做心理危機干預。
家長張先生:
孩子是我心頭的痛
張先生,46歲,省城某媒體記者,兒子今年15歲。提起孩子,張先生一臉的無奈:“怪我們做父母的沒有教育好,孩子今天這樣是我一生的痛。”
在孩子10歲時我便與老婆離婚了,孩子跟著我。開始孩子學習不錯,在班里名列前茅,我便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孩子身上,每天接送孩子,既當爹又當媽。但是孩子的性格慢慢有了變化,沉默寡言,問他什么也是哼哼哈哈。在孩子上六年級時,我因工作經常出差,放松了對孩子的管教,結果老師不斷地打電話給我,說孩子經常缺課。我非常生氣,便打了孩子一頓。沒想到孩子一星期沒有回家,也沒有去上課,找到他時是在一家網吧里。
從那以后,我也不再管孩子。孩子成了網吧里的常客,上學那就是想起來就去。結果學校讓我給孩子轉學。沒有辦法,我找關系又給孩子找了一個寄宿制學校。沒想到好了幾天,孩子又開始逃學……
有些事情說出來都可笑,因為孩子,好多警察都和我非常熟了。有時候,孩子上網到深夜,身上沒有錢又回不了家,他就打“110”,說自己回不了家了。警察把他送回家后經常把我教育一頓,就這樣隔三岔五警察就會來我家一趟。
孩子剛上初中一年級就不想上學了,告訴我,什么也學不會,坐到教室就頭疼。我也和他談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給他講,沒有辦法。孩子輟學后,那就更是瘋玩,我工作也忙,不再管他。經常和一些比他大的孩子玩,上網打游戲、聊天。沒有錢了就到我單位找朋友、同事5元10元地要。時間長了我也就麻木了,有時候我們坐在一起聊的時候,我也就不再把他當成孩子,反而像是個朋友。
有一次我下班回到家,一開門看到家里有一個女人,30歲左右,孩子把我叫到一邊笑著說,這是給我介紹的對象,鬧得我哭笑不得……
現在,他瘋玩了幾年后,覺得也沒有什么意思,我就又給他聯系了一所技校,讓他學點技術,將來也算有一技之長吧!雖說我的孩子現在剛15歲,可他的想法和心理年齡卻很成熟。我真是擔心他這樣長大會不會對將來有影響。
孩子張明:
上網是我最大的樂趣
和張先生聊完,記者又單獨和張先生的孩子張明(化名)進行了接觸,雖說張明剛滿15歲,但是沒有了青少年的那種羞澀和稚嫩,而是一臉的成熟和狡黠。剛一見面,張明便對記者說:“我叫你哥吧!叫你叔叔我不習慣。”
“我爸媽離婚后,對我的打擊很大,看著我爸每天為勞,好一段時間我都覺得壓抑,學習的興趣也慢慢消退。后來,我爸因工作也經常出差,同學們知道了我爸媽離婚,經常在我身邊唱‘沒媽的孩子像根草’。我一下子崩潰了,對我爸、對家、對學校,我特別厭惡。此后,我便開始逃學、上網玩游戲,虛擬世界讓我找到樂趣。我爸第一次打我以后,我就在網吧里呆了一個星期,餓了就向同學借錢,買面包或方便面充饑,一天只吃兩頓,沒錢上網我就看別人上網,有時候幫助別人一起玩,還能蹭吃蹭喝。從那以后,我爸再不敢打我,也不多管我了,上網成了我最大的樂趣。
到13歲時,我就不上學了,和比我大得多的人玩。沒錢了,我還找我媽要過幾次錢,還偷了她幾次錢,后來我媽就不再給我錢。沒有錢我很無奈,又想上網,就去偷網吧門口的自行車,偷過五次,每次都能賣二三十元。最后一次讓別人給逮住了,一頓暴打,看我還小就沒有送我去派出所。”
張明無奈地搖搖頭,問記者說:“哥,給支煙抽吧!”張明接過煙,利索地拿出一支點上,很自然地把剩下的煙裝了起來,并對記者笑著說:“還是好煙啊!就算你采訪給我的辛苦費了。”
“時間長了,我和網吧的老板也混熟了,就在網吧里當網管,管吃管喝管上網,每月還給我300元。第一個月發工資,我還給我爸買了兩盒好煙。我和爸的關系也慢慢好了點,我經常上網聊天,也想給我爸找個伴,畢竟他還不是太老。
這幾年我也瘋玩夠了,我爸和我商量想讓我學個技術什么的,我想學修車,再說吧!像我這樣真是一生都毀了……
在此,我也想提醒家長們,一時的沖動不僅毀了一個家,還會毀了一個孩子。
針對以上個例和一些家長對青春期孩子叛逆性格的抱怨,本刊記者采訪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山西省心理學會會員、太原十二中心理教師王宏,她告訴記者,受應試教育影響,家長總是用過于功利的眼光看孩子,太看重孩子的學習成績,卻常常忽視或無視孩子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十幾歲的孩子仍然是弱勢群體,生理、心理發育還不健全,非常需要得到家庭的關愛、師長的重視、同學的友誼。同時,他們又正處于身體斷乳期,認為已經長大,可以獨立面對社會。如果家長或學校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變化,對待孩子仍采用包辦、干涉、指責方式,不僅會影響孩子健康成長,甚至會影響孩子的一生。
王老師向記者介紹,太原市十二中早在1998年就開設了心理健康課,2003年成立了心理咨詢室,隔周給孩子上堂心理課,以引導青少年健康成長。尤其是新生入學后,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心理很容易失衡,他們會為新生準備如何適應新學校的講座。還在學校開展了心理短劇、如何感恩、如何認識自己、安全上網、意志的培訓、走出自卑的陰影、青春期異往等等的課程,讓青少年學生親自參與,效果很好。
談及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表現時,王老師介紹,大致可分為:學習類問題、人際關系類問題、情緒類問題、受挫心理類問題、自卑心理問題及青少年性心理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王老師結合案例,進行分析,給出建議,以幫助青少年以及家長正確面對和引導其健康成長。
學習類問題
案例:張某,男,12歲,學習成績差,對學習不感興趣,非常貪玩,尤其愛玩游戲機,父母對其無奈。
案例分析:這是一個學習動機不足的案例,具體表現為:厭倦學習和逃避學習,學習懶散,上課經常出現分心和厭倦情緒;不愿看書、不愿動腦,將大量時間放在其他活動上;學習精神不振,對學習冷漠、畏縮,經常以多種借口回避學習活動;學習目標缺乏或不明確,學習行為具有從眾性和依賴性;學習方法不當,沒有掌握靈活學習的策略和方法,學習沒計劃,很難適應新的學習任務。
專家建議:學習動機不足是個體、學校、家庭、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應著重從個體因素入手,全面地進行分析和有針對性地提供輔導,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協助孩子建立合理的學習目標,使其學習具有明確的努力方向;2.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提高對學習意義的認識,增強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家長切忌對孩子包辦代替,應給孩子一定的學習和生活空間;3.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在過程中感受學習的樂趣;4.引導孩子對學習成績的優差進行正確的歸因;5.指導孩子掌握良好的學習技能,如復習方法、記憶策略、聽課方法、閱讀策略、學習自我監控策略等;6.制定具體、可行的學習計劃,增強學習有序性,以提高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
人際關系類問題
案例:李某,女,13歲,小學班主任是其母親的同學,加上她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所以老師和同學都很照顧她,像個驕傲的公主,但到了中學后,學習成績大幅度下降,與同學關系很不融洽,心里很難過,感到孤立無助,情緒低落。
案例分析:這是一個新環境適應問題。因轉換學習環境而產生的適應問題在新生中普遍存在,它會導致學習、生活及人際交往功能的損害。表現如下特征:癥狀通常是慢慢形成的;必定面臨過環境的突然或很大變化;癥狀不會因環境改變而立刻好轉,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調理。原因:明確是生活事件(變化)引起了應激反應,如新的學習環境;挫折耐受力低;自我為中心;依賴性強;家庭教育不到位。
專家建議:做適應的主人,不做適應的奴隸;盡早認識到生活、學習中可能碰到的各種問題,認識到生活過程中總有失敗;認識到自己的缺點與不足,設法改變自己的想法、態度與行為方式;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鍛煉自己與人交往的技能,把自己融合在歡樂與團結的學生群體當中;建立同情心,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別人。
情緒類問題
案例 :王某,15歲,女,青春活潑,平時總把日記本鎖到抽屜里,好像有十分秘密的事情,父母覺得很奇怪,莫非孩子有什么秘密?有一天,他們撬開抽屜看了孩子的日記,被王某發現了,她情緒激動,質問父母怎么能偷看她的日記,當著父母的面把日記本撕了。其父母驚愕地站在那里,他們不明白孩子為什么連爸爸媽媽都不信任了。
案例分析:王某的氣憤源于父母對“自我秘密“的侵犯,父母的愕然、驚訝是因為缺乏對青春期孩子心理特點的了解。
專家建議:家長應了解青春期孩子心理發展的特點: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其自主性和成人感是他們自我意識急劇發展時期的一個特點,也是其個性發展的轉折點,如果不尊重他們或者生活上過分地照顧他們,就會使他們產生自卑、焦慮或敵對破壞的消極情緒,影響他們個性的健康發展;青少年自我意識雖有了飛速發展,但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自我教育的能力,而要多與父母溝通,全面評價自己的行為,提高自我認識水平。
異往類問題
案例:M是初二的學生,男,班長,學習成績也不錯,老師同學都喜歡他。可是,到了初二下學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狀況。有一次,M組織同學排練節目,和擅長唱歌的女同學K接觸較多,兩個人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同學們開始拿他們開玩笑。不久,班主任老師也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還批評了他們。不容他們兩個人解釋,并通知了雙方的家長,家長也不容分說批評了他們,M和K都很委屈,M變得有話不愿和家人說,對老師也產生了很強的抵觸情緒,上課故意頂撞老師,在老師的批評下干脆曠課。
案例分析:這個案例屬于異往中的逆反心理偏差問題。造成M出現行為偏差的主要原因:其老師、家長不懂得青春期少年的心理發展特點,不能正確對待他們成長中出現的問題,處理不當,使矛盾激化;M仍處于半幼稚半成熟時期,容易產生固執偏見,逆反心理很強,以為對立與破壞是表現自己的堅強、勇敢,是英雄行為。
專家建議:理解他們,真誠地關心和幫助他們,青少年隨著生理發展,渴望與異往,這種心理很正常。老師與家長應多引導而非限制;要多和他們溝通,了解他們的真實想法,不要無端猜疑;要善于發現和支持他們的正確行為,重新點燃他們自尊的火種。
自卑心理類問題
案例:Q是初一年級實驗班學生,13歲,小學階段學習成績不錯,是班上的佼佼者,上中學后家長和老師對其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也很努力,但學習成績仍然退到了班里30名后,敏感的她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稱自己是“一條被淹死的魚”,產生自卑感,痛苦不安,影響睡眠。
案例分析:該學生屬于焦慮自卑心理。主要是學習壓力太大,對學習效率、健康發展造成影響。壓力一:自我內部的壓力。“我始終應該樣樣比別人好”, 是一種絕對化的非理性觀念,是她問題的根源,當現實生活中出現比別人差的狀況,且自己覺得已經盡力時,現實與認知無法協調,于是產生焦慮和自卑;壓力二:來自外部的壓力。家長和老師的期望值過高;壓力三:學習環境的壓力。實驗班都非“等閑之輩”,競爭對手都很強。
專家建議:①緩解學習壓力。從改變她的認知著手,幫助她從自我困擾中走出來,引導她領悟到“沒有人能夠樣樣都比別人好”,指導她正確面對成績的起伏和人生競爭成敗;② 重建自信。家長和老師降低期望值,轉變教育理念,給予更多的理解、鼓勵和支持;③形成合理的用腦習慣。學習效果的提高重在方法的改進,而不是無限制延長學習時間。
如何預防青少年常見的心理問題
家庭是青少年人性和理想最主要的培育場所之一。因此,家庭關愛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缺少家庭關愛的兒童自尊心不強,心理不會健全,因為家庭關愛是自尊的第一個重要源泉。雙親和子女的關系對于兒童自尊的發展非常重要。
第8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職;心理學;教師;教學;心理輔導;心理健康;職業輔導;生涯規劃
高職院校的心理學教師,所承擔的角色往往比較特殊。首先,需要完成教學任務。而高等職業教育的特點,決定了其所教的課程多是以實踐應用為目的。即使是理論課程,也是為緊接其后的應用類課程做準備。其次,由于高職院校的特點,部分心理學教師亦會從事一些心理健康與職業生涯輔導的工作,這一點在民辦高職院校中尤其多見。再加上心理學專業內容本身的實用性,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高職心理學教師的實踐能力培養都是其主要成長與發展的重點。而基層單位的掛職鍛煉,無疑是全方位提升實踐能力的關鍵。
筆者作為一名高職心理學教師,曾利用課余時間前往多個與心理學和應用心理學相關的基層單位掛職鍛煉。通過在不同基層單位的實踐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專業收獲。作為高職心理學教師在產學研方面實踐意義的探索,在此權作分享:
一、課堂教學與學生未來工作實踐的緊密結合
課堂教學是教師的頭等任務。對于高職教學來說,其首要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掌握更多將來完成特定工作任務所需的知識與技能。這也是心理學中對于“能力”的標準定義。但是,目前不少高職心理學教師由于個人發展的原因,往往缺乏更多基層實務工作的機會。而掛職鍛煉無疑是提高這方面能力的一個幫助。
心理學本身是一門應用非常廣泛的學科,幾乎在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但也正是由于應用面太廣,造成不少教師在講授時無法與實踐很好結合,常常沒有針對性地尋找心理案例。通過掛職鍛煉,可以直接了解工作崗位中所需要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并探索如何在課堂教學中與之結合,從而真正提高教學質量、符合高職教育的獨特要求。這也意味著,高職心理學教師在選擇掛職鍛煉崗位的時候,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原則:
第一,與自己所任教專業課程的相關。考量基層機構能否成為高職心理學教師掛職鍛煉單位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該機構提供的掛職鍛煉工作崗位能否與所執教專業課程的匹配。比如,心理咨詢機構能夠提供與應用心理學課程相關的素材,基層社區機構能夠提供與社區心理健康課程相關的實踐經驗。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利于將實踐心得帶回課堂,作為教學案例分享給本專業學生;
第二,有利于了解學生在工作實踐中需要使用的心理知識與技能。教師的選擇崗位應盡量貼近畢業生工作的實際情況。例如,最佳的掛職單位是與高職院校簽訂校企合作協議的基地,歷屆基本上都有畢業生前往該處實習或就業。這就有利于教師了解學生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并在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解決方案,加入到課堂教學的實例當中。
二、心理健康教育與輔導的實踐訓練
心理健康工作,是高校學生工作的重要方面,尤其對高職院校來說更是如此。但是,心理健康教育與輔導卻是離不開大量的一線實踐經驗。而目前高職院校中從事心理教育與輔導工作的心理學教師往往在實踐經驗方面比較有限。除了日常針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服務以外,需要更多系統化的督導和訓練。由此,額外的專業實踐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環節。
以某著名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為例,該機構不僅針對青少年和家長身心健康長提供專業的心理咨詢服務,而且也是高職心理學教師進行實踐訓練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對青少年人群的針對性,與高職院校的學生年齡有交集,因此服務期間也可收獲不少直接經驗與心得。比如,通過一線咨詢服務發現,不少學生心理問題與其家庭成員的代際關系十分密切。他們所表現出的行為,往往是和其家長的影響極為關聯。這一點,是單在校內從事心理健康服務時難以發現的,而在這里就能容易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此才能制訂出正確的干預方案。另外,該機構提供專業的心理督導服務,也使得教師在這里獲得了更多專業指導。
由此可見,凡是在校內從事心理健康教育與輔導工作的高職心理學教師,在進行基層掛職鍛煉時,應當在實踐中加入一線臨床心理服務的內容,以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量。
三、對學生職業規劃與工作實踐輔導的幫助
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主要是使求學者獲得某一特定職業或職業群所需的實際能力,提供通向某一職業的道路。但現實中有相當數量的高職學生畢業后所選擇的職業與其所學專業并不相關。以某高職學院的社會工作專業為例,在五屆已畢業的學生中,每年從事相關職業的學生都沒有超過10%,而相應當地社會工作行業每年的人才需要缺口卻始終居高不下。究其根本,有學生自身在專業選擇上的問題,也有教師教學與指導的問題。就后者來說,教師個人的直接經驗顯得尤為重要。
職業心理學的創始人F.帕森斯提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格模式,每種人格模式都有其相適應的職業類型,即“人-職匹配”。如果遇到不匹配的崗位,自然就會出現難以維繼的情況。而通過針對高職院校實習生的調研發現,大多數學生并未對自己所適合的崗位以及成長目標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往往只是根據物質待遇、工作強度等情況盲目做出了選擇。這是許多畢業生無法長久安心工作而頻繁跳槽的關鍵,也突顯出在高職院校心理課程當中職業規劃與工作實踐輔導方面的不足。
目前許多高職院校所開設的職業生涯輔導課程,往往是由心理學教師或職業指導方面的專業教師通過大型講座開展理論宣教。到了畢業實習指導時又常常只求完成實習報告或論文,缺乏深入的實踐指導。這體現出教師對于基層工作崗位的認識有限、無法幫助學生樹立“人-職匹配”的理念。而通過基層的掛職鍛煉,尤其是前往專業相關的崗位中進行實踐,可以身臨其境地了解學生就業的過程及其遇到的問題、有效地幫助學生學習職業規劃和實踐的技巧,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崗位。另外,由于教師直接到基層崗位中參與工作,這也在很大程度上給學生以身作則的榜樣,更能體會到他們就業過程中的真實處境,并在情感上給予支持和鼓勵,避免了無法設身處地理解學生的尷尬局面。從人本主義教學與管理的角度,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將真正促使學生達到用心投入的“有意義學習”狀態。
因此,對于從事學生職業輔導的高職心理學教師來說,掛職鍛煉是直觀認識“人-職匹配”的意義、幫助學生掌握具體方法,以人性化的方式教育和指導學生完成職業規劃與就業過程的重要途徑!
綜上所述,高職心理學教師在基層的掛職鍛煉中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無論是教研、應用能力還是實踐指導方面,都是良好的訓練平臺。基于本人研究能力的有限,在此僅作拋磚引玉的探討,希望有更多專業同行能夠以此為契機,獲得更有價值的成果!
參考文獻:
[1]理查德.格里格, 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壘、王d等譯:心理學與生活. 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
[2]斯蒂芬.P.羅賓斯, 蒂莫西.A.賈奇著,孫健敏、李原、黃小勇譯:組織行為學.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3]鄭春賢:高職院校專業教師赴企業掛職鍛煉的思考.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學報,2008年第2卷第4期,2008.
第9篇:青少年心理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青少年,自我中心,假想觀眾,個人神話。
分類號 B844
青少年期,個體在身體上、認知上和社會情感上都會經歷巨大的變化。這個時期他們對于自己非常地關注,自我意識顯著提高,他們似乎有這樣的看法,即像他們自己關注自己那樣,其他人也非常關注他們,而且他人對他們的評價與他們對自己的評價非常吻合[1,2]。上個世紀60年代,受皮亞杰認知發展理論的影響,Elkind把青少年這樣一些特殊表現解釋為認知發展中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他提出了自我中心的兩個維度――假想觀眾(Imaginary audience)和個人神話(personal fable)。專家們認為這樣的心理特征影響了許多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比如對自我意識的夸大感覺、對危險的過分輕視、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對同伴壓力的過度敏感等。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概念一直沿用下來,并被用來解釋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和行為表現。
40年來,關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未曾間斷,其理論建構也在不斷發展,然而由于幾種理論模型不盡相同,研究工具和方法也缺乏一致性,使得在大多數領域上這方面的研究結果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對這些研究進行整合一方面有助于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釋這兩個觀念在青少年發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1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概念界定
在Elkind等人有關青少年自我中心的理論建構中,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作為了自我中心的構成要素。所以這兩個結構最初是作為自我中心的兩個維度被提出的。這兩個結構反映的思維模式對于青春期一些典型的情感和行為,如自我意識、對同伴群體準則的遵奉以及冒險行為等似乎具有特殊的解釋能力。因此,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理念在青少年發展研究中成為長期被引用和探討的概念[1]。
1.1 假想觀眾
青少年可能持有這樣信念,即其他人像自己那樣的關注他們。他們認為其他人,特別是同伴一直在關注他們、評價他們并且對于他們的想法和行為都很感興趣。這樣的信念導致了對自我意識的強調、對他人想法的過度關注和對于現實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應的預期[3~7]。假想觀眾使得青少年們必須時刻保持警覺以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導致尷尬、嘲笑或拒絕的行為[2,8]。從阿德勒學派的觀點來看,假想觀眾代表了一個更寬泛的群體,青少年希望歸屬于這個群體并從中獲得自我價值。而一些個體心理學家認為,假想觀眾的觀念反映了青少年渴望在同伴中顯得重要的愿望。“青少年相信他的一舉一動都被關注和評價著,因此當他認為別人對他評價不高時,他就會聯想到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因此而影響到青少年的價值感和歸屬感”[8,9]。
1.2 個人神話
青少年常常會有這樣的想法:“別人不能理解我正經歷的一切”,“那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或“我能應付一切”[1]。這些觀念反映出青少年認為自己的情感和體驗是與眾不同的,他們相信自己是獨特的、無懈可擊的、無所不能的。Elkind把青少年這樣的心理特點命名為“個人神話”。它被劃分為“獨一無二”、“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三個成分。心理動力學把個人神話定義為一種自戀補償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10]。個人神話的概念有助于解釋青少年的一些自毀行為或無意義行為,它反映了青少年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并且對危險具有特殊的防御能力的心理。同時由于青少年對自我價值和自我意識的過分強調,認為不好的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們對一些存在的危險常常視而不見[8,10]。
2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理論
從1967年Elkind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概念以來,這兩個概念已被很多研究青少年的學者所認可和接受,從1979年起對它們的研究就不曾中斷,有關的理論從最初強調認知發展到強調社會認知發展,再到最近強調自我認同的發展,也隨之在不斷發展。
2.1 最初的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理論
傳統理論的形成受到了皮亞杰認知發展中自我中心概念的影響,因此這兩個觀念被認為和思維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是作為認知發展的副產品被提出的[11]。
2.1.1 理論框架
很多青少年在青春期期間會變得更具自我意識,“他們以自我為中心、追求時尚、引領潮流又很理想主義,同時還可能體驗到強烈的對個人事務的自主愿望和獨一無二的感覺”[1,2]。Elkind把這些現象定義為 “青少年自我中心”,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意識,一種認為自己非常與眾不同并且總是受到他人評價性關注的感覺[2,7]。在皮亞杰的術語中,自我中心是指在沒有能力區分自己和他人[2,11]。依據這一觀點,Elkind認為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是認知發展的一個功能,而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是形式運算階段自我中心的產物。
青少年在青春期早期所經歷的身體和心理上的重大轉變,引起他們對自己的格外關注,雖然逐漸具有了形式運算的思維能力,但是他們對這種思維能力的把握還有欠缺,無法區分自己思考的東西和他人思考的東西之間的差異,Ellind等學者認為這造成了青少年的自我中心[1,2,11]。在此基礎上,由于青少年無法區分自己和他人的關注點產生了假想觀眾觀念,而個人神話的出現則是因為青少年在對自己過分關注的基礎上,過度地區分了自己的感覺。他們無法認識到自己和他人特別是同伴在情感和經歷上存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而是偏頗地認為自己對他人或那些假想觀眾非常重要,他們的感覺是獨特的、與眾不同的[2,11]。
傳統的理論認為形式思維的穩固建立會減弱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假想觀眾可以被看作是青少年用來與現實進行對比驗證的一系列假設,在不斷地對比中,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和他人關注和感興趣的東西并不完全一樣,這時候假想觀眾就會減退。另一方面,個人神話隨著艾里克森提出的“親密感”的建立也會逐漸被克服[2,11]。因此,這個最初的理論預測青少年自我中心發展的模式是曲線的。也就是說,形式運算思維早期的青少年自我中心水平比具體運算思維或完全的形式思維時期都要高。
2.1.2 實證研究
基于Elkind的理論,自1979年開始學者們對青少年自我中心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一些研究確實證實了中學生有比較高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1,12]。但在驗證自我中心和形式運算思維之間關系的研究上,卻存在著不一致。Hudson和Gray[11,12]以及Riley、Adams和Nielsen[1,11,12]的研究發現形式運算和青少年自我中心存在著顯著相關,而Lapsley和Milstead[1,10]、Goossens[3]、O’Connor和Nikolic[1,12]以及Buss[11,13]等學者所做的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相關關系。在對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這兩個觀念是否會在青春期減退進行的驗證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同的結果。Hudson和Gray發現兩個觀念和年齡增長確實存在負相關[1,11],在他們的另一個研究以及Lapsley、Milstead等人所做的研究中卻發現即使是在年齡跨度很大的樣本中也不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1,3,10]。而另一些研究者發現年齡較大的青少年有更高水平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14,16],這與理論構想是恰恰相反的。
最初的青少年自我中心理論模型雖然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但如前所述這些研究結果存在著彼此矛盾的地方。而且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兩個觀念上都存在性別差異,有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表露出更強的青春期自我中心,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男性的自我中心水平更高[1,3,11]。而一般認為認知發展過程應該不存在性別差異,如果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被單純認為是認知發展的一個結果,那么理論上講是不應該有性別差異的。同時很多青少年實際上都沒有達到形式運算思維,這使得傳統理論的基礎受到了質疑。
2.2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社會認知理論
由于傳統理論存在以上的問題,Lapsley和Muriphy等學者認為用認知邏輯中的自我中心來解釋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是不夠的,他們從社會認知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理論模型[1,3]。
2.2.1 理論框架
在這個理論中,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建構“被重新界定為‘人際理解中的問題’”[1,6],它們與青少年的“社會觀點采擇”(social perspective-taking)水平有密切的關系。Lapsley和Murphy用 Selman的社會觀點采擇和“人際關系理解”(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理論來解釋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產生和消退[1,11]。他們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可能是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3上的結果。10到15歲的青少年正處于這一水平,他們能從第三者(或“旁觀自我”observing ego)的角度同時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觀點。這使得他們的自我意識提高了并且能在意更高的層次上想象他人對自己的反映,與此同時也增強了青少年自身的獨特感和無所不能感[1,3,11,17]。
Lapsley和Murphy認為觀點采擇能力水平4的獲得削弱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在達到這個發展階段時,青少年有能力通過思考和協調多個第三者的觀點最終形成一個Selman所謂的“普遍性的社會觀點”(generalized societal perspective)[1,17]。這樣青少年能夠更好地看到自己和整個社會中其它觀點的關系,由此減少了他們的自我意識。同時,達到水平4的青少年對于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有更正確的理解,這降低了他們的個人神話觀念[1,13]。
2.2.2 實證研究
有關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這個社會認知模型的實證研究目前并不多。Jahnke和Blanchard-Fields比較了用形式運算和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來預測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水平的能力。他們發現無論是形式運算還是社會觀點采擇都不能顯著地預測假想觀眾。但是,個人神話觀點卻與社會觀點采擇能力水平3有著顯著的相關[13]。同樣,Vartanian和Powlishta等人的研究也沒有發現水平3與假想觀眾觀念有相關,但發現個人神話觀念在水平3的青少年中最高[1,11,17]。因此目前有限的研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支持這個社會認知模型對于個人神話的理論構想,但是沒能支持對假想觀眾的構想,尚需進一步的實證研究。總體來說,盡管Lapsley和Murphy加入了社會化發展的社會認知模型比Elkind單純的認知發展模型似乎更合理,但仍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
2.3 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新視點”理論
上個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提出青少年自我認同的發展可以被看作是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一個來源[1,15,17]。他們認為當青少年經歷大量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性的變化時,他們開始問自己“我是誰”,并考慮怎么去適應生活以及他們應該為改變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這時他們會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并且開始關心別人對他們的看法”[1]。而家長和其它的社會成人都會期望青少年開始形成他們自己的自我認同,而社會也會為他們提供這樣的機會,青少年的自我意識也因此而得到提高[15,18]。因此自我認同與青少年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成為解釋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新視點”(New Look)理論。
2.3.1 理論模型
O’Connor認為:“在自我認同發展過程中的自我關注和社會要求可能會導致青少年混淆他們自己和別人的關注點”。他提出這樣的假設:有自我認同問題的青少年比沒有經歷自我認同焦慮的孩子有更高的假想觀眾,也就是說自我認同危機可能會導致假想觀眾的增加[15]。同時O’Connor和Nikolic認為父母行為也是這兩個結構的一個重要預測因子。因此他們提出這樣的模型:對父母行為的知覺會影響青少年的自我認同,而自我認同又會去影響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青少年對父母行為的知覺對他們這兩個觀念的影響完全受到自我認同的調節[18]。
Lapsley和Rice等人以自我認同為理論依據,提出一個新的模型,進一步說明了自我認同與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之間的關系[1,3]。他們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時期的分離-個性化過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分離-個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是青春期的重要任務之一,目標是建立家庭關系之外的自我,同時保持與家庭成員親近感,是影響自我認同感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助于緩解青少年在青春期與父母的心理分離焦慮[6,17,18]。
Lapsley提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是關于人際交往和人際情境中的白日夢傾向”[17]。當分離-個性化這個心理過程發生時,青少年會更加關注家庭以外的關系,并開始思考或幻想自己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下的表現。假想觀眾使青少年能夠更好的適應新的社會角色,而個人神話強調的個人獨一無二和無懈可擊性,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關系之外發展個性,建立新的自我[1,17]。
2.3.2 實證研究
“新視點”的理論模型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O’Connor和Nikolic的研究證實了有自我認同危機的青少年特別是男孩,與假想觀眾觀念之間存在正相關[15]。
Lapsley、FitzGerald和Rice等人的研究證明假想觀眾和分離-個性化中的“客體關系特點”(objective-relational features),如美化(engulfment)、共生(symbiosis)、社會化焦慮等有正相關,個人神話觀念與拒絕依賴(dependency denial)、自我關注等存在正相關,和社會化焦慮存在負相關[18]。Lapsley等人1995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對于聯系(connectness)和焦慮以及潛在喪失(potential loss)的關注與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密切相關[17]。Vartanian的研究表明當青少年察覺到人際關系不和諧或某些情感聯系喪失時,他們會采用假想觀眾進行調節,他們對分離-個性化的關注與個人神話觀念存在一定的正相關[1]。
這三個理論模型對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的起因和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也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新視點”理論注意到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在青少年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而且它在解釋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兩個觀念的性別差異上更有說服力,這個模型比前兩個理論構想似乎更具優勢。
3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化觀念與青少年發展的某些關系
幾十年來,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揭示出這兩種心理特點與青少年很多特有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密切相關。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也被用來解釋青春期出現的一些重要的現象,如冒險行為、自我意識的提升、對外表的關注以及抑郁等等。
3.1 分離-個性化過程
分離-個性化被認為是青春期青少年面臨的一大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意識和公眾個性化(public individuation)水平增高,同時可能會經歷更多的社會焦慮。這期間青少年一方面希望脫離父母的保護和監督變得獨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聯系,而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種觀念正反映了這個過程中青少年與父母親密與分離的過程,對分離-個性化這個過程起著調節的作用。當青少年假想出一些觀眾時,他們相信其他人對自己是關注的,這有助于他們脫離父母建立一些家庭之外的關系,同時又不會感到過度的分離焦慮。而個人神話的觀念使得他們更有勇氣去進行自我表達,提高個性化水平[3,6,17,18]。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觀眾和親密感呈現正相關[5],而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與親密感有負相關[16],同時無所不能成分與健康的個性化也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3]。
總之,在青少年的分離-個性化過程中,假想觀眾可以緩解青少年的分離焦慮,讓它趨向一種正常、適度的狀態。而個人神話作為一種防御性的觀念,使青少年在分離過程中,避免或盡量少地體驗到相關的負性情緒體驗[1,3,6,17,18]。因此這兩個在早期的自我中心理論中被認為是一種扭曲、錯誤的心理模式在分離個性化的過程中被賦予了積極的作用。
3.2 親子關系
親子關系是影響青少年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同質量的親子關系對青少年的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有著不同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父母情感上的支持與低水平的假想觀眾相關,而拒絕控制與高的假想觀眾有關[15,18]。Riley、Adam和Nielsen等人的研究表明父親的身體(physical affection)與男孩的假想觀眾觀念呈負相關,和女孩的假想觀眾觀念呈正相關[1,17]。Lapsley和Rice認為與父母的不安全依戀可能導致青少年對社會環境的不安全感,突出表現就是過度的假想觀眾[1,18,19]。Ryan和Kuczkowski等人的研究表明與父母情感上的不安全依戀和青春期后期高水平的假想觀眾有關[20]。因此專家認為親子關系是預測假想觀眾觀念的重要因素,良好的親子關系能使假想觀眾在青春期后期逐步消退,而不良的親子關系將導致青少年在整個青春期都有很高的假想觀眾水平。
3.3 冒險行為
酗酒、斗毆、破壞行為、濫用藥物、等,各種各樣的冒險行為青少年幾乎都去嘗試[21]*。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對一些冒險行為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22,23]。
Elkind認為假想觀眾與一些中度的行為問題有關,如偷竊和破壞公物,青少年認為這些行為可以使他們免受想象的或真實觀眾的輕視[2]。臺灣的一些研究者發現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的賭博、吸煙、酗酒等偏差行為存在正相關,有高假想觀眾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希望博得想象觀眾的關注而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表示出來”[24,25],而個人神話無懈可擊、無所不能的特點使得他們更易于采取偏差行為。男生具有更高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觀念,所以有更多的冒險行為*。
另一些研究證明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青少年冒險性的存在相關。Holmbeck和Crossman等人的研究表明有低水平自我中心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避孕知識,更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對避孕有更積極的態度。而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則相反[21,26]。Goldsmith、Handler通過研究發現個人神話可以很好地解釋青少年為什么不使用避孕措施,在這些青少年看來懷孕或被感染性疾病只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太可能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21]*。
Greene等人的研究測量了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他們對艾滋病相關信息的態度的關系,他們發現個人神話觀念能調節青少年的,通過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可以預測青少年對冒險行為的態度,個人神話高的青少年會傾向于不去遵循安全的信息。而且這種信息越精細,個人神話和避免冒險行為之間的負相關就越高。但同時他們也發現了假想觀眾的一個積極作用,高水平的假想觀眾使青少年更傾向于遵奉同伴的規范,因此當同伴群體對冒險行為持否定態度時,青少年在決定實行冒險行為時就會更謹慎[22,23]。Greene特別指出在設計提供給青少年的健康信息時應考慮個人神話和假想觀眾的消極作用[23]。
3.4 抑郁癥和自殺
在傳統的理論中,Elkind認為自我中心實際上是青少年建立了一個歪曲的自我世界[1],而認知的歪曲是導致抑郁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青少年抑郁研究中,最初的自我中心就吸引了很多學者的關注。一些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水平和抑郁存在密切關系[1,26,27]。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年會報告更多的抑郁癥狀,并且這種相關從青春期早期到后期有跨年齡的一致性[26,27]。在之后的研究中,Goossens和Beyers發現假想觀眾和抑郁呈正相關,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與抑郁呈負相關[3]。Aalsma 和Lapsley等人2004年的研究表明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與青少年抑郁呈正相關,且女生具有更高的獨一無二感,她們面臨更大的、潛在的抑郁威脅。這可能因為在個人神話觀念中,獨一無二的感覺使青少年不愿與同齡人分享消極情緒,造成他們抑郁水平增高,而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可以幫助他們樹立自信,緩解抑郁[10]。
抑郁直接導致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自殺。因此一些心理學家開始直接考察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他們的自殺意念或自殺行為的關系。他們認為假想觀眾可能會導致消極體驗和自我批評,而由此造成的低自我價值感很可能引發自殺。Everall和Bostic等人的研究表明,假想觀眾觀念與青少年高的自責感和強烈的不安全感相關,間接引發了自殺意念。個人神話的獨一無二成分導致青少年更易過分概括化,更難擺脫消極體驗,他們認為自己的處境是獨一無二的,自己的遭遇和內心痛苦沒人能夠體會,他們更喜歡冥想和獨處,而不愿求助于他人,對家人和朋友的疏離使他們變得更加孤獨,從而增加了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的幾率。但一些學者同時認為個人神話的無懈可擊和無所不能成分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青少年的自信和獨立感,從而可以緩解他們的自殺意念。在社會認知框架中,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成為預測青少年抑郁和自殺的有力因素,但個人神話的三個成分對抑郁和自殺的預測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做出解釋[28]。
4 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研究展望
4.1 關于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概念界定
隨著研究的進展,特別是Lapsley等學者從社會認知的角度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是認知發展的副產品這種最初的提法已不再盛行,把這兩種觀念看作是單純扭曲、病態的心理過程的看法也有所改變,但在青少年發展的大多數教材中仍在使用Elkind最初的界定,而且對其缺點和方法論的問題沒有進行說明[7],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研究結果彼此矛盾的原因之一。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發現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可能是正常、自然發展過程的一個產物,假想觀眾只是社會認知成熟和個人適應的反映[7,15,19]。一些學者更是對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解釋為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提出了批評。目前自我中心這個概念沒有得到重新定義,更多研究者在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研究中只是傾向不再使用它。受此影響,目前研究者傾向于把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兩個最初同根同源的概念分開研究,分別探討它們與青少年某些發展問題的影響。隨著研究進展,未來,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可能會得到重新界定,而它們在青少年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也應得到進一步的研究。
4.2 關于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的文化差異
盡管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在一些青少年心理和行為問題上的解釋能力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和認同,很多心理學家也把它們看作是青少年共有的心理特征,但是其提出和發展都是在西方的教育背景下,研究對象也大多局限于西方青少年,對西方以外包括中國的青少年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心理理論都離不開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任何一種心理結構也不能脫離其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西方社會推崇個人主義的培養,鼓勵張揚個性,而東方文化如中國文化提倡集體主義,重視團體的和諧和對群體意見的遵循。因此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這種以自己為關注焦點、突出自身表現的心理特征是否在西方青少年身上更為明顯,而在東方或中國青少年身上比較少見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1,32]。盡管臺灣的一些研究者(張春興、陳明輝、曾育貞、陳惠如等)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已經開始涉及這個領域的探索性研究,他們的研究從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某些偏差行為(酗酒、飆車、斗毆等)這一角度得到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與西方相比,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于擴充和豐富。
4.3 關于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青少年發展某些問題的研究
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在解釋青少年一些特有的或極端的心理特點和行為上有一定的潛在優勢,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與問題行為(吸煙、酗酒、冒險)之間關系的考察上,而對這兩個觀念與青少年發展中一些其它心理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尚未涉及或較少涉及。因此未來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去揭示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與青少年發展特征以及一些特定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之間的關系,如自尊、自戀(narcissism)、樂觀偏向(optimistic bias)、身體映象、飲食障礙、社交焦慮、破壞行為、犯罪等。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個人神話這一觀念具有不同的成分,而目前關于這些成分對青少年某些發展問題作用的研究有著不盡相同的結果,Lapsley等學者提出個人神話不像之前研究所設定的那樣簡單,它應該是一個多元的概念(plural concept)[10],因此對個人神話觀念的成分做更深入和細致地探討應該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而目前測量工具彼此間相容效度低也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所以對這兩個觀念的研究,紙筆以外的研究方法和縱向研究也需要得到更多重視。
國外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研究已有30余年,在其理論、測量方法及與青少年發展的關系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長足進展,在我國這一領域的研究還非常少,深化對青少年假想觀眾和個人神話觀念的認識以及這兩個觀念與青少年某些發展問題和行為表現的關系模式,有必要以中國青少年為對象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1] Vartanian L. Revisiting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construct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 conceptual review. Adolescence, 2000, 35(140): 639~661
[2] Elkind D.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1967, 38: 1025~1034
[3] Goossens L, Beyers W, Emmen M, et al.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factor analyses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new look” measures.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2, 12(2): 193~215
[4] Cohn L, Millstein S, Irwin G, et al. A comparison of two measures of egocentr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8, 52(2): 212~222
[5] Rycek R, Stuhr S, McDermott J, et al.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during late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1998, 33(132): 745~749
[6] Lapsley D.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adolescent ego development: The “new look” at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93, 63, 562~571
[7] Bell J, Bromnick R.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dolescent, 2003, 38(150): 205~219
[8] Eckstein D, Rasmussen P, Wittschen L.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1999, 55(1): 31~50
[9] Lerner R, Olson C. The imaginary audience. Parents, 1994, 69: 1~3
[10] Lapsley D. The two faces of adolescent invulnerability. In: Romer. Reducing adolescent risk: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ennsylvania:SAGE, 2003. 23~31
[11] Buis J, Thompson D.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a brief review. Adolescence, 1989, 24(96): 773~781
[12] Vartanian L.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96, 16(2): 157~178
[13]Jahnke H, Blanchard-Fields, F. A test of two model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3, 22(3): 313~326
[14] Frankenberger K.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 comparis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dolescence, 2000, 23, 343~354
[15] O’Connor B.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r as sources of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5, 24(2): 205~227
[16] Peterson K, Roscoe B. Imaginary audience behavior in older adolescent females. Adolescence, 1991, 26(101): 195~200
[17] Lapsley D, Rice K. The “new look” at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personal fable: Toward a general model of adolescent ego development. In: Lapsley D, Power F. Self, ego, and identity: Integr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Springer, 1988. 109~129
[18] Vartanian L.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egocentrism: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7, 17(3): 245~270
[19] Vartanian L, Powlishta K.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report measures of imaginary audience sensitivity: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ng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egocentrism.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01, 162(2): 187~200.
[20] Ryan R, Kuczkowski R. The imaginary audience, self-consciousness, and public individuation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4, 62(2): 219~238
[21] Arnett J. The young and the reckless: Adolescent reckless behavior.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5, 4: 67~71
[22] Greene K, Krcmar M, Walters L,et al. Targeting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s: the contributions of egocentrism and sensation-seeking.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0, 23: 439~461
[23] Greene K, Krcmar M, Rubin D, et al. Elaboration in processing adolescent health messages: the impact of egocentrism and sensation seeking on message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52(4): 812~831
[24] 陳惠如. 自我控制、青少年自我中心與偏差行為之關系. 碩士論文. 臺灣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2004
[25] 曾育貞. 刺激尋求動機、青少年自我中心與偏差行為之相關研究――以臺南地區為例. 碩士論文, 2002, 臺灣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26] Holmbeck G, Crossman R, Wandrel M, et 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egocentrism,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 contraceptiv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4, 23(2): 169~193
[27] Baron P, Hanna J. Egocentrism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young adul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90, 18(2): 279~286
[28] Everall R, Bostic K, Paulson B. I’m sick of being me: developmental of themes in a suicidal adolescent. Adolescence, 2005, 40(160): 693~708
[29] Vartanian L. Adolescents’ reactions to hypothetical peer group conversations: evidence for an imaginary audience? Adolescence, 2001, 36(142): 347~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