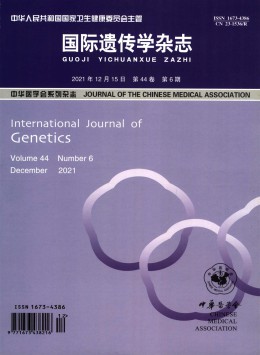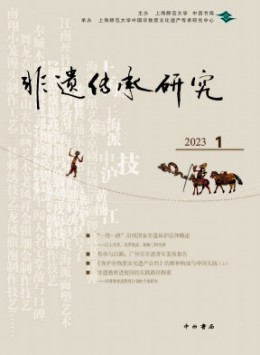遺傳學的意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遺傳學的意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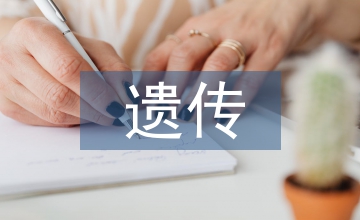
第1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討論式教學;醫學遺傳學;遺傳病例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5)12-0097-02
1 前言
醫學遺傳學是醫學中最前沿的學科,也是新興學科[1]。醫學遺傳學主要是利用DNA技術就疾病與基因之間的關系,從分子角度為疾病早期診斷提供依據,以有效預防出生缺陷、疑難雜癥等疾病的診斷[2]。醫學遺傳學是聯系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紐帶。日常教學中,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選擇合適的醫學遺傳學教學方法,已引起醫學教師的高度重視。本文通過對不同年級的醫學遺傳學專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對討論式教學模式的評價,分析討論式教學方法在醫學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效果。
2 調查問卷結果分析
選擇2012年、2013年、2014年醫學遺傳學專業的學生共921人,發放調查問卷921份,收回921份。統計分析調查問卷的結果,并得出最后結論。
對問題式教學方法的印象 通過對921份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有792人非常喜歡討論式教學方法,占85.99%;101人比較喜歡討論式教學方法,占10.97%;28人對討論式教學的印象一般,占3.04%。
對問題式教學方法的總體評價 834人認為討論式教學方法非常有新意,占90.55%;73人認為討論式教學有一定新意,占7.93%;14人認為討論式教學無新意但有意義,占1.52%。
設置問題的難度 82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很難,占8.90%;101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比較難,占10.97%;615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難度一般,占66.76%;123人認為設置問題簡單,占13.36%。
設置問題是否合理 145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非常合理,占15.74%;674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比較合理,占73.18%,86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較為一般,占9.34%,16人認為討論式教學過程中設置的問題不合理,占1.74%。
小組討論能否解決教師的提問 249人認為通過小組討論能解決教師的所有提問,占27.04%;有580人認為小組討論可以解決教師提出的大部分問題,占62.98%;有73人認為小組討論可以解決教師提出的小部分問題,占7.93%;有19人認為無法解決問題,占2.06%。
小組討論是否有助于理解遺傳知識 755人認為小組討論非常有助于遺傳學知識的理解,占81.98%;166人認為小組討論比較有助于知識理解,占18.02%。
對提高思維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的意義 810人認為討論式教學對提高思維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非常有意義,占87.95%;83人認為討論式教學對提高思維能
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比較有意義,占9.01%;10人認為對提高思維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無意義,占1.09%;18人不清楚是否具有意義,占1.95%。
學習模式 765人更喜歡小組討論的學習模式,占83.06%,125人更喜歡獨立思考的學習模式,占13.57%;31人認為兩種學習模式都可以,占3.37%。
授課模式 563人更喜歡授課式教學模式,占61.13%,324人更喜歡問題式教學模式,占35.18%,34人認為兩種授課模式都可以,占3.69%。
3 討論
近幾年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多媒體教學、實景教學等教學手段逐漸應用于教學中。多媒體教學、實景教學通過先進技術的運用,為學生提供更為全面、直觀的教學內容,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教學效果。教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生對教學方法、教學內容的要求越來越高,教師越來越注重靈活的教學方法,改變傳統的灌輸教育方式。
小組討論式教學方法是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強調教學活動中師生之間的合作互動,而且提倡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活動中來,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同時提高學生的主體作用。小組討論式教學的特點是充分結合理論知識與實際情況,利用多媒體技術讓學生直觀地感受到需要學習的內容,而不僅僅局限于文字方面的學習,加深了學生對理論知識的認識,同時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根據醫學遺傳學的教學內容、培養目標,以案例為導向的小組討論教學模式應用于醫學遺傳學教學中,可以充分利用遺傳咨詢科技服務平臺,讓學生充分了解臨床實踐中的真實遺傳病例,并通過分析、思考以及相互討論等解決實際問題。
醫學遺傳學是生命科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以分子水平為疾病實施早期診斷,包括實施基因診斷、轉基因治療等,有效預防出生缺陷與疑難雜癥,為患者提供更科學、更高效的新型醫學服務。醫學遺傳學基于DNA技術研究,通過研究受精卵或母體受到環境或遺傳影響引起下一代物質畸變引起的疾病,目前主要應用于產前診斷、遺傳咨詢、兒科及腫瘤科等。
醫學遺傳學的授課中采用討論式教學方法,可以充分利用遺傳咨詢科技服務平臺為學生提供真實的病例,通過讓學生分析、思考以及互相討論等解決問題。有研究顯示,討論式教學方法已逐漸應用于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的學習過程中,且已取得滿意效果。討論式教學方法強調課程開始階段,通過提供圖片、視頻等直觀資料,讓學生對所學內容有基本了解,根據提供的材料提出相關問題,學生帶著疑問進行學習,提高學生的課堂積極性,并改善學生的理論知識學習情況。
本組研究中,大部分學生認為討論式教學方法可以解決教師提出的問題,僅有2.06%的學生認為討論式教學解決不了問題,這可能與學生的學習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學習態度等密切相關。張英華[3]等人的研究認為,提供視頻、圖片等直觀資料可以讓學生了解疾病的臨床癥狀,切實體會到疾病帶來的痛苦,提高學生的職業責任以及職業態度,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認識。有研究顯示[4],討論式教學方法可以改變傳統教學方法的枯燥無味,通過直接觀察病例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研究顯示[5],討論式教學方法改變傳統的教師主導的授課方式,讓學生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可以明顯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協作能力以及分析能力。
綜上所述,以遺傳病例為主導的討論式教學方法可以明顯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對教師工作的滿意度,提升學生的專業素質及理論知識水平,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許雪青,王燕,王艷艷,等.構建病案導入式教學法的新型醫學遺傳學課堂教學模式[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
2012(1):8-10.
[2]王燕,章波,許雪青,等.病例討論法在醫學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J].現代教育技術,2013,17(9):31-34.
[3]張英華,高玲玲.以臨床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法在病例討論中的應用[J].現代護理,2012,9(7):563-564.
[4]吳常偉,霍春月,任麗麗.病例討論教學法在醫學遺傳學中的應用與思考[J].現代醫藥衛生,2014,2(28):613-614.
第2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細胞生物學;醫學遺傳學;實驗教學;教學質量
中圖分類號:G40-0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5)03-0085-01
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是醫學院校的基礎課程,也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學科。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的教學分為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兩部分。實驗教學與理論教學聯系密切,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實驗教學要重視對學生獨立觀察、思考和操作能力的培養,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及分析問題、總結問題能力的培養。綜合多年來對臨床醫學、口腔醫學等專業學生的實驗教學實踐和探索,筆者就實驗教學提出幾點體會,以期培養出高素質專業型醫學人才。
一、提高教師自身素質
首先,教師應通過網絡高校教師在線培訓和查閱最新文獻,不斷學習新的理論和技術,應用到日常實驗教學中,讓學生了解一些科學前沿的知識,充實教學內容。其次,基礎學科教師還要兼具臨床醫學方面的知識,為學生日后走向臨床打下堅實的基礎。另外,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保證實驗教學水平不斷提高的關鍵。近年來,我科室教師不斷提升自己的學歷,通過在職進修、脫產學習等方式提升師資隊伍的學歷水平。
二、改變教學模式,提高學習興趣
在以往的教學中,學生的一切實驗行為都由教師安排,教師是主體,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忽視了學生的自主意識。標本片都是教師給準備好的,直接在顯微鏡觀察即可。整個教學過程學生缺乏主動性,教學效果欠佳。如學生進入教室,首先就把教師提前在黑板上寫好的目的、原理和實驗步驟抄寫下來,顯微鏡下觀察標本片也是敷衍看看,結果有的就按照書上畫,或者互相抄襲,如同完成任務一樣完成實驗報告。事實上,在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實驗課中,學生也應該是實驗的參與者,而不是任務的執行者。因此,適當地安排一些由學生自己動手制作完成的實驗用品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如以前我們實驗課學習顯微鏡的使用,我們讓學生學會顯微鏡如何操作后,給學生一些已經制作好的各種組織的標本片進行觀察。而現在,我們讓學生自己動手制作標本片,取材更是取自學生自己的口腔上皮細胞,這樣,學生的制作熱情和觀察熱情就被激發了出來。每個學生都積極地制作一張自己的口腔上皮細胞標本片,放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認真繪圖。有的學生還用手機拍下來,看著自己親手制作的標本片,很有成就感和參與感,教學效果顯著提高。
三、采用多種教學手段輔助教學
有些實驗理論較為抽象,學生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尤其是對于文科學生,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的知識以前幾乎沒有學習過,基礎薄弱。怎么能讓這些學生快速入門呢?我們除了常規的板書以外,應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多媒體動畫輔助教學,真正做到抽象的理論直觀化,讓學生對于整個實驗原理是如何發生發展的一目了然。舉例來說,在細胞有絲分裂觀察實驗中,細胞有絲分裂的過程既是重點又是難點,復雜且抽象。但是借助于三維立體動畫展示,可把整個有絲分裂過程,即兩組完全一樣的染色體如何精確分離的過程清晰明了的呈現在學生眼前。通過這樣的展示,學生輕松地掌握了實驗理論,為接下來的細胞形態觀察和畫圖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四、改進教學方法,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常規使用的教學方法是講授法,這樣學生理解起來比較被動,只能跟著教師的思路走,忽視了學生對知識獲得的自主性和能動性。現在,我們除了講授法外還加入啟發式教學,并注重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調動了學生思維的主動性,為學生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例如人類染色體觀察與核型分析實驗中,在講授正常染色體形態、數目前,先提問學生是否見過先天愚型的人。學生在教師的啟發下開始積極思考,回答出自己見過哪些人,有什么樣的特征,如表情呆滯、發育遲緩、身材矮小等。教師接著提問這些人為什么有這樣的缺陷,學生一般答不上來。教師就可以解釋因為他們多了一條23號染色體,就造成了人生這么大的缺憾,所以今天我們要先把正常染色體的形態數目了解清楚,才能對一些遺傳學疾病采取積極地預防措施。通過這樣的講解,學生明白了學習和研究染色體的重大意義,學習態度也認真了許多。同時,還激發了學生投身科研、造福人類的熱情。
五、教學相長,亦師亦友
傳統教學中,學生對老師是比較敬畏的,課堂氣氛也比較嚴肅,教師在前面講,學生在下面做筆記。實際上,我們應該改變這種刻板的場景,與學生多一些交流與溝通。如可讓學生暢談自己對于某些理論、某些現象的看法,教師給予糾正和補充,從而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記憶。尤其是實驗課,學生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提出來讓老師幫助解決,或者學生有更好的建議可以應用于實驗教學,這樣才能做到教學相長。
通過以上幾點,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活躍了課堂氣氛,豐富了教學內容,培養了學生嚴謹的實驗態度和科研意識,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實驗教學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第3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行為遺傳學,抑郁,焦慮,行為偏差,雙生子研究。
分類號 B845
1 情緒與行為問題的行為遺傳學研究現狀
行為遺傳學是在遺傳學、醫學、心理學等學科基礎上形成的一門交叉學科,結合微觀的分子遺傳學水平和宏觀的社會行為水平的研究,探究在基因和環境的動態交互過程中人類復雜行為的形成機制。19世紀末至今,行為遺傳學已跨入第3個世紀。從孟德爾單基因遺傳定律到多基因系統與環境交互作用影響復雜的人類行為,從傳統的計量遺傳學研究到連鎖、關聯研究再到功能基因組學技術的應用,無論在思想體系還是研究方法上,行為遺傳學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在情緒和行為問題的研究領域內,研究者在抑郁、行為等方面開始取得令人振奮的成果,同時也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問題。
1.1焦慮障礙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焦慮障礙是包括廣泛性焦慮障礙、恐怖癥、驚恐發作、創傷后應激障礙以及強迫癥等在內的一大類情緒障礙。焦慮障礙是最常見的心理疾病之一,據國外研究報道,驚恐發作的終生患病率為3%,廣泛性焦慮障礙為5%,特殊恐怖癥為11%,社交恐怖癥為13%,強迫癥為3%[2]。焦慮障礙不僅直接地損害著個體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導致酗酒、抑郁等問題。
目前,研究者認為焦慮障礙是遺傳和環境兩者互動的結果,但目前針對焦慮障礙的行為遺傳學的具體研究結果還存在爭議。家庭研究發現這類障礙具有家族相似性[3]。兩項基于臨床樣本的雙生子研究顯示,遺傳因素對焦慮發病有影響[4];而另外兩項基于一般人群的雙生子研究則得到了相反的結論[5,6];但是一項基于一般人群的大規模女性雙生子研究結果似乎又偏向于支持遺傳的影響[7]。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群體的雙生子研究結果同樣有不同傾向。例如,一項使用8~16歲雙生子的研究支持共享環境的影響而不支持遺傳因素的影響,而另一項使用3~18歲雙生子的研究發現兩者對社交焦慮都有影響。Bolton等對英國上千對雙生子在4~6歲時的研究則發現,遺傳對分離焦慮障礙、特殊恐怖癥等早期焦慮障礙具有重要影響,兩者病癥的遺傳影響顯著大于環境因素的影響[8]。對于各種特定的焦慮障礙,各研究間仍然無法得到統一的結論。目前被認為與遺傳有關的焦慮障礙包括驚恐發作、廣泛性焦慮障礙、強迫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9]。
焦慮與抑郁障礙的共病率高達60%,研究者傾向于認為兩者在病因學上存在部分共因,例如相同的遺傳易感性。分子水平的研究顯示杏仁核-顳葉-前額葉皮層、單胺系統、應激-激素反應系統與焦慮和抑郁障礙有關。具體來說,從基因與環境互動的角度,研究者探討了5-HT1A受體、五羥色胺轉運蛋白(serotonin transporter, 5-HTT)、色胺酸羥化酶2(tryptophan hydroxylase 2,TPH2)基因的作用及影響這些基因表達的發展關鍵期。但總的來說,焦慮障礙的分子行為遺傳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初期階段[10]。有報道指出,5-HTT基因多態性與焦慮相關人格特質有關,大約可以解釋總變異性的3%到4%,可以解釋遺傳差異的7%到9%[11]。
1.2抑郁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在世界范圍內,抑郁癥是名列前五的致殘和導致疾病負擔的原因之一。預計到2010年,抑郁癥將在全世界范圍內成為第二大負擔的疾病。在我國,隨著社會的轉型,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抑郁癥發病率有著逐年上升的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不斷發生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殺事件,不僅對家庭和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精神和物質損失,還形成非常消極的社會影響。科研人員正不斷努力,試圖了解影響抑郁癥發病的各種因素,尋找有效的手段控制和治療抑郁癥。
行為遺傳學研究專家Robert Plomin等綜合7項家庭研究的結果顯示抑郁癥患者家庭成員的發病危險為9%,明顯高于3%的基線水平,提示遺傳因素在抑郁癥發病中的重要作用。而運用雙生子研究的方法也證實遺傳因素在抑郁癥發病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一項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顯示,同卵雙生子的共病率為40%,顯著高于異卵雙生子的共病率11%[12]。在近期的兩項基于住院患者的研究中,同卵雙生和異卵雙生的平均共病率分別為42%和20%[13]。對于輕、中度抑郁癥,比較各研究的結果,似乎很難得到較確定的結論。但一些研究顯示,遺傳的影響程度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成正比,抑郁越嚴重,遺傳因素的影響就越顯著[13,14]。
現代分子生物學為行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許多研究者致力于將二者結合起來,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奮的成果。例如,Caspi等考查了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的問題:面對同樣的壓力生活事件,為什么有些人會出現抑郁癥狀,而另外一些人則不會[15]。他們發現,5-HTT基因在壓力性事件誘發抑郁的環節上具有調制作用。5-HTT基因在啟動子區有短和長兩種等位基因,具有短等位基因的個體面臨壓力性事件時,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患上抑郁癥甚至自殺。另一個與五羥色胺代謝有關的基因TPH基因被認為是與自殺行為和抑郁有關的主要候選基因之一[16,17]。
1.3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發展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觀點認為,青春期的個體正處于身體和心理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歷性的萌發到成熟,正處于人生的轉折點。這時期的個體常常面對學業、家庭關系、就業、人際交往等問題,承受較多壓力和挫折。而青少年的社會適應功能和應對挫折的能力發展還不成熟,因此,青春期容易發生行為偏離。但越來越多的行為遺傳學研究卻顯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也受遺傳因素的影響。
結合分子遺傳學的研究,Caspi等2002年的研究[18]發現兒童受虐待的生活經歷與單胺氧化酶(MAO-A)基因的交互作用,結果表明那些幼時受到虐待并且攜帶編碼低水平MAO-A基因型的兒童與那些雖然幼時受虐待但攜帶編碼高水平MAO-A基因型的兒童比起來,前者的行為幾乎是后者的兩倍。
國外關于青少年焦慮、抑郁和偏差行為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正方興未艾,還有很多具體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與此同時,我們國家的研究則正在起步,建立我國的青少年行為遺傳學研究的樣本庫,并開展相關研究具有特殊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2 行為遺傳學研究中雙生子研究的價值與現狀
2.1雙生子研究方法的新進展
近年來,行為遺傳學的研究方法,包括雙生子研究方法都有了新的發展。2000年人類基因組全序列的公布與分子遺傳學新技術的發展,大大推動了分子人類遺傳學的研究,并增加了人們對基因產品及其在細胞水平上功能的理解,為研究基因和行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機會。倫敦大學精神病學研究所于1994年建立包含16000對英國雙生子被試的大規模縱向研究項目,開始重構量化行為遺傳學的研究。2002年和2003年,Caspi等結合傳統的心理學評估方法和候選基因技術進行研究,獲得的研究成果更極大地鼓舞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微觀分子水平和宏觀社會行為水平間的聯系[15,18]。
在過去的20年里,隨著行為遺傳學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在人類行為遺傳學研究中微觀層面的基因技術不再是主要困難,影響研究水平的關鍵因素回歸到宏觀層面的行為數據問題上。行為數據的來源、獲取方式、客觀性等成為目前行為遺傳學研究首要考慮的問題。
自高爾頓在百年之前對天才的遺傳因素進行研究以來,雙生子設計――比較同卵雙生子(MZ)和異卵雙生子(DZ)在行為上的相似性,一直是行為遺傳學量化研究中使用范圍最廣的研究方法。雙生子在遺傳與環境方面的異同可謂“天然實驗設計”。近十幾年來,雙生子研究方法本身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最初,研究者只是單純利用雙生子研究來定量估計遺傳作用的大小,估計遺傳度的方法也只是簡單的相關系數法或方差分析法。隨著統計學的發展,研究者不僅可以得到更可靠的遺傳度估計值,還可將各種影響因素進一步分解,并且進一步探討遺傳度的年齡性別差異。另外,許多研究者還將雙生子研究與其他類型研究結合起來,以獲取更多的有用信息。如與收養研究結合起來,可以將環境因素進一步分解。近年來,結合新的分子遺傳學技術后,雙生子研究方法變得更加富有價值[19,20]。
行為遺傳學在分子和環境水平的迅速發展使我們不再局限于研究遺傳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類行為。研究人員現在可以進一步去探尋基因和環境如何影響行為的變化,探討其中的連續、共變和異質問題,闡述先天與后天交互發展的問題。這些新發展對基因和環境在遺傳、表型及環境中交互作用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
2.2國內外雙生子庫的發展狀況
雙生子庫已經在北歐國家系統地建立起來,其他工業化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意大利,荷蘭等國)正在積極地開展相關工作[4]。丹麥于1950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雙生子庫[21]。瑞典有世界上最大的雙生子樣本庫,該庫有近14萬對雙生子[22]。行為遺傳學研究專家Robert Plomin教授在英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雙生子追蹤研究樣本庫。美國有多個區域性的雙生子庫,明尼蘇達雙生子家庭研究項目(Minnesota Twin Family Project ,MTFS)是其中最著名的之一。在亞洲,目前見諸報道的有影響的雙生子庫是斯里蘭卡雙生子庫[23]。國內近年來也開始開展相關工作。例如,近年青島疾控中心在青島地區建立了雙生子發展促進協會,登記了青島地區雙生子并在一部分成人中開展了與疾病有關的研究[24]。
國外研究情況顯示雙生子庫為解決一些邊緣學科問題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研究方法,成果產出非常顯著。如,僅芬蘭雙生子庫的相關研究已經發表了近400篇科研報告[25]。而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雙生子”、“孿生子”、“雙胞胎”為關鍵詞檢索到我國1979~2006年2月發表的中文報告累計163篇。從研究內容上看,國內雙生子研究主要以生理發育和軀體疾病為主[26],缺乏心理發展和精神健康方面的追蹤性研究。這和我國的人口水平和科研需要很不相符合。此外,我國大陸人口已達13億,研究統計顯示我國絕大部分地區雙生子的出生率在0.5%~0.9%[27],我國的雙生子資源非常豐富。因此,充分利用我國的人口優勢結合我國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背景,建立一個基于人口學特點的雙生子樣本追蹤數據庫將對促進我國的人類行為遺傳學研究發揮重要意義。
2.3我國青少年雙生子研究的意義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雙生子庫的建設
隨著國際上行為遺傳學的迅速發展,隨著我國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日益關注,建立我國行為遺傳學研究的樣本庫,并深入開展心理健康的遺傳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已勢在必行。
國際上,分子行為遺傳學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的相關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有關環境-基因交互作用的研究結果具有很高的價值,但相關的報道尚不充分。關于THP基因、5HT1、5HT2、5-HTT、MAO-A等候選基因與人類行為、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究。而且現有的基因研究大多以歐美白種人為樣本,其結果有待于在其他人種和社會文化環境中進一步證實。因此,建立中國的雙生子樣本庫,并以此為基礎,研究抑郁、焦慮和偏差行為的問題,不僅可以為國內相關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科研基礎,而且為國際行為遺傳學領域提供了基于黃種人和東方文化社會的寶貴資料。
青少年期是心理發展的關鍵階段之一。以往研究發現青春期時個體的生理、認知和社會情緒會發生顯著的變化,行為問題大量涌現[28]。以抑郁為例,青少年期是抑郁的性別差異產生的主要階段,也是抑郁水平的曲線發展的重要階段[29,30],因此對探明抑郁的發生機制十分重要。現在研究發現青春期發動是有更多遺傳基礎的,它的出現將伴隨著生理、內分泌及腦的共同變化。因此,這一時期為研究人類行為、認知和情緒的變化性與連續性提供了理想的契機。
值得指出的是,國外對青少年心理和行為的重要研究都采用了追蹤研究方法。事實上,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為隨年齡不斷發展變化并受生活變遷的影響,如果不進行多年的追蹤考察不可能獲得有價值的發現。然而,我國目前非常欠缺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追蹤研究。由于文化社會背景的巨大差異,我們無法確定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的現象和機制與國外的研究結果是否相符。因此,有必要開展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追蹤研究,探明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我國青少年的抑郁隨年齡是否也是曲線發展,拐點在什么年齡?我國抑郁的性別差異狀況如何,在何時產生,主要機制如何?青少年行為的發展的環境和遺傳交互作用如何體現?這些問題都有賴于我國本土的追蹤研究,無法由其它研究替代回答。
中國科學院正建設行為遺傳學研究平臺,集中心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遺傳學家、生物化學家、生理學家和藥理學家的綜合優勢,對意識與思維的本質以及對神經系統疾病機理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通過國際學術合作的方式組建了一支研究隊伍,采用雙生子研究方法開展有關青少年認知、情緒及偏差行為發展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探索遺傳和環境影響人類行為的機制。該項目葛小佳教授對青少年的情緒和行為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28,30~38],特別是青春期過渡對行為的和情緒問題的影響及其基因與環境互動[32]。該項目成員對兒童與青少年情緒特點與發展[39]、情緒與認知的關系[40~42]、情緒問題的心理測量[43]等方面也進行了一定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支研究隊伍,致力于研究影響人類行為的遺傳和環境因素。
目前,該項目已初步建立青少年雙生子信息登記系統,已在北京地區登記400多對雙胞胎,并確立了表型和基因型數據的收集方法。表型數據的收集主要采用心理測驗。通過比較焦慮、抑郁和偏差行為及有關因素的多種測量工具,繼而在中學進行試測,確定了一套適用于青少年的多角度的心理測驗。為了建立最優的口腔細胞收集方案和DNA提取方案,開展了以DNA產率、DNA完整性和儲存時間等作為衡量指標的預實驗,比較了文獻中介紹的幾種常用方法,并結合該項目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進,確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收集方法和技術。
該項目旨在建立我國青少年雙生子庫,結合心理學研究設計與分子行為遺傳技術研究遺傳和環境影響人類行為的機制。通過縱向研究,收集大規模雙生子代表性樣本的表型和基因型數據,分析遺傳和環境資源的變化性和連續性,系統探討焦慮、抑郁和偏差行為的環境影響和遺傳作用,研究抑郁、焦慮和偏差行為的發展機制。為進一步理解人類情感、認知和行為的形成和發展機制提供重要的科研依據。
參考文獻
[1] 白云靜, 鄭希耕, 葛小佳, 隋南. 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 心理科學進展, 2005, 13: 305~313
[2] Kessler R, McGonagle K A, Zhao C B, Nelson C B, Hughes M, Eshleman S, Wittchen H U, Kendler K S. Lifetime and 12-month prevalence of DSM-III-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tud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4, 51: 8~19
[3] Marks I M. Genetics of fear and anxiety disor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86, 149: 406~418
[4] Slater E, Shields J. Genetical aspects of anxiety. In: Lader M H (Ed.), Studies of anxiety. Headley, UK: Ashford, 1969. 62~71
[5] Andrews G, Stewart G, Allen R, Henderson A S. The genetics of six neurotic disorders: A twin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 1990, 19: 23~29
[6] Allgulander C, Nowark J, Rice J P. Psychopathology and treatment of 30344 twins in Sweden. II. Heritability estimates of psych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12884 twin pair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991, 83: 12~15
[7] Kendler K S, Neale M C, Kessler R C, Heath A C, Eaves L J. A population-based twin study of major depression in women: The impact of varying definitions of illnes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2, 49: 257~266
[8] Bolton D,Eley T C,O’Connor T G,et al. Prevalence and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nxiety disorders in 6-year-old twin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5, 36: 1~10
[9] Plomin R, DeFries J C, McClearn G E, McGuffin P. Psychopathology. In: Plomin R, et al. (Eds.), Behavioral Genetics.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00
[10] Leonardo E D, Hen R. Genetics of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6, 57: 117~137
[11] Lesch K-P, Bengel D, Heils A, Sabol S Z, Greenberg B D, Petri S, et al. Association of anxiety-related traits with a polymorphism in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regulatory region. Science, 1996, 274: 1527
[12] Allen M G. Twin studies of affective illnes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76, 33: 1476~1478
[13] McGuffin P, Katz R, Watkins S, Rutherford J. A hospital-based twin register of the heritability of DSM-IV unipolar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6, 53: 129~136
[14] Kendler K S, MacLean C J, Ma Y, O’Neill F A, Walsh D, Straub R E. Marker-to-marker linkage disequilibrium on chromosomes 5q, 6p, and 8p in Irish high-density schizophrenia pedigree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Neuropsychiatric Genetics), 1999, 88: 29~33
[15] Caspi A, Sugden K, et al. 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 Moderation by a polymorphism in the 5-HTT gene. Science, 2003, 301 (July): 386~389
[16] Rujescu D, Giegling I, Sato T, Hartmann A M, Moller H J. Genetic variations in tryptophan hydroxylase in suicidal behavior: analysis and meta-analysis.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3, 54: 465~473
[17] Bellivier F, Chaste P, Malafosse A.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PH gene A218C polymorphism and suicid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B. Neuropsychiatric Genetics, 2004, 124: 87
[18] Caspi A, McClay J, et al. 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 Science, 2002, 297: 851~854
[19] Boomsma D, Busjahn A, Peltonen L. Classical twin study and beyond. Nature Review, 2002, 3: 872~882
[20] 劉曉陵, 金瑜. 行為遺傳學及其新進展. 心理學探新,2005, 25:11~21
[21] The Danish Twin Registry, , 2006-5-28
[26] 潘玲,王米渠,龍鑫等. 10年來雙生子醫學研究的進展與證候起步.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 2005, 14(11): 1393~1395
[27] 干建平,鄭 堅. 中國雙生子出生率和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分布. 中國衛生統計,2001, 18:283~285
[28] Ge X, Lorenz F O,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Simons R L. Trajectori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1: 406~419
[29] Nolen-Hoeksema S, Girgus J S. The emerg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 115: 424~443
[30] Ge X J, Natsuaki M N, Conger R 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mong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in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famili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6, 18: 253~273
[31] Ge X, Conger R D, Lorenz F O, Shanahan M, Elder G H Jr. Mutual influences in parent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5, 31: 406~419
[32] Ge X, Conger R D, Cadoret R D, Neiderhiser J, Troughton E, Stewart E, Yates W. The developmental interfac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A mutual influence model of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32: 574~589
[33] Ge X, Best K, Conger R D, Simons R L.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the occurrence and co-occurrence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nduct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32: 717~731
[34] Ge X, Conger R D. Early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oblems and emergence of late adolescent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9, 27: 429~459
[35] Ge X,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ert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dolescent boy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01, 11: 49~70
[36] Ge X,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Pubertal transitio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emerg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 404~417
[37] Ge X, Brody G H, Conger R D, Simons R L, Murry V M.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 of the effects of pubertal transition on African-American children’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externalized behavioral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2, 38: 42~54
[38] Ge X, Kim I J, Brody G H, Conger R D, Simons R L, Gibbons F X, Cutrona C E. It’s about timing and change: Pubertal transition effects on symptoms of major depress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39: 430~439
[39] 陳祉妍. 負面評價恐懼量表與考試焦慮量表在中學生中的測試報告.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2,16(12):855~857
[40] 楊小冬,羅躍嘉. 焦慮障礙患者的注意偏向和自我注意特點.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5, 19(8): 545~548
[41] Li X, Li X, Luo Y-J. Anxiety and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Neuroreport, 2005, 16 (13): 1501~1505
[42] Poliakoff E, Miles E, Li X, Blanchette I.The effect of visual threat on exogenous spatial attention to touch. Cognition, 2006 (in press)
[43] 陳祉妍,黃崢,劉嘉. 同伴互評對初中生的TAT中親和意象的影響研究. 心理科學,2003,26(2):301~304
The Advance of Behavioral Genetics Studies on Adolescent Anxiety, Depression and Deviant Behaviors
Chen Zhiyan1, Li Xinying 1, Yang Xiaodong 1, Ge Xiaojia1,2
(1 Adolescent Twin Study Group,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Huma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UC Davis,USA)
Abstract:Behavioral genetics researches on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have shown that both genetic and enviormental influences 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deviant behaviors.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new advances of behavioral genetics methods have provided researchers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of gene and enviornment interactions. It is also a opportune time for psychologists to be involved in the investiagtion of the effect of gene and enviornment interaction 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We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lated researches and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Chinese twin registry for carrying out behavioral genetics research on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第4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遺傳學是大學生物學相關專業的一門重要專業課程,對學生打下堅實的生物學基礎及其未來在生物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大學遺傳學課程的教學技術及方法日益完善,但仍有一些方面有待優化。該文以遺傳學教學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及積累的教學經驗為基礎,提出改進遺傳學教學模式及策略:教材內容與科學前沿動態的整合;將生產實踐中的應用及社會關注熱點引入課程教學;實驗課程與理論課程的合理搭配;注意培養學生歸納總結的能力。通過對教學模式的優化及教學策略的改進,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知識擴展能力,完善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及科研創新能力。
遺傳學是大學生物學及相關專業的一門重要理論課程和實驗課程,是生物學分支下的一個重要二級學科,包含了微生物、動物、植物等領域的全部遺傳進化相關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內容,與生物學領域其它學科的知識交叉滲透并相輔相承。因此,大學遺傳學是生物學相關專業本科生的一門重要理論課程。盡管近年來大學教學水平不斷提高,遺傳學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在不斷豐富,但在教學模式及教學策略方面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本文基于在遺傳學教學過程中發現的不足及積累的教學經驗,通過分析學生學習特點及對知識吸收和需求等方面提出若干遺傳學教學內容及策略方面的改進意見,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有助于學生更好地掌握遺傳學領域的知識。
1 教材內容與科學前沿動態的整合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科學研究在不同領域也發生著日新月異的進步,新技術和新成果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遺傳學研究的發展同樣突飛猛進。能被遺傳學教科書收錄的知識都是不同階段遺傳學研究中的精華,同時有價值的遺傳學相關研究成果也不斷被寫入教科書。因此,對于大學遺傳學的教學要做到兩個方面:使學生對遺傳學研究歷史中的重大發現如數家珍;使學生對遺傳學領域現今的科學前沿及發展動態了如指掌。為達到以上兩個方面的教學效果,教師需要在教學內容上進行優化,加強遺傳學研究歷史的講解并將“CNS”的重要成果及諾貝爾獎的介紹引入課堂。
遺傳學的發展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過程,針對同一問題介紹其前因后果,追蹤發展動態有助于學生對知識整體脈絡的掌握。如對《遺傳學》教材第四章“孟德爾遺傳”知識的講解可以加入其研究歷史和后續的發展動態,使學生對該部分內容的掌握更加深刻[1]。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學生在這個章節需要掌握孟德爾以豌豆籽粒形狀、子葉顏色、莖的長度等7對相對性狀為基礎所發現的基因分離和自由組合規律的相關知識。如果在講課過程中僅介紹基因分離和自由組合的原理及相關計算方法不足以加深學生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掌握及科學實驗設計思維的提升。在該部分內容可適當介紹孟德爾發表該成果的主要論文《植物雜交試驗》的相關實驗設計及數理統計,以達到使學生了解科學研究的具體過程,培養學生實驗設計及結果分析的相關能力。同時,在該部分內容講解完畢后要追蹤該問題的發展動態,介紹后續的進一步研究成果。如該部分內容可增加部分關于孟德爾選取的不同性狀背后分子調控機制的研究進展。如對于豌豆籽粒形狀的表現型(圓粒豌豆、皺粒豌豆)是由那些分子機制導致的。對于這個問題,后續的研究結果已經清楚證明,皺粒豌豆是受淀粉分支酶I(SEB1)編碼基因所調控的,由于淀粉分支酶基因突變使種子中的果糖不能轉化為淀粉,隨著失水作用而使籽粒形狀表現為皺縮[2]。其它幾個性狀的研究進展同樣可以進行簡單介紹,如子葉顏色受常綠蛋白(SGR)調控,莖的長度受赤霉素3-氧化酶(GA3ox)調控等[3]。通過圍繞遺傳學某一部分的內容,對其前因后果及研究動態的講解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整體性把握,加深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程度。
諾貝爾獎是科學研究領域的最重要獎項之一,絕大部分獲獎成果在科學研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或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遺傳學領域的發展史上不乏許多被授予諾貝爾獎的重要成果,支撐著遺傳學的發展和生物學領域的進步。因此,在遺傳學課堂上適當引入諾貝爾獎的介紹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程度,同時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和科學探索精神。如在講解遺傳學第三章《遺傳物質的分子基礎》時可以引入1962年沃森(James Watson)、克里克(Francis Crick)、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由于發現DNA雙螺旋模型所獲得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遺傳學教學的第五章《連鎖遺傳和性連鎖》的教學過程中,可以圍繞摩爾根發現連鎖遺傳的相關內容引入1933年摩爾根(Thomas Hunt Morgan)由于創立遺傳學說所獲得的諾貝爾獎以及1946年摩爾根的學生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由于發現X射線照射可引發基因突變所獲得的諾貝爾獎。其它部分章節均可適當向學生介紹由于轉座子的發現,聚合酶鏈式反應體系建立所獲得的諾貝爾獎的相關信息等。同時最新的諾貝爾獎獲獎內容同樣涉及遺傳學領域,如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關于DNA修復的細胞機制方面的研究是對遺傳學第十章《基因突變》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2016年關于細胞自噬理論的研究是對第二章《遺傳的細胞學基礎》中細胞膜功能的深入闡述等。使學生在遺傳學的學習過程中能不斷了解該領域的最新前沿有助于學生追尋科研領域重大發現者的腳步與時俱進,打下深厚的知識基礎。
2 將生產實踐中的應用及社會關注熱點引入課程教學
教師的教學活動除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理論知識外,還應聯系實際,使學生在工作和生活中對所學知識運用自如。遺傳學的教學同樣需要在講解理論基礎知識的同時聯系實際,使學生對所學的知識的應用產生切身的體會,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同時可以增強學生學以致用,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遺傳學課程的講授過程中,可以適當添加一些對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公眾普遍存在的爭議問題等的講解,增加以課程的吸引力和實際應用價值。如在講解遺傳學第三章《遺傳物質的分子基礎》這部分內容時,主要教學目標是通過幾個實驗證據的介紹證明DNA是主要的遺傳物質。該章節可以通過中國古代的迷信思想“滴血認親”是否具有科學依據來引入,講授親子鑒定方法(如DNA指紋技術)應用的理論基礎,最后通過總結否定古代迷信的親自關系鑒定方法,提出新的鑒定方法。在講授過程中穿插這種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更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創造良好的課堂氣氛。此外,在教學過程中還可以理論聯系實際對遺傳學領域社會爭議的熱點問題進行科普及探討。如目前“轉基因是否存在危害”這個問題是公眾中存在爭議的焦點之一,甚至引發崔永元和方舟子之間的爭論大戰,而公眾對轉基因的具體機理及操作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誤讀。在遺傳學課程第九章《基因工程和基因組學》這部分內容的講解過程中可以聯系教科書中介紹的轉基因操作流程在教學過程中做適當的擴展,深入闡述轉基因的原理、田間試驗的流程、目前中國可食用的轉基因產品、目前中國可種植的轉基因產品以及轉基因真正容易引發的問題和不可能引發的問題等,使學生對類似的社會爭議熱點問題具有客觀的認知,激發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通過理論聯系實際和將社會熱點問題引入遺傳學課程教學的方法可增強該課程的趣味性及應用性。
3 實驗課程與理論課程的合理搭配
遺傳學是生物學領域里一門重要理論課程,同時也是一門重要的實驗課程。大學遺傳學課程分為理論課和實驗課兩個部分,實驗課的教學需要與理論課的教學配合進行才能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在遺傳學的教學安排中,對于同一部分內容的理論課程和實驗課程連續進行容易使學生印象深刻。如在講解“細胞有絲分裂”這部分內容時,把實驗課安排在理論課結束一周內進行效果較好。如同學們在課堂上學習了有絲分裂具體過程及細胞分裂各個時期形態特征后一周內進行實驗操作,觀察顯微鏡下真實的染色體形態,比較與教科書中的差異可使學生更牢固地掌握所學到的知識。同樣,遺傳學的實驗設計需針對各部分所講的理論課程內容相配合,在理論課學習完成一周內開展,可以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4 注重培養學生歸納總結的能力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學會學習的能力同樣是大學教學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大學的教學要求學生不僅要被動地接受知識,還要主動地歸納總結進而很好地吸收所學知識。因此,在大學遺傳學的教學中同樣要注重培養學生歸納總結知識的能力,訓練思考問題的邏輯思維能力。在遺傳學的教學活動中,教師不僅要教學生具體的理論知識內容,還需要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因此要做到以下兩點:展示給學生學習的邏輯思維;引導學生歸納總結。引導學生學習的邏輯思維要求教師不僅要展示給學生具體的知識內容,還要求教師展示給學生對問題的理解及學習過程,圖示教學法是實現該目標的很好方法。教師在準備教學幻燈片時應盡量以圖示的方式展示每一部分的知識內容,備課過程中教師可以閱讀書中的每一段主要文字,然后可通過自己的理解將學習到的以文字為主體現的內容轉化為以各種圖形及流程圖為主來表達,在授課過程中結合圖示用文字的方式再將知識點傳達給學生,這樣就可以是學生了解到每一段文字都可以轉化為以圖形表示的直觀內容,引導他們采用類似方法進行知識的學習。如在講授遺傳學中“乳糖操縱子”相關內容時,為表達“乳糖乳糖水解酶基因開啟乳糖分解乳糖水解酶基因關閉”這一過程時,可通過制作一個該過程動態變化的幻燈片來進行講解,展示每一步反應及其原理,引導學生學習的邏輯思維能力。遺傳學教學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引導學生對問題的歸納總結能力,通過比較相似及異同達到對不同知識點清晰掌握的效果。如在講到“非等位基因間的相互作用”這一教學難點時,可引導學生通過歸納總結對其進行區分。在該部分內容中,學生對控制同一生物性狀的兩對基因間的幾類相互作用容易混淆,我們做了如下總結和歸納,采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揭示控制同一性狀兩個基因的內在聯系,如表1:
通過對不同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提高學生歸納和總結問題的能力,找出各部分知識及內容的異同點,可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在大學遺傳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針對教材內容與科學前沿動態的整合,將生產實踐中的應用及社會關注熱點引入課程教學、實驗課程與理論課程的合理搭配、注意培養學生歸納總結的能力等幾個方面,靈活使用不同的教學模式及教學策略,對學生進行教學引導和興趣的激發,從而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第5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遺傳學;布魯姆;認知水平;目標教學
中圖分類號:Q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9)28-0055-02
一、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含義
布魯姆教學目標系統涵蓋認知領域、情感領域和動作領域,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從低到高、從簡單到復雜分別是知道、意會、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1],轉義為教學應培養的不同水平的認知能力。“知道”停留在對事物的初步辨認層面,其技能表現是列舉、引用、命名、定義等。“意會”涉及淺層的理解,其典型技能是描述和解釋。“應用”有點像“生搬硬套”,其典型技能是圖示、計算和預測。“分析”則指向構成要素、相互關系甚至作用原理,其典型技能是對比和辨別。“綜合”就是要體現創造性,其技能特征是設計、開發、規劃和提議。“評價”就是在融會貫通的情況下指出事物的本質或者明確其特點,其典型技能是證明和辯護。
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既可以指導平時教學,也可以運用到考試測驗;既可以指導教師,也可以用于學生自測。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貫穿整個教學過程,從而避免各種錯位的情況下,學生一方面練習了高水平認知技能,另一方面樂于接受高水平認知技能測試,這非常有利于學生認知水平的提高。
二、布魯姆認知水平的確認
建立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時要注意區分“意會”和“分析”這兩個認知水平,因為它們包含了同樣的技能表現。譬如比較,它會位于其中任何一個水平,這取決于比較的深度。例如,學生通過圖片本身判斷哪條曲線代表DNA鏈有最高的熔解溫度是一個意會水平的問題,而指出哪條曲線代表著最高的GC含量則因需要額外的堿基配對穩定性知識而是一個分析水平的問題。此時的一個有益的做法是找出學生必須知道的每個知識點,例如意會要求學生識別每條曲線的熔解點,分析還要求學生聯想到堿基配對、穩定性、能量等與溫度的關系。
應用水平的技能表現變化幅度較大。例如,普通化學中的應用水平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在檢查機械記憶和對變量明確的公式的運用。與此同時,生物化學的應用水平的問題往往是應用概念、選擇公式和決定變量,是一個多步驟的過程。有時候,“應用”被進一步分為低水平和高水平應用,并且可以通過兩個不同的認知過程來區分。“執行”,只涉及用程序性知識解決熟悉的問題;“實施”,要求用概念性和程序性知識去面對不熟悉的問題。例如,低水平的應用問題要求學生把已知的數值代入等式去求米氏常數并且作圖,而在高水平應用中學生必須從概念上知道酶抑制劑的類別,然后選擇公式并畫出反應曲線。
認知水平的確定有一個“就高不就低”的原則,譬如一個需要“知道”、“意會”、“應用”和“分析”技能的問題最終應定在分析水平[1]。這個原則與“知道”、“意會”和“應用”的相互包含關系有一定的聯系,因為通常來講回答一個“應用”水平的問題需要前兩個“水平”的認知技能。“知情則降級”的原則說的是,一個需要分析水平相關技能的問題在學生已經知道其答案的情況下也只能代表知道這個水平的認知能力。總之,確定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認知能力水平時,必須明白學生為了回答問題要掌握什么或者完成什么。
三、建立遺傳學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程序
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建立始于與特定學科或專門領域的結合,終于反復完善直至高度的穩定性。在前一階段,首先要將認知技能通過專業的測評條目表述出來。譬如,在DNA雙螺旋模型的提出中,沃森和克里克的綜合能力讓人嘆服。這一階段的第二步是表面效度檢測,通常是把認知技能相關的所有測評條目給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新生瀏覽,讓他們評判條目內容與所涉學科或者領域的相關性。最后一步是將初步形成的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原型送給擅長布魯姆教育理論的專家并讓其審閱。在第二階段,首先根據原型獨立編碼出不同版本的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并在實際教學中檢驗其效果。經過反復測試和修改,不同版本之間的百分一致性要達到80%以上,并且卡巴值要大于0.75。如果是跨學科的認知階層體系,還要在不同的學科教學中檢查它的通用性。
在編寫遺傳學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認真學習了多本遺傳學教材,做到了基本把握遺傳學知識架構、對經典的遺傳學發展軌跡了然于胸。然后,我們列出遺傳學知識測試條目,并精心地為它們確定對應的認知技能,最終賦予它們不同的認知水平。我們為每堂課設置了六個代表不同認知水平的問題,并且為了形成即時性評價,這些問題在相關的講解之后馬上用于測驗。我們制定的遺傳學認知階層體系也用于指導考試,從而通過教考對比調整知識點的時間和精力分配以及將教學維持在高水平認知。
四、建立遺傳學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的維度
我們嘗試從三個維度編寫遺傳學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
一是問題類型。標注圖表至多是應用水平的認知技能,填空和判斷題至多可測試分析能力[1]。簡答和論述題可測試所有水平的認知技能。多選題可用于綜合水平之外的所有認知技能的測試,“知道”和“意會”水平的多選題的顯著區別是有無干擾項。
二是從題目設計入手編制遺傳學布魯姆認知階層體系。同樣是計算題,“知道水平”的設計是觀察等式兩邊數值的變化,“意會水平”的問題是指出等式的變量,“應用水平”的計算是選擇等式或者變量,“分析水平”的計算是指出等式或者變量的生物學意義,“綜合水平”的問題是提出新的等式,“評價水平”的計算題設計為問題解決的數學方案的優勢和不足[1]。同樣是考察對哈-溫平衡定律的理解,“知道水平”的問題是已知一個等位基因的頻率求出另一個等位基因的頻率,“意會水平”的問題是說出該定律的前提條件,“應用水平”的設計是已知隱性等位基因的頻率求出攜帶者的人群比例,“分析水平”的問題設計成判斷一個群體是否處于哈-溫平衡狀態,“綜合水平”的問題是寫出包含三個等位基因的哈-溫平衡公式,“評價水平”的問題設計是對哈-溫數據進行統計檢驗。最后是學生活動。“知道水平”的活動有標注圖表、列舉特征、辨別結構、卡片測驗、分類配對、抄寫定義等[1]。“意會水平”的活動有用自己的話復述以及舉出一個新的例子。“應用水平”的活動主要是思考增加或剔除一個系統成分或者形狀及過程改變的后果。“分析水平”的活動有解釋原始數據、辨別前提和原理、比較思想或者概念、概念作圖。“綜合水平”的活動有提出假設、設計實驗、建立模型、聯系事實與概念。“評價水平”的活動有寫出他人作品的特點和不足。以上是學生個人的活動,針對不同水平的認知也設計了小組活動。小組活動的基本模式是相互檢查和批判,但是在“知道水平”可以把他人的卡片拿來一起做測驗,在“應用水平”可以輪流給組員講述一個生物學過程,在“綜合水平”可以匯總他人的結果最終形成一個新的模型。
第6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行為遺傳學 本土心理學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02.076
當今分子遺傳學和心理學研究疆域的飛速拓展給行為遺傳學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人類基因組計劃以及物種基因組測序最新研究的進展也已經提示,遺傳和基因組學方法必將從根本上挑戰傳統的神經生物學、醫學、行為學、尤其是心理學研究的方向。
行為遺傳學研究進展
行為遺傳學是一門探討行為的起源、基因對人類行為發展的影響,以及在行為形成過程中,遺傳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的學科。該學科的研究對人類心理發展的機制、教育、優生優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行為遺傳學研究的爭議止于20世紀70年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90年代,行為科學家們越來越接受基因的影響的觀點。1992年的美國心理學年會上, 遺傳被確立為最能代表心理學未來發展的主題之一(Plomin & McClearn,1993)。
行為遺傳學的研究進展主要體現在定量遺傳學(quantitative genetics)的具體研究成果上,尤其體現在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領域的新成果上。
定量遺傳學對于人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譜系研究、雙生子研究和領養研究上。在Bouchard和McGue(2003)的文章中引用了歷年來在雙生子研究中對遺傳和環境作用的估計結果,這些結果分為人格、精神能力(mental ability)、職業興趣、心理疾病和社會態度五個方面。其中,在人格的影響中,基因影響的范圍是40%~50%,且對不同的人格特質遺傳力大致相同。對于精神能力,即IQ而言,遺傳的影響隨年齡增長在上升(5歲時,遺傳力是0122;10歲時是0154;16歲時是0162;18歲時是0182;50歲時是0185),共享環境的作用隨年齡增長從5歲時的0154到年老降至近乎0。職業興趣的遺傳力平均為0136,共享環境對每一因素的影響是大致相當的,約是10%。在心理疾病方面,各種疾病的影響力是不同的,其中精神分裂癥的遺傳力大約是0180,沒有非共享環境的影響;抑郁癥的遺傳力約是0140,沒有共享環境的作用;恐懼癥約是0137,也沒有共享環境的作用;酒精中毒是0150~0160,有共享環境的影響;行為的遺傳力成人大于兒童,遺傳力0141~0146,共享環境的影響從兒童到成人是下降了。社會態度方面,既有遺傳的影響,又有共享環境方面的作用,且在不同層面上的影響作用不同,如20歲以上的成人保守性的遺傳力是0145~0165,女性有共享環境效應;成人虔敬性的遺傳力為0130~0145,共享環境的影響是0120~0140。此外,在其他研究領域,也有相應的結果出現,如自尊領域,也發現遺傳力對自尊水平和穩定性均有重要作用,其余的則用非共享環境來解釋(Neiss,Michell等,2006);Ryan W1 Herndon等人(2005)對17歲青少年對家庭環境的認知進行了有關研究,發現青少年對《家庭環境量表》(FES)的測量結果具有相當的遺傳力。
隨著分子遺傳學的發展,科學家試圖尋找哪些基因與特定行為特征相聯系。分子遺傳學方面的突破為行為遺傳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鑒別DNA的各種技術和成果為在分子水平上研究認識和分析復雜特征的遺傳因素提供了事實依據。目前,在行為遺傳學領域已經發現了諸如老年癡呆、閱讀障礙、活動過度、酒精中毒、同性戀等的相關基因。在尋找特定基因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大多數行為性狀是受到多種基因的影響的,個體之間的差異并不在于基因數量和位置的多大差別,而在于比人們先前考慮的更小效應的數量性狀位點(quantitive trait loci,簡稱QTLs)。QTLs是多基因系統里的基因,每一個QTLs為我們打開了聯系基因和行為的一個小窗。例如,Smith等人(1983)在第15號染色體上發現一片區域與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閱讀障礙有關;2003年,Taipale等發現位于15q21染色體的DYX1基因座附近的DYX1C1是發展性閱讀障礙的候選基因。Gayán等(2005)運用雙變量連鎖分析的方法考察合并閱讀障礙和活動過度,發現14q32染色體區域與閱讀與活動過度有關。在研究中,科學家們也提出質疑,縱使QTLs的效應十分微弱,但也不能排除有的QTLs對某些特定個體的作用很大,只是在人群的平均下效應被沖淡了;QTLs的微弱效應也有可能是基因與基因相互作用(即遺傳抑制)或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GxE)的結果,這也使QTLs的效應特別難辨別。在尋找QTLs的過程中的問題就在于QTLs效應大小的分布以及QTLs主效應被遺傳、GxE和測量問題所沖淡的程度。所以,分子遺傳學的研究也有它的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的發展。
當前,在行為遺傳學領域進一步要考慮的問題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因如何影響心理特質間的關系;第二,基因如何在遺傳和教養之間相互作用;第三,某行為的特定基因是什么;第四,基因型如何轉化為表現型。
行為遺傳學對心理發展的解釋
行為遺傳學在研究人類心理與行為的發展中,對遺傳和環境的影響提出了兩個前提:第一,一種心理或行為,如果在不同的時間及情境下相一致,那它就可以歸于遺傳;第二,一種心理或行為,如果可以通過持續強化而使之鞏固下來并保持穩定,就認為它由環境決定。
著名的行為遺傳學家普洛明(Plomin)將個體心理特質的差異歸為遺傳、共享環境與非共享環境三個方面。遺傳指的是個體的心理特質中來源于基因控制的部分;共享環境指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所分享的使他們在行為上具有相似性的環境,如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職業、受教育水平、鄰里等;非共享環境指的是使同一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兄弟姐妹在心理行為上產生差異的環境,它是個體在家庭內外所獲得的獨特經驗,如不同的出生順序、父母的不同教養態度、所處的同伴群體等。更進一步,個體的心理特點是在遺傳的生理基礎上,通過遺傳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斯卡爾等(Scarr & McCartney)提出,個體的遺傳類型將影響他對環境的選擇和經驗,即雖然個體成長中的環境因素很重要,但哪些環境因素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將取決于個體的遺傳特征。他們將遺傳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方式分為三類:一是被動型(passive),即當父母和孩子具有相同的遺傳傾向時,父母所提供的環境會強化該傾向,如父母的攻擊性強,他們所營造的緊張的家庭氣氛會強化子女的攻擊傾向;二是喚起型(evocative),即個體在遺傳的作用下做出某些反應,這些反應又反過來強化了該遺傳特征,如某個體易激惹,以至其所處的環境充滿了緊張氣氛,這又強化了他的易激惹行為;三是主動型(active),即個體能選擇適合其遺傳特點的環境,如某個體外向、活潑,他會選擇同樣外向、活潑開朗的同伴群體。
總的來說,在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心理發展的過程中,遺傳是發展的基石,環境的決定作用是在這一基石所確定的潛在范圍內有選擇地進行著。
以行為遺傳學的研究視角對本土心理學發展的啟示
行為遺傳學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人們也在這些研究成果面前不斷地加深對自身心理發展的認識。這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問題,即隨著分子遺傳學的研究一步步揭示出與人類心理特質有關的基因組,人們對基因在人類心理發展中的作用的認識在一步步深入,那么他與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存在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是減弱了本土心理學的研究的力量,還是強化了本土心理學的發展?本土心理學中強調的本土文化、環境、教育的干預在基因面前是否就無能為力了?這就是在行為遺傳學研究成果面前,本土心理學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白云靜,等.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J].心理科學進展,2005,13(3):305-306.
2 Robert Plomin.Behavioural gene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0,24(1):30-34.
3 David R.Shaffer,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6th Edition):87.
4 桑標.當代兒童發展心理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78.
5 Rober Plomin.Finding genes in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 When are we going to be there?[J].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05,46(10):1030-1038.
6 Tomas J.Bouchard,J r:Genetic Influence on Human Psychological Trait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J].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2004:148-151.
第7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建構主義教學模式 遺傳與優生 實踐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53
Abstract "Genetics and eugenics" course is a cross subject combined of genetics and eugenics, and is bounded on the course between basic and major courses. The course content is multifarious, knowledge point trivial and students before learning this course, not involved professional course learning, unable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course and clinical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enable them to produce a strong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professional teaching.
Key words Constructivism teaching mode; Genetics and eugenics; practice teaching
“遺傳與優生”課程是遺傳學與優生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性學科,是利用遺傳學的基礎理論分析人類遺傳過程中的規律與特點,指導人類提高群體遺傳素質的一門學科,①該課程知識點瑣碎、內容繁雜,學生普遍反映在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時,不能很好地將知識進行遷移、不能全面地解決問題,而且聽課時也總有各知識點散亂、抽象、枯燥的感覺;而且在學習本門課程之前,雖然高中已涉及部分生物學基礎知識,但還未涉及過專業課程的學習,無法體會到本門課程與臨床實際應用之間的聯系,故難以使他們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因此,需要找到一種更加適合高職高專生身心特點,能培養其綜合應用能力的教學理念和方法。本文結合作者的一些教學體會對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在教學中的應用作一論述。
1 “遺傳與優生”課程的教學現狀
在日常教學和對學生的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很多學生并沒有理解學習本門課程的真正目的和實際意義,部分學生認為這只是一門基礎通識課不必像專業課那樣重視,甚至有部分學生抱著只要考試合格就行的態度,并沒有意識到醫學遺傳學實際是一門界于基礎和專業課之間的課程,甚至部分教學內容如遺傳病的診斷、治療以及遺傳咨詢等就是臨床實際應用的內容。
而傳統的教學模式,以教師講授知識為主,并未注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其主體作用,學生學習知識點空泛,知識面脆弱,不能有效地對知識綜合運用,無法在新的或類似的情境中遷移應用知識。因此,學生學習起來枯燥無趣,積極性不高。
2 將建構主義理論應用于專科院校“遺傳與優生”教學中的必要性
建構主義是在認知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習觀,最早是由心理學家皮亞杰和維果茨基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不僅要求學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知識的灌輸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且要求教師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②使學生通過創設情景、人際協作、商討等一系列活動實現對知識的建構。
將建構主義理論應用于高等醫學專科院校“遺傳與優生”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實現有意義的發現學習,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同時可增加學生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同時應用建構主義理論的實踐探索,也可為醫學高等專科院校其他基礎醫學類課程課堂教學模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3 基于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模式設計
由于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有別于傳統教學,因此教學模式也有顯著不同,強調學生的中心地位。其基本程序為:激活認知結構―創設學習情境―學生自主學習―組織協作學習―完善認知結構。
3.1 建立合作學習小組
每班以6名學生為一個合作學習小組,在本門課程開始之前,先對學生講明合作學習小組的學習方式、目的和意義,激發學生合作學習的興趣,形成合作學習動力,并培養學生合作學習的基本技能,如學習方法、討論技能、討論的記錄、合作學習成果的匯總等。
3.2 分析教學目標設定情境
教學方法的改革是教學改革的核心,在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下,可使用的教學方法有很多,但是公認的、比較成熟的方法有三種,分別為支架式、拋錨式、隨機進入式教學方法。③④
支架式教學其方式是為學習者提供一種概念框架,這種框架中的概念是為發展學生對問題的進一步理解所需要的。在應用時首先圍繞當前學習主題,建立概念框架,并將學生引入框架中的某一點,之后經獨立探索及分組討論最終使學生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
拋錨式教學是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實事件或真實問題的基礎上,以真實事件或問題為基礎(作為“錨”),也可稱為 “基于問題的教學”。在應用時首先創設一個案例情境,提出一個需要讓學生去解決的現實問題,而后教師再向學生提供一些解決該問題所需的相關線索,讓學生自己去獲取信息、探索解決方法,最后經小組討論、交流加深學生對問題的深刻理解。
隨機進入式教學即在教學中對同一教學內容,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下,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現。學習者可以隨意通過不同途徑、不同方式進入同樣教學內容的學習,從而獲得對同一事物或同一問題的多方面的認識與理解。應用時首先教師要為學生呈現出與當前學習主題內容相關的所有信息,學生可自主、隨意選擇進入當前學習主題的相關信息,從而完成對當前學習主題知識的意義建構。在此過程中,教師要注意學生發散性思維能力的培養,通過提問幫助學生需找問題之間的聯系及延伸。
在實踐教學中我們依據不同的教學內容選擇不同的教學模式,設定不同的教學情境,幫助學生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激活自身認知結構,引導學生對知識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對所學新知識進行主動構建。
3.3 自主學習
教師根據當前學習的主題,創設情境,并將問題引入情境,教師在此過程中不直接告知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提供解決該問題的有關線索,之后各小組成員聚集在一起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案,學生通過整理已知信息大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假設,并根據所確定的知識要點和解決方案,收集信息與資料。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他們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及探索精神,并且使自身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
3.4 協作學習
協作學習包括師生間協作和學生間協作。在自主學習的基礎上開展小組討論、組間交流,通過不同觀點的交織碰撞,進一步完善和深化對學習主題的建構。在協作學習過程中,要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教師不再直接灌輸知識或告訴學生該怎樣做,而是在討論過程中及時對學生的表現做出恰當的評價,并對探討方向進行整體把控。協作學習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生的參與意識,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創新精神以及合作能力。
3.5 教師梳理講解
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和協作學結成果,并推薦一人做展示,通過展示匯報,加強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及記憶,更使學生的膽量及語言表達能力得到了鍛煉,而且通過展示匯報教師可了解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建構程度。而后,教師根據學生自主學習、協作學習和展示匯報的具體情況,有重點地對本次課的知識點進行總結及梳理。
3.6 學習效果評價
建構主義教學效果的評價不能用原有僅注重學生期末考試成績的考核方式,需要建立一套綜合評價體系,該體系更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考查。我們采用的評價體系為理論知識考核(占70%)、實驗考核(占10%)以及學生的綜合評價考核(占20%)相結合的形式。理論知識考核即為期中、期末考試的成績;實驗操作考核包括動手操作能力、實驗表現和實驗報告成績;學生的綜合評價考核主要是對學生學習態度、自主學習能力、協作學習過程中的參與程度、協作精神及在協作學習中的貢獻等方面做綜合評價。
4 總結與反思
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使學生由被動聽課變為主動獲取知識信息,建構新知識,整個教學過程強調了學生的主體性,充分鍛煉了學生主動思考問題的能力、語言表達的能力及協作的能力。通過學生座談,大多數學生表示支持這種教學方法,認為這種教學模式對于提高學習的主動性、解決問題的操作性、記憶前后知識的關聯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間接增加了學生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增強了他們的團隊意識、提高了語言表達的能力。⑤
總之,該教學模式對于提高學生整體能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教無定法,教學是一個受多因素制約的復雜活動,過分注重或單獨運用某一種教學模式與策略很難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教師應該根據教學主題的不同,將建構主義與其他互補性的教學方式配合使用,以期得到最佳的教學效果。⑥而且在采用建構主義教學模式進行教學的實踐中,我們發現教師要實現從知識傳遞者向建構合作者的角色轉換,前期的引導與搭建合理的建構情境是至關重要的,而學生要完成由知識被動接受者向一個主動建構者轉變這本身也是一種挑戰,特別是對已習慣灌輸式教學模式的學生來說,這種轉變意味著更多的不確定。因此,教師若想真正帶動學生實現有意義的建構,就必須先深刻理解建構主義的內涵,同時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積極引導和帶動學生,盡可能地激發學生的潛力,從而指導學生實現主動的有意義的知識構建。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度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建構主義理論在醫學高等專科院校《遺傳與優生》教學中的應用研究”(編號:SZ151123)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 丁顯平.人類遺傳與優生.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5.
② 何克抗.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與教學設計[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5):74-81.
③ 何克抗.建構主義――革新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二)[J].學科教育,1998(4):17-20.
④ 陳連豐,趙覓.解讀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四要素――“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J].科技創新導報,2012(24):179.
第8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醫學遺傳學;遺傳咨詢;情景模擬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6-0225-03
醫學遺傳學是醫學與遺傳學相結合、并互相滲透的一門綜合性學科。醫學遺傳學理論學習中主要針對人類遺傳性疾病的發生機制、傳遞規律、診斷方法以及治療和預后進行系統學習。在此基礎上開設實驗課,將理論應用于實踐,通過遺傳咨詢估算再發風險和制定應對對策和措施,有效預防遺傳病的發生,從而達到降低遺傳病發病率的目的[1]。根據現代醫學的發展,我國將面臨極具缺乏醫學遺傳學醫師這一職業。目前,大多數醫院無專門的遺傳咨詢門診,使醫學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遺傳病病例,學生對遺傳性疾病的掌握只限于書本而無臨床實踐機會,這將會導致臨床醫生缺乏對遺傳病的認知能力。因此,我校從2007年開始對五年制臨床醫學、檢驗等本科專業開展醫學遺傳學實驗教學,其中開設了遺傳咨詢教學內容。通過多年教學實踐探索和改進,發現利用情景模擬教學法進行遺傳咨詢知識點的傳授可以更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更好地理解遺傳咨詢的理論基礎及臨床意義,培養學生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
一、教學設計
1.明確教學目的。遺傳咨詢情景模擬教學法是模擬臨床遺傳咨詢的情景進行教學的方法。它是針對臨床醫學、檢驗等專業本科醫學生在學習過染色體標本的制備與人類非顯帶染色體核型分析兩次實驗課的基礎上來開展的。通過此次課的學習,使醫學生能夠充分掌握系譜及系譜分析的理論知識,掌握系譜分析的過程及系譜的繪制方法,熟悉遺傳咨詢的一般步驟和原則,并能推測系譜中各成員的基因型,計算再發風險,了解系譜分析和遺傳咨詢的臨床意義。在此過程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達能力,促進高素質醫學生的培養。
2.教學內容。情景模擬教學法的主要內容是模擬遺傳咨詢過程、講授和熟悉遺傳咨詢的概念、對象、時機、步驟等。作為醫學生首先要讓他們明確知道什么是遺傳咨詢。遺傳咨詢是由醫學遺傳學專業人員或遺傳咨詢醫師(或稱咨詢醫師、醫學遺傳學醫師),應用醫學和遺傳學基本原理,對咨詢者提出的家庭中遺傳病的發病原因、遺傳方式、診斷、治療和預后、一級患者同胞和子女再患此病風險等問題進行交談和討論,并就咨詢者提出的婚育等問題提出可供咨詢者選擇的建議或具體指導措施的過程[2]。遺傳咨詢的時機和對象是一個人在婚姻或生育方面遇到問題,意識到可能面臨患遺傳病的風險,或者本人或子女已患有遺傳病等情況下的人群。其次,傳授和強調進行遺傳咨詢的一般步驟包括遺傳病的明確診斷、繪制系譜并確定遺傳方式、估計再發風險、提出對策和措施。遺傳病的診斷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臨床層次、細胞水平、蛋白質水平、基因水平(基因診斷)等四個水平層次的診斷;繪制系譜并確定遺傳方式以及估計再發風險需要遺傳學理論知識做基礎,要求學生在本科醫學遺傳學中作為掌握的內容加以理解和熟悉后計算再發風險;提出的對策和措施更進一步要求在學生掌握各層次的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系統的理論知識后,給咨詢者提出合適的意見和措施。最后,重點強調醫生給咨詢者提出意見和措施時,要遵循非指令性遺傳咨詢的原則。作為醫生只提出可供咨詢者選擇的若干方案,并陳述各種方案的利弊提供咨詢者選擇,咨詢醫師不應代替咨詢者做決定。
3.教學案例的準備。教學案例的好壞直接影響教學效果。任課教師需要注意從多渠道深入開展病案搜尋工作,從病案中挑選診斷明確、典型的遺傳病案例,除了教材中給出的常見多發遺傳病病例外,也需經常瀏覽OMIM(OnLine Mendelian Inheritence)及等互聯網址,了解重要的有關臨床遺傳學最新診斷技術及進展情況。案例挑選出來后,需要進行加工提煉、細心分析、集體討論,按臨床思維進行教學方案的設計。案例設計原則既要傳授理論知識,又與臨床需要結合,既有利于學生分析,于利于學生演練。
對于案例的教學準備,不但要求任課教師要熟悉案例遺傳病的臨床表現、發病機理,特別要熟悉遺傳病的傳遞規律、傳遞方式、診斷方法、治療方法和預后等方面的相關進展資料,還要要求教師對這些資料的深刻理解和透徹分析,以便針對學生演練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準確的表達或者錯誤的理解進行有效的指導。根據遺傳咨詢的復雜性,則需要教師具有深厚的理論知識基礎,才能提高在模擬遺傳咨詢教學中的指導能力。因此,在案例準備時,要求任課教師要做好充足的教學準備,以應變課堂中隨時出現的問題。
4.教學組織。做好充分的準備后,就進入了模擬遺傳咨詢情景課階段,即開始遺傳咨詢情景模擬教學。由于課堂教學組織難度較大,需要教師在做好充分的案例準備基礎上隨機應變、深入淺出、因材施教。
教師組織教學的基本過程包括:第一步,教師詳細講解遺傳咨詢的定義、步驟、方法、意義;第二步,學生選擇教師準備好的案例分組討論,編寫案例遺傳咨詢的對話,并要求學生在課結束后將所編寫的對話上交作為課堂作業;第三步,學生兩人一組,在45分鐘左右的時間內討論并編寫對話,根據臨床可能的情景,模擬演練遺傳咨詢的過程;第四步,當學生模擬演練完成遺傳咨詢的整個過程后,教師針對學生存在的問題一一進行分析和講解。在肯定學生正確的理解和表達的基礎上指出不當的或者不準確的或者錯誤的表達。
隨著學生不同組別的模擬演練的進行,教師要注意始終引導學生圍繞遺傳咨詢進行交談,其詢問和交談的內容包括對遺傳病的臨床表現、發病原因、遺傳方式、診斷等情況的了解,詢問內容還包括病史、發育史、婚姻史和生育史、家族史,查閱和比對資料進行系譜分析,對咨詢者提出的治療和預后等問題一一作答,并且對患者同胞、子女再患此病的風險提出參考意見。教師始終在一旁提醒、引導和輔佐,并注意把控住整個課堂紀律,使每位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中來,制造出學生在臨床實踐的氣氛,提高學生課堂活躍度。
5.課堂總結。教師根據學生在課堂中的討論、模擬遺傳咨詢的情況進行小結,聯系理論知識肯定學生在討論過程中表現好的地方,指出錯誤或忽視的地方,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記憶,加深學生對遺傳咨詢在臨床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解。最后根據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進行評價,包括學生對案例的分析能力、理論知識的掌握、表達能力、臨床綜合分析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創新能力等等方面。
二、教學思考與討論
1.遺傳咨詢情景模擬教學法的優點和意義。經過多年的教學發現,大多數學生對于應用情景模擬方法進行遺傳咨詢都非常感興趣,整個課堂氣氛活躍,學生參與度高。整個教學活動中,一直圍繞只有真實生活中才存在的病例來進行,組織學生分組開展討論,教師從旁指導,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此教學法解決了以往醫學遺傳學理論教學與臨床脫節,理論教學內容的枯燥難懂,教學手段落后等問題,有效地提高了學生對醫學遺傳學的學習效果及興趣,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教學方法。學生普遍認為通過情景模擬教學,對遺傳性疾病的認識更加深刻和形象,他們所學習的內容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知識,而是在實際臨床工作中切切實實需要解決的問題,極大的激發了學生對于學習《醫學遺傳學》的興趣。
傳統的遺傳咨詢教學主要以灌輸式為主,要求學生大量記憶枯燥無味的基礎知識,在這種模式下的教學不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相反,經過實踐證明,利用情景模擬教學進行遺傳咨詢,將所學理論知識與實際運用緊密結合,將理論課知識運用于實際臨床當中,極大的激發了學生對于學習醫學遺傳學的興趣,使學生整堂課都能夠融入到課堂教學過程中,使學生將講臺變為他們自由發揮的舞臺,而教師課堂中僅僅起到引導作用。在此過程中,學生從被動的接受知識向主動學習轉變,既加深了對理論知識的記憶,又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訓練了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
近年來醫患關系逐漸緊張,患者的維權意識也越來越強,如何緩解醫患關系也是醫學院校在培養學生時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通過臨床情景模擬教學的方法,讓學生扮演患者有助于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學生通過扮演患者,能夠充分的體會患者的心理和情緒上的變化,站在患者的角度看待就醫過程,起到了換位思考的作用。另一方面,學生站在醫生的角度學會處理醫生和患者之間的矛盾,可以縮短學校與社會實踐的差距,幫助學生建立醫生角色,為學生將來走向社會處理醫患關系奠定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遺傳咨詢師在我國醫學領域缺乏大量的人才,是一個有待新增的職業。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醫療用人單位都要求他們的醫生通過全美醫學遺傳學會的考試和資格認證[3]。所以,教師可借此課程向學生宣講國際國內外醫學遺傳學理論、臨床遺傳學的發展的趨勢和中國醫學發展的所面臨機遇和挑戰。向學生說明遺傳咨詢是一項極具挑戰的醫療活動,希望有更多的醫學志愿者加入這項醫療事業中來。
2.遺傳咨詢情景模擬教學法的欠缺之處。首先,情景模擬與實際臨床有一定的差別,學生由于缺少臨床經驗,在進行扮演患者的過程中,很容易用到所學的專業術語,與真正臨床中所遇到的實際病例有較大的差別,沒有達到角色交換的目的。其次,在提出對策和措施時,由于缺乏各層次的分子細胞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系統的理論知識,并且對所學醫學遺傳學知識不能靈活運用,只能提出供咨詢者選擇一到兩種方案,沒有真正提供可供咨詢者選擇的若干方案,且無法做到非指令性原則。最后,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由于每位學生學習水平參差不齊,不愿意作為學習的主體,導致過分依賴老師,影響教學效果。目前看來,要使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最好的方法是讓學生參與真正的臨床實踐,使學生體會到遺傳咨詢過程的復雜性。
通過7年的教學效果來看,情景模擬教學極大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真正實現了對醫學生綜合素質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值得推薦的好方法。
參考文獻:
[1]蔡紹京,李學英.醫學遺傳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
[2]章遠志,Nanbert ZHONG.中國目前的遺傳咨詢(英文)[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06,(01).
[3]趙會全.美國臨床醫學進展[J].國外遺傳學雜志,2007,30(2).
基金項目:遵義醫學院教學改革計劃項目2013(j-2-7)。
第9篇: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摘 要 瘧原蟲產生抗藥性是瘧疾防治中遇到的主要難題之一。抗葉酸類抗瘧藥的抗藥性機制已基本搞清,與其作用靶酶二氫葉酸還原酶或二氫蝶酸合成酶基因點突變相關。喹啉類藥物抗性影響因子尚不完全清楚。惡性瘧原蟲5號染色體上的多藥耐藥基因1及7號染色體上的cg2基因可能是抗性相關基因,但二者都不能完全解釋抗性,尚待深入研究。
瘧疾的流行至今仍然十分廣泛,遍及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20億人面臨感染瘧疾的危險。據統計,全球每年有3億~5億瘧疾病例,導致150萬~270萬人死亡,其中100萬是居住在非洲的5歲以下兒童[1]。人類在長期實踐過程中篩選了大量防治瘧疾的藥物,但是,自從50年代末在東南亞和南美洲分別發現惡性瘧原蟲對氯喹產生抗藥性以后,抗氯喹惡性瘧迅速擴散蔓延,抗藥性程度不斷增加,并且從單藥抗藥性向多藥抗藥性發展。我國的海南、云南和廣西等省、自治區也有抗藥性瘧疾的流行。目前,瘧原蟲對幾乎每一種抗瘧藥都產生了抗性,瘧疾防治形勢非常嚴峻,迫切要求我們盡快搞清抗藥性產生的機制,以便采取措施防止或逆轉抗藥性的發生并指導新藥研究。近年來,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及學科滲透大大推動了瘧原蟲抗藥性機制的遺傳學研究,本文就抗葉酸制劑及喹啉類藥物抗性的分子機制作一綜述。
1 抗葉酸制劑抗性的分子機制
1.1 二氫葉酸還原酶(DHFR)基因
乙胺嘧啶和環氯胍都是二氫葉酸還原酶抑制劑。研究表明,惡性瘧原蟲對兩藥產生抗藥性都與DHFR基因點突變相關,但二者存在差異[2,3]。迄今為止,共報道了6個DHFR基因編碼區變異:108位SerAsn或Thr,51位AsnIle,59位CysArg,16位AlaVal,164位IleLeu。單一點突變所致DHFR108位Ser變異成Asn即可產生乙胺嘧啶抗性,但對環氯胍的反應性僅稍有降低。對乙胺嘧啶產生高度抗性則需其他位點突變共存,包括51位AsnIle和(或)59位CysArg。而與環氯胍抗性相關的變異是DHFR108位SerThr伴隨16位AlaVal,同樣,該抗性株對乙胺嘧啶的敏感性變化不大。
另外,在對乙胺嘧啶和環氯胍交叉耐藥的惡性瘧原蟲中發現存在多個位點變異:DHFR164位IleLeu,108位SerAsn,59位CysArg和(或)51位AsnIle。由于僅包含Asn-108和Arg-59變異的原蟲分離物不具有環氯胍抗性,因此,認為Leu-164變異在瘧原蟲對兩藥產生交叉抗性的機制中起重要作用[3]。
1.2 二氫蝶酸合成酶(DHPS)基因
磺胺類藥是二氫蝶酸合成酶抑制劑。研究發現,正是由于磺胺類藥作用的靶酶DHPS基因點突變,使得酶活性中心結構域形狀改變,因而降低了對藥物的敏感性。體外低葉酸條件下實驗表明[4],與磺胺多辛易感性降低相關的DHPS氨基酸變異主要包括581位AlaGly,436位SerPhe伴隨613位AlaThr/Ser,以及436位SerAla,437位AlaGly。
磺胺多辛通常與乙胺嘧啶合用于治療惡性瘧疾。對兩藥聯用的體外研究揭示,瘧原蟲對乙胺嘧啶的易感性決定著兩藥協同作用的效果[5]。體內研究也發現[6],前面所述的DHFR變異類型均存在并與抗性程度相關,而DHPS基因突變與抗性的發生沒有明顯相關性,僅在抗性程度較高的玻利維亞地區可見Gly-581高度流行,Gly-437和Glu-540的發生與用乙胺嘧啶-磺胺多辛治療失敗率相當,這可能由于體外研究中葉酸和PABA水平不同于體內。另一種解釋是Ala-436的變異可能僅在低度抗性時出現,且不與高度抗性時的變異Gly-437,Glu-540和Gly-581共存。因此推測,DHPS變異在臨床乙胺嘧啶-磺胺多辛抗性的產生中不起主導作用。
我們能夠肯定,體內乙胺嘧啶-磺胺多辛抗性與DHFR基因突變相關,然而在抗性瘧流行區治療失敗率并不像突變發生率那樣高,提示體外研究發現的三種變異Asn-108,Ile-51和Arg-59不能完全解釋體內高度抗性。在玻利維亞的高度抗性病例中曾發現Leu-164及另外兩個新的變異Arg-50和插入30-31位間的玻利維亞重復區高度流行,提示這些變異可能是在抗性發展的較高時期產生的,關系到治療的成敗。據此Plowe等[6]提出假設,體內乙胺嘧啶-磺胺多辛抗性程度分級RⅠ,RⅡ,RⅢ正是基于DHFR和DHPS基因突變的不斷積累。由于現實中惡性瘧原蟲感染的復雜性及宿主免疫與葉酸水平的影響,事實上所檢測到的抗性突變往往是交叉重疊的。
總之,關于抗葉酸制劑的抗藥性分子機制已基本搞清。因此,我們可以根據特有的突變類型,運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進行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研究,這對于鑒定某一瘧疾流行區的藥物敏感性,從而指導臨床用藥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可指導新藥設計及臨床藥物聯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藥物抗性的發生。
2 喹啉類藥物抗性的分子機制
氯喹曾經是使用最廣泛的抗瘧藥,由于抗性的發展及傳播,在大部分地區已不再具有以往的效力。影響抗性機理最終闡明的重要因素是喹啉類藥物作用機制還不十分清楚。不同地區的研究者報道關于氯喹抗性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抗氯喹蟲株較敏感性蟲株藥物聚集水平降低了。因此,氯喹的轉運和聚集不僅對其發揮抗瘧活性是必需的,而且與抗性表型密切相關,提示喹啉類藥物抗性產生可能與其作用方式沒有直接關系,這與抗葉酸制劑不同。
2.1 惡性瘧原蟲多藥耐藥基因(pfmdr1和pfmdr2)
研究發現,維拉帕米(一種鈣通道阻滯劑)可逆轉氯喹抗藥性,促使人們考慮氯喹抗性可能與哺乳動物腫瘤細胞多藥抗藥性(MDR)表型相似[7]。研究表明,腫瘤細胞產生MDR是由于一種ATP依賴性的、與藥物外排相關的蛋白過量表達所致,稱為P-糖蛋白,它定位于細胞表面,與許多不同類型的化合物有親合力[8]。在此基礎上,Krogstad等[9]發現抗氯喹株原蟲較敏感株排出氯喹的速率快40~50倍,且這種排出是能量依賴性的,并可被能量缺乏及ATP阻斷劑抑制。但是也有研究顯示,抗氯喹株與敏感株藥物外排率相等[10];二者藥物聚集量的差別是由于最初的藥物攝入速率不同所致[11]。
哺乳動物MDR表型通常伴有mdr基因的擴增,導致其產物P-糖蛋白表達增加[8]。對惡性瘧原蟲基因的研究表明也存在mdr基因同系物,以pfmdr1和pfmdr2為主[12,13]。目前尚無證據表明pfmdr2及其表達產物與氯喹抗性有關,而有相當多的研究認為pfmdr1與抗藥性機制相關。
Pfmdr1編碼一個相對分子質量約162的蛋白,稱為P-糖蛋白同系物1(Pgh1)。早期研究表明,在一些抗氯喹株中存在pfmdr1擴增[12,13]。免疫熒光及免疫電鏡技術觀察pfmdr1蛋白產物,發現Pgh1在紅內期表達,主要定位于食物泡膜上,這與它可能充當氯喹轉運蛋白的角色一致,但是定量分析不能確認Pgh1過表達與抗藥性相關[14]。
Foote 等[15]對pfmdr1基因3′多態性及等位基因變異分析表明,pfmdr1突變與氯喹抗性表型相關,并提出存在兩種類型抗性相關等位基因,一種可致單一氨基酸變異86位AsnTyr,為K1型;另一種則導致三種氨基酸變異,1034位SerCys、1042位AsnAsp和1246位AspTry,為7G8型。這可能分別代表著最早在東南亞和南美洲出現的氯喹抗性類型。以此為基礎,運用單盲法研究,曾正確地預測了36份樣品中的34份的藥物易感性。Adagu等[16]的研究也表明86位Tyr突變與氯喹抗性相關。但是,同時有些研究不能得到相同的結果。這提示可能pfmdr1不是唯一的控制抗性的基因。
氯喹抗性與pfmdr1的關系尚不明確,從選自氯喹抗性親代的甲氟喹抗性株中卻發現有pfmdr1的擴增,并且蟲株對甲氟喹抗性增加的同時對氯喹的易感性增加了[12]。Barnes等[17]的研究表明,隨著原蟲對氯喹抗性的增加,pfmdr1基因拷貝數減少,甲氟喹易感性增加,這無疑加強了pfmdr1擴增與甲氟喹抗性的關聯。因此推測pfmdr1擴增可能與氯喹高度抗性是不相容的,Pgh1的功能可能是促進對氯喹的易感性。
將pfmdr1基因轉染于異源表達系統中國倉鼠卵巢細胞(CHO),使其表達惡性瘧原蟲Pgh1,發現Pgh1表達伴隨有能量依賴性的藥物攝入增加[18],而且Pgh1就定位于轉染的CHO細胞溶酶體上,經測定,發現轉染細胞溶酶體內pH值有所下降,認為氯喹聚集增加可能是溶酶體酸化的結果,推測pfmdr1可能編碼一種液泡氯化物通道。當CHO細胞被攜帶有7G8型1034和1042位突變的pfmdr1基因轉染時,則發現氯喹易感性喪失,細胞聚集藥物及酸化溶酶體的能力減弱,這就從某種意義上證實了關于Pgh1促進氯喹易感性的推測。但這仍不足以解釋抗性。Ritchie等[19]發現源自氯喹抗性親代的鹵泛曲林抗株表現對鹵泛曲林、甲氟喹和奎寧敏感性降低而對氯喹敏感性增強,卻未檢測到任何pfmdr1基因序列或拷貝數及Pgh1表達的變化。
很明顯,關于pfmdr1與喹啉類藥物抗性的關系仍有很大疑問,可能抗性的發生有一定的地理學基礎,而尋找某個單一的基因來解釋抗性本身過于簡單化,氯喹抗性發生的緩慢及復雜性也不支持單基因決定抗性的假設。
2.2 cg1基因和cg2基因
早在90年代初,Wellems等[20]從一次遺傳雜交試驗中發現瘧原蟲抗氯喹表型以孟德爾方式遺傳,親代pfmdr1基因不與子代藥物反應表型分離。對雜交子代進一步觀察發現氯喹抗性表型與惡性瘧原蟲7號染色體上約400 kb的區域相關而不是5號染色體的pfmdr1基因。這一區域包含80~100個基因,對該區域進行大量的分析研究后[21],確定36 kb的片段與氯喹抗性表型相關,并鑒定了2個候選基因:cg1和cg2。對采自東南亞和非洲大量的抗氯喹株檢測結果表明,cg1尤其是cg2基因多態性與氯喹抗性顯著相關,但不排除cg1與cg2協同參與了抗性。不過,對南美洲抗氯喹株的檢測沒有得到同樣結論。運用免疫電鏡技術觀察到CG2蛋白定位于原蟲周圍液泡、食物泡及囊泡結構形成的外膜復合物上,暗示CG2可能是一種轉運蛋白。然而檢索序列數據庫未發現CG2與任何已知離子通道或轉運蛋白同源。
Sanchez等[22]認為在氯喹抗性過程中,有轉運分子在起作用,一個Na+/H+交換蛋白(NHE)可能調控著氯喹的攝取。已證實惡性瘧原蟲以一種熱敏感的可飽和的方式主動攝取氯喹,并可被高等真核生物NHE的特異性抑制劑氨氯吡咪競爭性抑制。運用與Su等同樣的親代子代克隆研究發現,氯喹抗性表型與惡性瘧原蟲NHE的生理生化特征有遺傳學關聯。因此,Sanchez等[23]推測惡性瘧原蟲cg2基因可能編碼Na+/H+交換蛋白,他們認為兩者可能有共同的結構和功能,比如氨氯吡咪結合位點、與NHE離子交換區同源等。但是,Wellems等[24]詳細分析了CG2蛋白序列,不支持上述觀點。首先,盡管CG2序列有一些疏水性氨基酸,卻沒有整合膜蛋白的典型特征,疏水性與跨膜區域分析表明,NHE與CG2有顯著差別。其次,CG2與NHE離子交換區域不具有同源性,Sanchez等提出的CG2有氨氯吡咪結合位點也沒有可靠的根據。此外,如果CG2是一種整合膜Na+/H+交換蛋白,應當定位于胞漿膜上,而不是原蟲周圍液泡及食物泡上。
Wellems等[24]認為CG2不是轉運蛋白,而是通過直接影響氯喹攝入、血紅蛋白消化、血紅素聚合或血紅素與氯喹復合物的毒性作用來調控原蟲對氯喹的易感性,但需要進一步的生化實驗及蛋白功能研究才能確定其確切機制。
總之,關于喹啉類藥物抗性機制已提出了多種理論,雖然每種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抗性,但是這些研究對于搞清抗性機制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現代藥理學、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夠闡明這一問題。
參考文獻
[1] Kondrachine aV, Trigg PI. Global overview of malaria[J]. Indian J Med Res, 1997, 106(8):39.
[2] Peterson DS, Walliker D, Wellems TE. Evidence that a point mutation in dihydrofolate reductase-thymidylate synthase confers resistance to pyrimethamine in P.falciparum malaria[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8, 85(23): 9114.
[3] Peterson DS, Milhous WK, Wellems TE. Molecular basis of differential resistance to cycloguanil and pyrimethamine in P.falciparum malaria[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0, 87(8): 3018.
[4] Triglia T, Cowman AF. Primary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of the dihydropteroate synthase gene of P.falciparum[J]. 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4, 91(15): 7149.
[5] Watkins WM, Mberu EK, Winstanley PA, et al. The efficacy of antifolate antimalarial combinations in Africa: a predictive model based on pharmacodynamic and pharmacokinetic analyses[J]. Parasitol Today, 1997, 91(4): 456.
[6] Plowe CV, Cortese JF, Djimde A, et al. Mutations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 dihydrofolate reductase and dihydropteroate synthase and epidemiologic patterns of pyrimethamine-sulfadoxine use and resistance[J]. J infect Dis, 1997, 176(6): 1590.
[7] Martin SK, Oduola AMJ, Milhous WK. Reversal of chloroquine resistance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 by verapamil. Science, 1987, 235(4791): 899.
[8] Riordan JR, Deuchars K, Kartner N, et al. Amplification of P-glycoprotein genes in multidrug-resistant mammalian cell lines[J]. Nature, 1985,316(6031): 817.
[9] Krogstad DJ, Gluzman IY, Kyle DE, et al. Efflux of chloroquine from plasmodium falciparum: mechanism of chloroquine resistance[J]. Science,1987, 27(11): 1283.
[10]
Bray PG, Howells RE, Ritchie GY, et al. Rapid chloroquine efflux phenotype in both chloroquine-sensitive and chloroquine-resistant plasmodium falciparum[J]. Biochem Pharmacol, 1992, 44(7): 1317.
[11] Bray PG, Hawley SR, Ward SA. 4-Aminoquinoline resistance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amodiaquine uptake[J]. Mol pharmacol, 1996, 50(6): 1551.
[12] Wilson CM, Serrano AE, Wasley A, et al. Amplification of a gene related to mammalian mdr genes in drug resistant P.falciparum[J]. Science,1989, 244(4909): 1184.
[13] Foote SJ, Thompson JK, Cowman AF, et al. Amplification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in some chloroquine resistant isolates of P.falciparum[J]. cell, 1989, 57(6): 921.
[14] Cowman AF, Karcz S, Galatis D, et al. A P-glycoprotein homologue of p.falciparum is localized on the digestive vacuole[J]. J Cell Biol, 1991,113(5): 1033.
[15] Foote SJ, Kyle DE, Martin RK, et al. Several alleles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are closely linked to chloroquine resistance in P.falciparum. nature, 1990, 345(6272): 255.
[16] Adagu IS, Warhurst DC, Carucci DJ, et al. Pfmdr1 mutations and chloroquine-resistance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 isolates from Zaire, Nigeria. trans R Soc Trop Med Hyg, 1995, 89(2): 132.
[17] Barnes DA, Foote SJ, Galatis D, et al. Selection for high-level chloroquine resistance results in deamplification of the pfmdr1 gene and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mefloquine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J]. EMBO J,1992, 11(8): 3067.
[18] van Es HHG, Karcz S, Chu F, et al. Expression of the plasmodial pfmdr1 gene in mammalian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chloroquine[J]. Mol Cell Biol, 1994, 14(4): 2419.
[19] Ritchie GY, Mungthin M, Green JE, et al. In vitro selection of halofantrine resistance in P.falciparum is not correlated with amplification of pfmdr1 or overexpression of Pgh1[J]. Mol Biochem Parasitol, 1996, 83(1): 35.
[20]
Wellems TE, Walker-Jonah A, Panton LJ. Genetic mapping of the chloroquine resistance locus on P.falciparum chromosome 7[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1, 88(8): 3382.
[21] Su X, Kirkman LA, Fujioka H, et al. Complex polymorphisms in an ~300 kDa protein are linked to chloroquine-resistant P.falciparum in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J]. Cell, 1997, 91(5): 593.
[22] Sanchez CP, Wunsch S, Lanzer M. Identification of a chloroquine importer in Plasmodium falciparum[J]. J Biol Chem, 1997, 272(5): 2652.
相關熱門標簽
相關文章閱讀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遺傳病論文
- 2遺傳學顯性基因隱性基因
- 3遺傳學的問題
- 4遺傳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 5遺傳學基因突變
- 6遺傳學在農業上的應用
- 7遺傳學分離定律
- 8遺傳學在育種中的應用
- 9遺傳學發展史
- 10遺傳學和分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