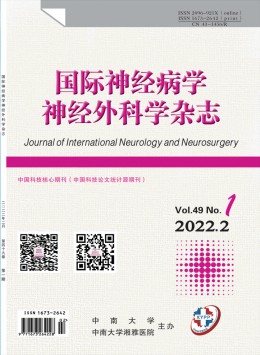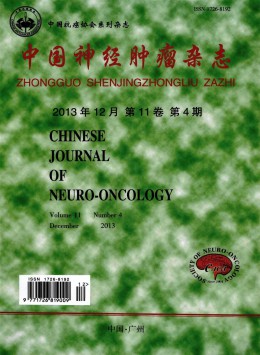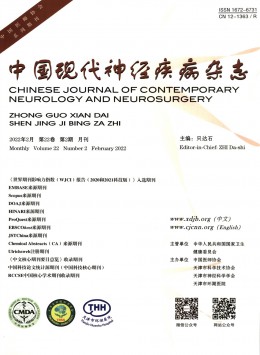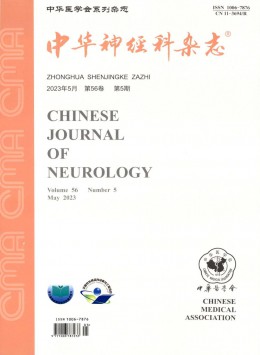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范文
【摘要】目的:我們將收住院的256例腦卒中患者發生卒中后抑郁(PSD)進行了研究,目的是提高臨床醫師及患者對腦卒中后抑郁的認識,為早期發現和治療提供更多的信息。 方法:將256例腦卒中患者在疾病峰期進行神經缺損評分,分析與抑郁癥的關系及CT損害部位與抑郁癥的關系,抑郁癥的發生、臨床特點及治療反應進行探討。結果:本組腦卒中后抑郁的發病37.5%(96/256), 其中73例(76%)發生在6個月以內,左額葉及左基底節區62例,右額葉及右基底節區34例,經治療后79例明顯改善 結論腦卒中后抑郁的發病率高, 抑郁常出現于卒中急性期,左側額葉和基底節區損傷的患者卒中后抑郁癥發生率 高,通過有效的抗抑郁治療,達到提高精神狀態,恢復正常心境,進而改善和促進軀體功能恢復。
【關鍵詞】【關鍵詞】腦卒中;抑郁;患病率;影響因素
長期以來,腦血管意外(又稱腦卒中)一直是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致死率和致殘率很高的疾病之一。隨著醫學的發展和人們對腦血管意外認識的提高,腦卒中本身所導致的死亡率和致殘率呈明顯下降趨勢,而腦卒中后的抑郁癥卻成為阻礙病人神經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恢復的重要因素,也是腦卒中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嚴重病人可能會產生輕生的念頭,如不及時防范,部分病人可能導致自殺的后果。國外對醫院腦卒中患者的研究發現抑郁的患病率為31%~52%[1],國內卒中后伴抑郁癥發病率的報道為25%~80%[2,3]。PSD不僅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導致出現種種不良的心境體驗和軀體功能障礙[4],還影響患者神經及肢體活動功能的康復,且PSD患者的死亡率高于非PSD患者[5]。我們將收住院的96例PSD的發病率,分析與抑郁癥的關系及CT損害部位與抑郁癥的關系,抑郁癥的發生、臨床特點及治療反應進行探討,目的是提高臨床醫師及患者對本病的認識,為早期治療提供更多的信息,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選擇2005年3月~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腦卒中患者256例,其中男131例,女125例,年齡45~82歲,平均62.5歲。腦出血108例,腦梗塞148例,全部病例符合全國第四次腦血管病會議診斷標準[6]。并經頭顱CT或/及頭部核磁(MRI)證實。發病后存活30天以上。觀察1~6 月。抑郁癥診斷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中抑郁病的診斷標準[7],分輕、重二型。除外昏迷、失語、智能損害和既往有腦器質性疾病者。病灶位于左半球118例,右半球105例,雙半球33例;單發病灶159例,多發病灶97例;首發卒中75例,復發卒中181例。
1.2 方法
1.2.1 抑郁程度評分: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DS)[8]評分,SDS總分乘1.25得標準分,以標準分來評定,50~59分為輕度抑郁,60~69分為中度抑郁,70分以上為重度抑郁。
1.2.2 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采用神經功能缺損量表(CSS)[9]評定腦血管病嚴重程度,0~15分為輕度,16~30分為中度,31~45分為重度。
1.2.3 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中風評分表[10],在疾病峰期進行神經缺損評分,分析與抑郁癥的關系及CT損害部位與抑郁癥的關系,抑郁癥的發生、臨床特點及治療反應。
1.2.4 統計學處理:采用χ2檢驗,t檢驗。
2 結果
2.1 卒中后抑郁發生率:全組256例,發生抑郁者96例,其發生率為37.5%,其中輕型45例(46.87%),中型40例(41.67%),重型11例(11.46%)。急性期發生率46例(47.91%),急性期后至6個月內發生者27例(28.12%),6個月后患抑郁癥23例(23.97%)。
2.2 卒中后抑郁與卒中性質的關系:腦梗塞并發抑郁癥者52例,發生率35.12%(52/148),神經缺損評 (13.4±4.2)分,腦溢血合并抑郁癥者44例,發生率40.74%(44/108),神經缺損評分為(13.9±4.9)分,兩者差異無顯著性(P>0.05)。首發卒中者發生抑郁18例,發生率24%(18/75),復發卒中者發生抑郁78例,發生率43.09%(78/181),兩者差異顯著 (P
2.3 卒中后抑郁與CT損害部位:左大腦半球62例,占52.54%(62/118)。右大腦半球34例,占32.38%(34/105)。左額葉及左基底節區42例,右額葉及右基底節區28例, P值
2.4 治療:將96例卒中后抑郁患者分成對照組和治療組,兩組在抑郁程度和神經功能缺損程度比較無明顯差別(見表1),(P>0.05)。對照組給予神經內科藥物治療,治療組在上述治療方法基礎上,加用氟西汀20mg/d,連續8周。在治療后4周和8周再進行抑郁程度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定 (見表2)。運用軼和檢驗進行統計學處理。
3 結果
在對照組, 治療4周和8周后抑郁程度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和入院時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在治療組,氟西汀治療4周后,抑郁程度減輕(P
4 討論
腦卒中抑郁癥是腦卒中患者的常見并發癥, ,多數研究認為,抑郁常出現于卒中急性期,但也可發生于卒中后1~2年,關于卒中后抑郁癥的發生機制還尚未十分明確[11],多數學者認為[12]與社會心理因素和神經生物學因素有關。有專家認為腦低灌注與卒中后抑郁的嚴重程度有密切關系。其中左側額葉和基底節區損傷的患者卒中后抑郁癥發生率 高, 是由于大腦損傷的不對稱性對卒中后抑郁癥的發生有直接影響。左側卒中同右側相比,可以引起相對較輕的5-羥色胺能和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元的破壞,從而導致了兩種神經能的降低,從而引起抑郁。卒中后抑郁在腦梗塞或腦溢血患者中發病率無明顯差別(P>0.05),同時卒中后抑郁癥的發生有它的外在因素,它與卒中前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及腦卒中導致的社會、情感、智能障礙和既往有腦卒中、抑郁癥史密切相關,而與年齡、性別、人種、社會階層無關。由于各種原因,急性期軀體功能無顯著改善,在慢性期,患者負性心理反應日漸突出,這是發生抑郁的第二個高峰期,一般在3個月以后,尤其是多次復發或長期恢復不良是抑郁的重要致患因素。本組6個月后仍表現抑郁者多屬多病灶、復發病例,CT表現為多次、多發病灶者占43.09%(78/181),表明多次腦卒中復發對患者心理影響可能有負性累加作用。抑郁癥的出現對于神經功能缺損的恢復或生活狀況的改善均不利,因此要重視對抑郁癥的預防和治療,住院期間發現患者有抑郁傾向、焦慮或淡漠等負性情緒時,要及時給予心理干預[13]及藥物治療。氟西汀是一種新型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類抗抑郁藥,可以有效地改善或消除卒中后抑郁癥狀,使患者樹立康復的信心,因此PSD患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可減少卒中后的致殘率及死亡率,使患者早日回到家庭與社會當中。
參考文獻
[1] Kauhanen ML,Korpelainen JT,Hiltunen P,et al.Poststroke depression correlates with cognitive imoairment and neurological deficits[J].Stroke,1999;30(22):1875-80
[2] 周盛年,于會艷,劉黎青,等.腦卒中后抑郁[J].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04;17(3):154
[3] 許南艷,江先娣.腦卒中后抑郁狀態的隨訪研究[J].現代康復,2000;3(9):1330-1
[4] 蔡焯基.抑郁癥-基礎與臨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20-5
[5] House A,Knapp P,Bamford J,et al.Mortality at 12 and 24 months after strok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t 1 month[J].Stroke,2001;32(6):696-701
[6] 中華醫學會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腦血管疾病分類診斷要點.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376-379
[7] 中華醫學會全國精神分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第三版.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87-100
[8] 王向東,王希林,馬 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91-253
[9] 孟家眉.對腦卒中臨床研究工作的建議[J].中華神經精神科雜志,1988,21(1):57
[10] Wityk RJ,Pessin Ms,Kaplan RF,et al.Serial assessment of acute stroke using NIH stroke scale.Stroke,1994,25(2):362
[11] 劉胡園,朱仁祥.卒中后抑郁與神經功能關系的研究.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2004,21(2):183
[12] 趙康仁,韓泰然.卒中后抑郁[J].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02;15(1):60
第2篇: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范文
腦梗死是指各種原因所致的腦部血液供應障礙,導致腦組織缺血缺氧壞死,出現相應神經功能缺損[1]。我院采用自由基清除劑依達拉奉治療急性腦梗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2007年5月至2008年5月我院神經內科的急性腦梗死病人128例為研究對象,均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會議通過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2],并均經頭CT或MRI確診。并符合以下入選標準:臨床為頸內動脈系統腦梗死;首次發病或既往發病的肢體癱瘓后遺癥不影響神經功能評分的再次發病;18~80 歲的住院病人,性別不限;起病48 h以內;無全身嚴重并發癥;頭顱CT排除腦出血。除外過敏體質、血液病、嚴重心肝肺腎功能不全及嚴重精神疾病及癡呆者。將128例病人用抽簽法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64例。治療組64 例中,男35例,女29例,年齡49~78 歲,平均(66.1±5.2)歲,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29.22±7.24。對照組64例中,男40例,女24 例,年齡51~79 歲平均(68.7±4.4) 歲,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29.76±7.68。兩組在性別、年齡、病程、病情分度、既往史及伴發病情況、實驗室檢查方面均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對所有入選病例隨訪3 個月。
1.2 治療方法 兩組基礎治療相同,給予阿司匹林片每天100 mg口服,脈絡寧注射液20 mL加0.9%氯化鈉250 mL靜脈滴注,每日1 次,連續14 d;同時,根據病情使用降血壓、降血糖藥和脫水劑,保持水電解質平衡。治療組在以上治療的基礎上加用依達拉奉注射液30 mg加0.9%氯化鈉250 mL靜脈滴注,每日2 次,連續治療14 d;對照組加用胞二磷膽堿注射液0.75 g加5%葡萄糖250 mL靜脈滴注,每天1 次,連續治療14 d。
1.3 臨床療效判斷
1.3.1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 根據第四次腦血管病會議通過的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2]379-383,在治療前及后3 、7 、14 d各評分1 次。14 d時療效按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分值減少及評定時病殘狀態綜合評定[2]379-383。基本痊愈:神經功能缺損評分(NDS)降低90%以上,病殘程度0級;顯著進步:NDS 減少46%~89%,病殘程度1~3級;有效:NDS減少18%~45%;無效:NDS減少不足17%,臥床病例,病殘5 級以上。總有效率為(基本痊愈+顯著進步+有效)。
1.3.2 日常生活活動(ADL)評定用Barthel指數(BI)記分法[3]評定治療前、治療21 d后、治療3 個月后的生活質量。
1.4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采用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顯著性,P<0.01為差異有高度顯著性。
1.5 副作用 兩組在治療前及治療后第14 d各檢測血常規、尿常規、肝腎功能。治療期間密切觀察并記錄各種副作用。
2 結
果
2.1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 見表1。表1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比較注:*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 **與對照組比較有高度顯著差異,P<0.01
2.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2。
表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組 注:對照組比較P<0.01;兩組總有效率比較χ2=7.385,P=0.007
2.3 兩組BI指數評分 見表3。表3 兩組BI指數評分比較注:與對照組比較 P<0.05
2.4 副作用 治療組有2例、對照組1 例谷丙轉氨酶略增高,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余無異常發現。
3 討
論
急性腦梗死病灶由中心壞死區及周圍缺血半暗帶組成。如果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缺血半暗帶血流,該區腦組織損傷是可逆的,神經細胞仍可存活并恢復功能[1]。但是此可逆性是有時間限制的,腦缺血超早期治療時間一般不超過6 h[2]。臨床上能在治療時間窗內入院接受治療的患者非常少。如果腦血流再通超過時間窗,腦損傷可繼續加劇,甚至產生再灌注損傷。目前認為,再灌注損傷主要是通過引起自由基過度產生及“瀑布式”連鎖反應等一系列變化,導致神經細胞損傷[3]。
依達拉奉是一種新型自由基清除劑,具有保護腦神經,抑制由腦梗死灶的血流量減少和水溶性及脂溶性自由基引起的脂質過氧化的作用[4];可以防止腦血管內皮細胞受損,抑制缺血性腦水腫,改善神經功能[5]。本研究結果顯示,依達拉奉治療急性腦梗死的有效率為90.62%,明顯優于對照組(P<0.01);能降低急性腦梗死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提高急性腦梗死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評分,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差異(P<0.01),90 d時治療組改善生活質量遠優于對照組(P<0.01)。不良反應發生率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表明依達拉奉治療急性腦梗死,不僅可以改善近期臨床效果,而且可以改善遠期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是一種安全有效的藥物,可在臨床中推廣使用。
參考文獻
[1] 賈建平.神經病學[M].第6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175-177.
[2] 王新德.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及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1995)[J].中華神經科雜志,1996,29(6):379-383.
[3] Hacke W,Biuhmki E,Steiner T,et al.Dichotomized ellicacy end points and plobal end point analysis to the ESASS in tention to treat date set[J].Stroke,1998,29:2037-2075.
第3篇: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范文
南方醫科大學附屬鄭州人民醫院 神經內科一病區,河南鄭州 450003
[摘要] 目的 研究急性腦梗死與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產生的危險因素,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方法 通過頭顱磁共振檢查,將患者為A組急性腦梗死組和B組非急性腦梗死組,比較兩組間危險因素的差別,并研究急性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態。 結果 男性、吸煙史、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超敏C反應蛋白(Hs-CRP)在兩組間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急性腦梗死組不穩定斑塊檢出率高于對照組(P=0.013)。結論 男性、吸煙史、空腹血糖值較高為急性腦梗死的危險因素。此外,急性腦梗死患者不穩定斑塊檢出比率增高。
關鍵詞 動脈粥樣硬化;不穩定型斑塊;危險因素;腦梗死
[中圖分類號] R743.3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4(a)-0056-02
心腦血管疾病成為人類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腦梗死因其高致殘率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與腦梗死存在直接關系[1]。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性質及管腔狹窄情況與腦梗死有明顯的相關性[2]。通過頸部血管彩超可判斷頸部血管斑塊的性質及管腔狹窄程度,其操作簡單、價格低廉,越來越受到臨床的重視。為研究急性腦梗死與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產生的危險因素,及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該研究2012年12月—2013年8月通過研究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與腦梗死之間的關系,提出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危險因素,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為該院住院的97例行頸動脈超聲檢查,并完善相關生化指標檢測,排除近期存在感染、嚴重肝腎功能異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處于應激狀況的患者。共收集97例,其中急性腦梗死組44例,平均年齡(62.88±11.957)歲,男33例,女11例;非急性腦梗死組53例,平均年齡(64.94±11.631)歲,男18例,女35例。
1.2研究方法
①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糖尿病、腦卒中、冠心病、吸煙、飲酒)通過病歷資料獲得。生化指標通過實驗室檢查獲得,每例患者均進行3.0T頭顱磁共振(MRI)檢查,根據彌散像(DWI)結果有無急性梗死病灶,分為急性腦梗死組(A組)和非急性腦梗死組(B組)。
②所有患者均進行頸部血管超聲檢查,檢查血管包括頸總動脈、頸內動脈、頸外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觀察血管內膜、管腔內有無斑塊,及斑塊的性質。將不規則、不均回聲、低回聲斑塊、混合回聲斑塊定義為不穩定斑塊。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16.0統計分析軟件,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取Mann Whitney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結果
2.1急性腦梗死組危險因素分析
急性腦梗死組男性患者比例為75%,明顯高于非急性腦梗死組(3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1。此外,急性腦梗死組吸煙患者比例(50%)明顯高于非急性腦梗死組(2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從表2中可以看出,急性腦梗死組的空腹血糖值、超敏C反應蛋白(Hs-CRP)值明顯高于非急性腦梗死組(P值分別為0.037,0.021),此外,急性腦梗死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值明顯低于非急性腦梗死組(P=0.01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2急性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特征
急性腦梗死組患者44例,通過頸部血管彩超檢出不穩定斑塊為36例,檢出率為81.8%,非急性腦梗死組患者共53例,不穩定斑塊共檢出31例,檢出率為58.5%,兩組間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3),見表3。
3討論
頸動脈粥樣硬化與腦梗死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缺血性腦血管病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發生率明顯增高[3]。有研究提出[4-5],急性腦梗死伴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患者炎性標記物Hs-CRP和IL-6數值明顯升高,且與年齡和高血壓之間明顯相關。血清Hs-CRP可以反映急性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的嚴重程度。此外,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位置、性質與腦梗死具有明顯相關性,低回聲、易出血、變化快、體積短期內增加的不穩定性斑塊引發腦梗死的危險性最高[6]。吸煙、高血糖可加重頸動脈粥樣硬化,從而增加發生腦梗死的危險。HDL為動脈粥樣硬化的保護性因素,可加速肝臟內膽固醇代謝。
該研究發現男性、吸煙史患者較易發生腦梗死,既往研究結果指出男性患者吸煙率明顯高于女性[7],吸煙易導致不穩定斑塊的產生[8],因此男性患者更易產生不穩定型斑塊,從而產生急性腦梗死。此外,急性腦梗死患者組空腹血糖值、Hs-CRP明顯高于非急性腦梗死組,提示空腹血糖值高為急性腦梗死的危險因素,且炎性因子的升高與急性腦梗死相關,驗證既往研究結果。該次結果指出非急性腦梗死組的HDL值明顯高于急性腦梗死組,驗證HDL為動脈粥樣硬化的保護性因素之一。急性腦梗死組不穩定型斑塊檢出率為81.8%,明顯高于非急性腦梗死組患者組(58.5%),進一步驗證不穩定型斑塊為急性腦梗死的危險因素之一。
綜上,頸動脈超聲對頸動脈斑塊的檢出,預防急性腦梗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男性、吸煙史、高血糖患者更易發生腦梗死,因此,通過頸動脈超聲檢查,配合危險因素篩查,極大推進腦梗死篩查、防治工作的開展。
參考文獻
[1]王志曄,張作念,顧偉,等. 急性腦梗死患者血漿溶血磷脂酸、總磷脂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改變及其與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關系[J]. 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09,22(5):368-370.
[2]華揚,鄭宇,凌晨,等. 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因素與頸動脈狹窄和缺血性卒中的相關性[J]. 中國腦血管病雜志, 2004,1(2):69-72.
[3]唐奇. 頸部血管彩超對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評價[J]. 中國實用醫藥,2009,4(9):13-14.
[4]張俊華,蘇建華. 急性腦梗死伴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相關因素臨床觀察[J]. 長治醫學院學報,2012,26(1):27-29.
[5]溫慧軍,楊金鎖,張建軍. 急性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與血液炎癥因子水平的關系[J]. 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12,25(1):54-56.
[6]董秦川,張勇. 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與腦梗死的相關性研究[J]. 華南國防醫學雜志,2012,26(1):83-85.
[7]Ansari R, Khosravi A, Bahonar A, et al. Risk factors of atherosclerosis in male smokers, passive smokers, and hypertensive nonsmokers in central Iran[J]. ARYA Atheroscler,2012,8(2):90-95.
第4篇: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范文
[關鍵詞] 東莞外來務工人員;腦卒中;危險因素;預警信號知識水平
[中圖分類號] R743.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4)13-5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pidemiological status of knowledge level of Dongguan migrant workers regarding risk factors and early warning signals of cerebral apoplexy. Methods According to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principle, simple cluster sampling was applied to randomly select 10,000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quota allocation of the amount of migrant workers. Knowledge of cerebral apoplexy,risk factors, early warning signals,knowledge sources and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Cognitive status of Dongguan migrant workers regarding knowledge of cerebral apoplexy,risk factors and early warning signals was showed that: Cognitive status was the highest for the knowledge of cerebral apoplexy,and the lowest for early warning signals.The knowledge sources were mainly from relatives, friends,and TV,but the source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internet,school education,doctors and books were extremely deficient. Conclusion Paths for Dongguan migrant workers to acquire knowledge in risk factors and early warning signals of cerebral apoplexy are few, and related medical knowledge level is low. Therefore,a complete range of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so as to enhance the health level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alleviate their life burdens.
[Key words] Dongguan migrant workers;Cerebral apoplexy;Risk factors;Knowledge level of early warning signals
腦卒中作為神經系統疾病,其發病率、致殘率高,復發率及死亡率頻率維持高頻狀態,成為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一種常見病,并且發病率年齡日趨年輕化。現代流行病學研究證明:在中國大陸,每年新發腦卒中有150萬~200萬的病例,年發病率為116/10萬~219/10萬,年死亡率為58/10萬~142/10萬,占人口死因的第二位,在不少城市中已占首位,存活的卒中患者中約3/4留有不同程度的殘疾。這種后遺癥嚴重影響患群的生活質量,降低患群的健康狀況,不僅給家庭帶來壓力,也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1]。腦卒中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盡管其癥狀和體征因病變發生的性質、部位、面積不同而有差別,甚至差別巨大,但是基本預警信號諸如一側肢體僵硬、麻木,頭痛不止,視覺模糊,昏厥,嘔吐等發病現象,又容易被患群忽視為其他普通急癥,認識不清也認識不足自己得的就是腦卒中,拖延就診而錯過最佳治療時機。據北京地區觀察數據顯示,全市大中小型醫院,及時收治的腦卒中患者幾乎為零。24h可觀察的北京大醫院統計數據表明,6h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到診率只有50%,其他都因延誤送治而出現生命危險,造成一個個家庭的遺憾。武漢城區統計數據表明,急性腦卒中患者發病后3h內送治的僅占34%。給家庭造成遺憾的最重要的根本原因就是腦卒中基本知識的普及存在缺位,人們主動學習、主動關心的程度不夠,缺乏早期癥狀的識別能力,淡薄急救治療的意識[2]。本研究通過全面了解東莞外來務工人員腦卒中危險因素、預警信號知識水平現況,并了解其信息來源,為今后在東莞外來務工人員中有針對性地開展腦卒中知識宣傳教育工作準備科學根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我們選擇東莞外來務工人員比較密集的厚街鎮、大朗鎮和長安鎮三個鎮區的不同企業(包括建筑工地、服務行業、工廠等)年齡18~50歲,在東莞工作3個月以上且為外地戶口的部分外來務工人員。
1.2 研究方法
按照多階段隨機抽樣原則,采用單純整群抽樣的方法,在東莞市外來務工人員比較密集厚街鎮、大朗鎮和長安鎮為的鎮區不同企業中進行抽樣。將每個鎮區中運營超過3個月以上的建筑工地、酒店、工廠分別進行編號,隨機抽取企業,按外來務工人員數量按額分配名額隨機抽取10 000名外來務工人員。
1.3 調查內容
調查的表格設計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表格框架,其調查問卷內容依據中國國情自行設計,涵蓋4個方面:(1)腦卒中基本常識。主要以調查形式普及腦卒中的發生部位、危險因素及預警信號知識:發生部位包含心、眼、腦、肢體4個選項;危險因素包含精神壓迫癥、吸煙過度、過度肥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高血壓病、高血脂癥、腦動脈硬化、糖尿病、高鹽高脂飲食、缺乏鍛煉、酗酒、遺傳、感染、心臟病、口服避孕藥共15選項;預警信號包含肢體麻痹,視物模糊、單眼失明,說話不靈、飲水嗆咳,劇烈頭痛,理解力下降,昏厥,肢體麻木,站立行走不穩,惡心、眩暈、嘔吐共9個選項,附有干擾預警信號1項:胸悶、憋氣、心慌。(2)腦卒中知識獲取渠道。包括親朋、電視、報紙雜志、網絡、學校教育、醫生、書籍共7項。(3)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年齡(本調查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對年齡的最新劃分標準,將44歲以下人群定義為青年人群,將45~59歲為中年人,60~74歲為年輕老年人)、性別、婚姻(已婚、未婚、其他)、教育程度(根據常規制定方法將小學文化程度及以下定義為初等,將初中及高中、中專文化程度定義為中等,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定義為高等)、職業、月財政收入共6個選項。(4)調查對象本人及家屬遺傳病史。填寫方式以“是”或“否”填寫。
1.4 調查方法
調查員為經過統一培訓的神經內科醫生,按統一指導語和實施步驟,以100人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采用現場發放、現場回收的方式,調查表收回后進行檢查,剔除無效調查表。
1.5 統計學分析
采集來的原始數據核對無誤后,采用Visum Foxpro 6.0軟件系統建立相關數據庫,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終結性分析。一般材料采用描述性分析,計量資料均以()表示,計數資料組問采用單向方差分析,全部數據檢驗均采用雙側檢驗,多變量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P
2 結果
2.1 認知狀況
經過調查,東莞外來務工人員對于腦卒中知識、危險因素、預警信號的認知狀況見表1。其中對于腦卒中知識的認知最高,預警信號的認知最低。見表1。
2.2 應對方式狀況
東莞外來務工人員腦卒中知識獲得渠道主要為親朋的口碑與電視的廣告,而更為廣泛的渠道如報紙雜志書籍基本不看、網絡主打游戲、學校教育程度不高、不愿與醫生打交道,對腦卒中的基本知識了解相對不多。見表2。
3 討論
全世界比較起來,我國腦卒中有兩個比較大的特點:一是歐美發病率都在降低,而我國還在持續上升;二是復發率排在全世界較高位置。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國腦卒中的基本知識普及不到位,患者群沒有預防常識,一般性醫院治療水平有限,缺乏應有的治療方案和經驗,特別是專業醫生對此新業務培訓不到位,認識不足,使得我國腦卒中的防治總體水平偏低。
現代流行病學發現,公眾接受了良好的腦卒中知識教育,大腦中充分予以重視,就可以做好預防措施,增強對自身健康的關注,進而降低腦卒中的發病率,在爭取時間及時送治的情況下,死亡率和致殘率也得以大大降低 [3]。進入21世紀,各國腦血管病專家依據臨床和動物實驗得出的數據提出,80%左右的缺血性腦卒中應進行超早期治療,這樣才能贏得治療時間,才能增加療效、減少致殘率。而國內很多地區腦卒中的知識普及還沒有覆蓋到位,處于腦卒中只是真空階段,許多腦卒中病人無法意識到中風危險因素、預警信號,即使發病了也會誤判導致延誤入院治療的黃金時間。這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治療與預防要并重,特別是綜合預防,醫療管理行政部門要予以高度重視,投入相當力量,加大教育力度,及時迅速推廣普及腦卒中基本知識,確保每一位公眾都了解腦卒中的基本情況。相信通過廣泛開展健康教育,公眾對腦卒中的基本知識具備,早期識別能力增強,急救意識得到培養,在全社會建立和健全了腦卒中的急救網絡情況下,就會及時判清腦卒中的發病情況,及時送診,微博患者爭取活命時間,這樣腦卒中的致殘率和致死率就會大大降低[4-5]。
隨著全世界對腦卒中的發病危險因素的廣泛研究與交流,基本形成共識,包括如高齡、性別、鐮狀細胞病、家族史、種族、氣候、纖維肌性發育不良和卒中家族史等不可干預的危險因素,此外還有如心臟病、糖尿病、頸動脈狹窄、感染、酗酒、TIA、高血壓、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等可控制的危險因素也日益成為腦卒中發病的誘因。控制卒中危險因素,是腦卒中一級預防和預防卒中復發的關鍵[6]。近年來,國內外努力的結果表明:對公眾及時宣傳普及腦卒中基本知識,幫助公眾及時辨清腦卒中的表征,是降低腦卒中發病率,杜絕致殘率、死亡率的根本措施[7-8]。美國、法國、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學者先后都進行過腦血管病公眾知識水平調查,并探討各種宣傳手段的效果[9-12];2004年郭偉等[13]在我國青島市市區居民中行中風危險因素、預警信號知識水平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在經濟比較發達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島市區居民中,中風危險因和預警信號知識水平仍較低,由此推測,在我國經濟比較落后和文化素質比較低的地區的人群如工人、農民,他們的中風危險因和預警信號知識水平可能更低,而目前國內暫無學者進行該方面的研究。
東莞外來務工人員700萬,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缺乏衛生保健意識和知識,近期發現該人群的腦卒中的發病率較高,且患病后不能及時就診或因經濟原因不能得到最好的醫治,因此,留下后遺癥的較多,給家庭帶來嚴重的負擔。本文結果顯示東莞外來務工人員對于腦卒中知識、危險因素、預警信號的認知狀況見表1。其中對于腦卒中知識的認知最高,預警信號的認知最低。東莞外來務工人員對于腦卒中知識認知的知識來源主要為親朋與電視,在報紙雜志、網絡、學校教育、醫生、書籍中的了解相對不多。
總之,我們希望通過以后針對性的宣教工作,能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腦卒中知識,盡量降低該人群卒中發病率,提高卒中治療率,從而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健康水平和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具有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普及公眾腦卒中基本知識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宣傳到位,普及到位,我們才能構建更為有效的腦卒中公眾健康教育平臺。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撰寫組.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0[J].中華神經科雜志,2010,2(1):10-16.
[2] Jones SP,Jenkinson AJ.Strok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evidence[J].Age Ageing,2010,39(1):11-22.
[3] 張愛香,韋君同.缺血性腦卒中危險因素研究進展[J].吉林醫學,2010(17):2678-2681.
[4] Stroebele N,Müller-Riemenschneider F.Knowledge of risk factors,and warning signs of stroke: a systematic review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J].Int J Stroke,2011,6(1):60-66.
[5] Darin B,Zahurancc MD.Stroke heath and risk education SHARE)pilet project.feasibility and need for church-based stroke health promotion in a Bi-Ethnic Community[J].Stroke,2008,39:1583.
[6] Nicol MB,Thrift AG.Knowledge of risk factors and warning signs of stroke[J].Vasc Health Risk Manag,2005,1(2):137-147.
[7] Müller-Nordhorn J,Nolte CH.Knowledge about risk factors for stroke: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with 28090 participants[J].Stroke,2006,37(4):946-950.
[8] Das K,Mondal GP.Awareness of warning symptoms and risk factors of strok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in survivors stroke[J].J Clin Neurosci,2007,14(1):12-16.
[9] Hwang SY,Zerwic JJ.Knowledge of stroke symptoms and risk factors among Kore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Res Nurs Health,2006,29(4):337-344.
[10 ] Neau JP,Ingrand P,Godeneche G.Awareness within the French population concerning stroke signs, symptoms,and risk factors[J].Clin Neurol Neurosurg,2009,11(8):659-664.
[11] Pontes-Neto OM,Silva GS.Stroke awareness in Brazil:alarming results in a community-based study[J].Stroke,2008,39(2):292-296.
[12] Pandian JD,Jaison A.Public awareness of warning symptoms,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of stroke in northwest India[J].Stroke,2005,36(3):644-648.
第5篇:神經病學和神經內科差別范文
關鍵詞 淡漠癥狀 額顳葉癡呆 行為變異 早期診斷
中圖分類號:R749.16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6-1533(2016)13-0056-03
The importance of apathy symptom for early diagnosis of behavioral variant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one case report
ZHAO Xiaohui1*, LIU Wei1, WU Yan2**
( 1.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eijing 100730, China;
2.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 manifests widely different symptoms in early stage, so it is often unidentified in the beginning or easily misdiagnosed as psychosis, thus its treatment will be delayed.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cours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outcome of a FTD patient, and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apathy symptom for early diagnosis of behavioral variant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KEY WORDS apathy;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behavioral symptoms; early diagnosis
額顳葉癡呆是早發型癡呆的常見病因,因其早期癥狀類似精神障礙而影像學改變較隱匿,識別率較低,但對該疾病進行早期診斷和干預可以顯著改善其功能狀態,延緩疾病進展。研究表明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類藥物和美金剛都可能有改善作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需要謹慎使用,而膽堿酯酶抑制劑則無效或可加重癥狀[1]。故臨床醫生有必要及時了解該疾病的診治進展,提高識別率。本文以一例經住院觀察、治療4個月后被識別并有顯著療效的行為變異型額顳葉癡呆患者為例,闡述額顳葉癡呆早期診斷的重要價值。
1 病史摘要
患者男性,45歲,因“行為紊亂2年余,猜疑、攻擊行為1年,加重半月”于2015-08-22入精神專科醫院住院治療。
患者2013年起逐漸有異常舉動,如半夜打通親友的電話又不出聲,到親友的單位門口站很久,去弟弟家又不進門不說話等。2014年下半年患者無故認為樓上老伯半夜故意吵自己,用榔頭砸壞其大門,經家人勸說未再糾結于此。2015年8月再次猜疑該鄰居,認為他跟蹤自己、吵自己,故經常上樓踢門,敲打樓上的空調架子,不聽勸說。
患者既往有過痛風發作,余無殊。病前性格內向,智能好,99年碩士生畢業,從事工程師工作,工作表現優異。2009年離婚(原因不詳),2010年因工作不能勝任被辭退離職。此后患者獨居,生活能自理,日間外出活動,如去圖書館等,未再工作。無精神障礙及癡呆家族史。
2 診療過程
入院時精神檢查:意識清,儀表尚整潔,接觸被動,不合作,表現緘默不語,面無表情,情感淡漠,主動違拗。體格檢查未見異常。血尿糞常規、生化、甲狀腺功能、VitB12、梅毒血清學檢查指標均正常,腦電圖、核磁共振(MRI)(圖1)未見異常。
入院幾天后,精神檢查時能引出可疑物理性幻聽、片段關系及被害妄想,稱:“樓上鄰居弄出噪音,是針對我的”、“影響了我的生活環境”、“就是在我要睡覺的時候弄出聲音讓我睡不著”、“聲音很輕,只有我家能聽到”、“房子會震動”、“儀器弄的”等等,對象不泛化,無系統推理過程,“就覺得是他,因為看到他別扭”,追問下能簡單講述過去曾因水管破裂與該鄰居有過糾紛。在病室里總體表現尚安靜,少有主動言語動作,經常長時間保持不變的站姿或坐姿,個人衛生及儀表維持基本如常人,對病友、醫務人員和家人均無情感表達。對檢查智能的常規問題能給出正確回答,作答遲緩。韋氏智力測驗:智商80分(正常范圍中下水平);韋氏記憶測驗:記憶商數30(重度缺損);神經精神問卷(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NPI)評分16分。
擬診“精神分裂癥”,予以改良電痙攣治療(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MECT)和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約2個月(利培酮日高量6 mg,后換用舒必利日高量0.8 g),患者癥狀變化不大,醫生查房時會反映情緒緊張,“我覺得很緊張很不安”、“我覺得腦部壓力很大,人有點難過”、“醫生護士的動作好像跟我有關”等等,臨時予勞拉西泮片口服能緩解。并漸有上肢震顫,有時保持傾斜站姿數小時,有“磁性步態”,常站在醫生必經之處望著醫生,有期待表情但數問不答。換用阿利哌唑日高量10 mg,言語似有增加。行簡易精神狀態檢查表(minimum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檢查合作但遲緩,得分29(正常30分,回憶能力扣1分)
入院2.5個月時請神經內科會診,體格檢查見四肢肌力4級,雙手平舉明顯抖動,雙側巴氏征(-),等位征(+),讀片發現有雙側額顳葉萎縮,病變對稱,頂葉萎縮不明顯。考慮額顳葉癡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FTD)伴帕金森綜合征待排,予停用阿立哌唑,改用美金剛5 mg bid,美多芭1/4片tid,緘默及刻板行為略加重。4周后改用舍曲林100 mg/d,0.5個月后患者行為開始改善,不再長時間站立,偏斜站姿很少出現,主動幫忙擦桌子、洗碗并收到規定位置,周圍人聊天時偶爾插話,經常主動找護士聊兩句或去活動室看電視。用舍曲林7周時交流明顯改善,回答問題時語句不再簡短,回答前沉默的時間明顯縮短。能主動詢問出院后的治療安排并要求減少服藥次數,常有愉快、急切等情感表達。自述自2009年起表達有困難,與妻子交流減少“見面都不大說話”,自覺難以應付工作及婚姻問題,心情不好時感覺鄰居跟自己作對。未引出幻覺和妄想,自認既往沖動行為是不正常的表現。自覺治療有幫助,如頭暈沒有了,情緒不那么煩躁了。步態穩,步幅及步速基本正常,雙臂伴隨動作少。指鼻(-),反擊征(-),肌張力檢查配合度差,鐘擺試驗(+)雙手震顫(+)。NPI評分7分。復查MRI,仔細對照可見病變較入院時略有加重(圖2)。2016-02-26出院。
3 討論
額顳葉癡呆是一組以進行性精神行為異常、執行功能障礙和語言損害為主要特征的癡呆癥候群,是額顳葉變性病(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FTLD)的主要表現。臨床表現差異很大,國際上分為3種主要臨床亞型,行為變異型額顳葉癡呆型(behavioral variant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bvTFD)以人格和社會行為異常為主,語言障礙相對不突出;而另2種均可歸于原發性進行性失語,表現為詞匯理解或語法障礙,行為異常不突出。2014年發表的《額顳葉變性專家共識》中采用了國際最新的分級診斷標準,臨床表現歸于6大類,分別為:早期去抑制行為、早期出現冷漠和(或)遲鈍、早期出現缺乏同情、早期出現刻板行為、口欲亢進和飲食習慣改變、神經心理測驗表現執行功能障礙而記憶及視覺功能障礙較輕。具備6中之3則診為“疑似bvFTD”,若同時還存在功能受損及影像學證據即可診為“可能bvFTD”,當然也需符合排除標準[1]。新的診斷標準與1998年較嚴格的Neary標準相比,提高了診斷敏感度,有助于bvFTD患者早期獲得診斷[2]。
本例患者起病隱匿,癥狀集中在行為方面,根據有限的病史信息可以明確患者在2010年工作能力下降,2012年出現不恰當的社會行為,2015年間斷出現攻擊、緘默和刻板行為。推測病程不止2年,患者冷漠遲鈍、缺乏共情的癥狀可能在2009年離婚時已有出現(患者癥狀緩解后的自發描述證實了這部分病史)。有神經科體征。妄想短暫存在,不牢固不系統,言語表達減少但思維形式未發現明顯障礙。記憶功能受損相對輕。三種抗精神病藥物及MECT治療均效果不佳,舍曲林治療效果顯著。影像學改變較輕微但局限在額葉和顳葉。符合行為變異型額顳葉癡呆(bvFTD)的國際診斷標準中“Ⅲ可能的bvFTD”。患者說話費力但語義理解、語法和命名能力衰退均不明顯,MMSE檢查時書寫句子表現好(“今天天氣很好,陽光燦爛”),故不符合FTLD的另外兩型。據其少語少動的表現應與抑郁障礙鑒別,但家屬未發現可疑的情緒低落和動力減退,患者也未出現過睡眠和進食的問題,癥狀改善后自述有焦慮抑郁體驗但不持續,且入院初的異常行為和妄想均無法用抑郁障礙解釋,故可排除。因病初有明確妄想和怪異沖動行為,精神分裂癥診斷仍需考慮,但癥狀并非被動體驗、系統性妄想、思維障礙等較為特異的精神病性癥狀,發病年齡晚,針對精神分裂癥的療法均效果不佳,故認為bvFTD是能夠更加完整地解釋患者全貌的診斷。
目前FTLD的治療仍是個難題,現有治療主要用于管理行為癥狀[3],療效參差不齊。支持SSRI(帕羅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蘭)的研究較多[1,3-5]。小劑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藥也有效,但因嗜睡、體重增加、錐體外系反應等不良反應,建議謹慎使用[1]。美金剛在我國共識中是推薦使用的藥物[1],但近兩年有些研究顯示無效[3,5]。另外也有少數研究支持曲唑酮[5]、安非他明、催產素、哌甲酯等[6]。膽堿酯酶抑制劑不被推薦使用[1,3],因為FTLD患者腦內不存在膽堿能遞質系統的異常,臨床研究也未發現有效,還可能導致去抑制和強迫行為惡化[1,5]。
患者初診時沒有口部探索、異常、舉止輕率等明顯的脫抑制癥狀,記憶減退不突出,行為紊亂不持續。這些與過去觀念中典型的額顳葉癡呆臨床表現不夠符合,卻恰恰符合bvFTD的早期表現。國內外多項臨床案例總結顯示,bvFTD的早期表現中淡漠是最常見的癥狀:如駱雄等[7]回顧16例符合FTD的患者中有14例伴發淡漠癥狀;李凌等[8]總結確診FTD的患者14例,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淡漠(13例);顧小花[9]根據癥狀嚴重度評分將bvFTD分為輕度認知障礙組(bvFTD-MCI組)和癡呆組(bvFTD-DEM組),發現兩組的臨床癥狀頻率差別顯著,淡漠/惰性表現在MCI組明顯多見(94.6%),記憶力下降和同情心喪失、言語功能障礙及非特異性精神癥狀則是在DEM組頻率較高。國外研究也有類似發現,Shinagawa等[10]統計FTLD照料者回憶的患者最早出現的變化,頻率最高的是“淡漠或無自發性社會退縮(apathy or social withdrawal of aspontaneity)”,占14.1%。我國共識中也將“早期(最初3年)出現冷漠和(或)遲鈍”作為疑似bvFTD的6類癥狀之一。
因此,淡漠癥狀對于bvFTD診斷的意義雖不特異但非常敏感,精神科醫生在針對淡漠表現的患者鑒別診斷時需注意考慮到bvFTD的可能性。尤其在發病年齡晚(>40~45歲),起病隱襲,病程持續進展,對抗精神病藥物反應不佳,有癡呆家族史或進展性認知損害等特征都是提示可能性的線索[11]。此時尤其需要多方詳細詢問病史,密切觀察患者言行舉止,進行全套認知功能評估,與神經科醫生密切合作[1,12],方能及時明確診斷,給予正確治療,則有望使患者及其家庭顯著獲益。
參考文獻
[1] 中華醫學會老年醫學分會老年神經病學組額顳葉變性專家. 額顳葉變性專家共識[J]. 中華神經科雜志, 2014, 47(5): 351-356.
[2] 盛燦, 李瑜霞, 韓瓔. 行為變異型額顳葉癡呆診斷標準的進展[J]. 醫學研究雜志, 2015, 44(9): 155-158.
[3] Bang J, Spina S, Miller BL. Frontotemporal dementia[J]. Lancet, 2015, 386(10004): 1672-1682.
[4] Herrmann N, Black SE, Chow T, et al. Serotonergic function and treatment of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J]. Am J Geriatr Psychiatry, 2012, 20(9): 789-797.
[5] Wang X, Shen Y, Chen W. Progress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research[J]. Am J Alzheimers Dis Other Demen,2013, 28(1): 15-23.
[6] Nardell M, Tampi RR.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for frontotemporal dementia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Am J Alzheimers Dis Other Demen, 2014, 29(2): 123-132.
[7] 駱雄, 唐牟尼, 郁俊昌, 等. 額顳葉癡呆患者的臨床特征與早期診斷[J]. 臨床精神醫學雜志, 2013, 23(1): 39-41.
[8] 李凌, 張振馨, 袁晶, 等. 額顳葉癡呆患者14例臨床及影像學特點分析[J]. 中華神經科雜志, 2009, 42(11): 742-744.
[9] 顧小花. 行為異常型額顳葉癡呆的臨床分析及早期診斷[D]. 南京: 南京醫科大學, 2015.
[10] Shinagawa S, Ikeda M, Fukuhara R, et al. Initial symptoms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and semantic dementia compar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 Dement Geriatr Cogn Disord, 2006, 21(2): 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