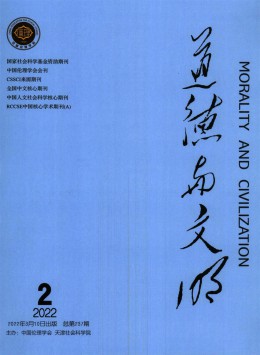道德敘事在思政教育中的價值和運用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道德敘事在思政教育中的價值和運用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借助于道德敘事開展教育,不僅需要教育者精心備故事、生動敘故事和恰當合理解故事,有序把握敘事進程,同時更需從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層次考慮如何運用敘事以充分發揮其在整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一般而言,道德敘事的運用主要有三種形式,其一是把敘事作為輔助性工具,用以說明道理或是引發教育對象學習興趣的點綴敘事;其二是把敘事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起點,借助于敘事提供的背景和素材開展教育活動的起點敘事;其三是以敘事作為教育理念,倡導教育過程敘事化,將理論隱寓于故事,潛移默化地為教育對象所內化,引導其在故事體驗中實現意義反思和素質提升的自然敘事。
1.點綴敘事。點綴敘事是指在教育過程中,敘事主要被作為一種激發學習興趣、說明和論證教育內容的輔助性教學策略。在“活躍氣氛、激發興趣”的教育理念下,教育者依照個人經驗零散地在教育過程中敘述故事,運用故事的情境性和形象性吸引教育對象的注意力和學習興趣,或是用以闡釋和說明某一思想理論。由于缺乏系統的敘事設計,點綴敘事的運用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和經驗性。敘事既可能被置于教育的最初導入階段,也可能被置于某一理論教育內容之前或之后。如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同志針對當時一些戰士和干部只知要革命,不知什么是路線和政策的情況,就借助于“張果老騎驢朝圣”的故事為大家闡述了路線、政策的重要性。首先以敘事開始,他說:“張果老下華山,去蓬萊朝圣,這個人不是凡人,是個仙家,所以,他騎毛驢和我們不同,是倒騎。走著走著,遇到仙人呂洞賓,問張果老去何處?張果老說去蓬萊。呂洞賓驚詫地問:蓬萊在東,你騎毛驢向西,怎么能到?張果老生氣了,認為自己有理,反駁道:我的臉是朝東方蓬萊的!”接著,便說,想要革命的人,如果只是“面朝蓬萊”式的心中有革命,但卻采取“騎毛驢向西”的錯誤路線,是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因此,革命是要講究策略路線的。點綴敘事中,敘事作為輔助性策略往往不具有持續性,也不是教育活動的中心,而是從屬于一定教育內容或教育形式的、一次性孤立存在的“一點一事”。如前面關于“張果老騎驢朝圣”的敘事,主要是用以說明路線策略的重要性,但對于接下來要具體闡釋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路線策略等問題,就不會也不適宜借助于該故事展開了。
2.起點敘事。起點敘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把敘事作為教育活動的起點,進而借助于敘事所提供的背景和素材,開展多樣化拓展教育活動的教育過程。起點敘事中,故事以媒體、語言等方式敘述呈現之后,可能會被作為模擬真實生活的典型情境、承載相關思想理論的形象載體和包含道德問題解決策略的具體脈絡而存在,并因之在隨后的教育活動中發揮著不同作用。作為典型情境,敘事為教育活動提供了角色扮演的生活實驗室,幫助教育對象體驗和感受相關生活情境,豐富體驗,提升認識;作為思想理論的形象載體,敘事為教育活動提供了討論和分析的生活線索,在幫助教育對象聯系生活實現自身理論知識重構的同時,為他們在實際生活情境中運用知識奠定了基礎;而作為問題解決策略的具體脈絡,敘事能夠幫助和引導教育對象不斷豐富和拓展對于自身思想問題產生原因與發展方向的認識,借助于敘事探討各種可能的解決策略并獲得對自身問題解決的領悟。如在關于誠信教育的過程中,教育者以“逃票的博士生找不到工作”的敘事開始,在隨后的教育活動中分別通過“角色扮演、討論辯論、故事續編”等活動,在敘事提供的背景和素材運用中,和教育對象一起就誠信的重要性、誠信的要求和誠信的品德養成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如此,敘事不再是引發教育對象興趣的零散存在,也不是局限于某一教育內容的“一點一事”,而是承載教育條件、貫穿教育始終的持續存在,是基于敘事的就事論理。
3.自然敘事。自然敘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以敘事的理念實施教育,倡導教育過程敘事化,主張通過自然而然地敘述故事而實現教育目標。自然敘事中,敘事不再是點綴,也不再是起點,而是教育本身。與點綴敘事和起點敘事把敘事作為說明和闡釋教育內容的工具、敘事處于邊緣地位相比,自然敘事中敘事成為教育過程的中心任務。這時,教育的重點不是放在如何條分縷析地、符合邏輯地進行理論分析上,也不是放在具體細致的行為指導上,而是把整個教育過程變成敘事過程,力求完整細致地敘述故事本身,注重故事細節的描寫,從故事人物、時間地點到故事發生發展的前因后果,情節完整、矛盾集中、血肉飽滿,希望最大程度地貼近真實生活。當然,教育過程中的自然敘事雖然在本質上和真實生活相吻合,但教育屬性必然要求其在內容豐富性、情節典型性等方面超越自然故事,成為適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類自然敘事。類自然敘事看似自然發生,實則是經由教育者精心設計的、進行過思想政治教育改造的、反映和承載教育目標的道德敘事。與真實故事相比,自然敘事更加注重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相關內容的深度描寫,并凸顯涉及價值沖突和道德選擇的矛盾沖突。其中深度描寫是對故事人物、環境、情節中的某一局部、某一特征、某一細節所作的具體細膩的描述,會使敘事更加貼近生活真實,從而為教育對象提供更多有效進入和理解故事傳遞道德信息的線索和路徑。因為“在深度敘事中,交往個體的聲音、情感行動與意義不僅能被人‘聽’到,而且能被人‘看見’”。凸顯矛盾是在敘事中注重還原、再現并典型化生活中的價值沖突和道德沖突,以激發和促進教育對象對不同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的反思,促進其道德成長。如有教育者在進行“人生價值在于奉獻”的教育時,就直接敘述了2005年感動中國人物叢飛的生命故事,并重點剖析呈現了“助學貧困生卻得不到受助學生回報”的沖突情節,深描了叢飛生病后因受助學生冷漠而產生的矛盾困惑心理,以及后來矛盾困惑心理的解決和人生境界的升華過程。這一敘事雖然沒有伴隨理論分析,但生命敘事的內在時間序列和整體脈絡以及敘事自身的真實自然使教育對象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通過對沖突的體驗、分析和判斷,體會和領悟到奉獻的純潔性和超越性就在于“無回報要求”。
二、需要注意的問題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道德敘事的運用會遇到教育預設與品德生成、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價值引導與生動敘事之間一些不容易處理的關系問題,需要妥善處理。這一問題處理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不斷探討如何在教育中不斷完善道德敘事的過程。1.教育預設與品德生成之間的關系問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為使道德敘事更加合理有序,教育者需事先對敘事環節做出預設性的盡可能的“完美設計”,以既有的程序、固定的框架、一貫的做法,保證敘事各環節的實施及整個過程的順利進行。但是,此種預先設計的敘事模式,容易影響和傷害教育對象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限制教育對象品德養成的內在生成性,阻斷敘事過程應有的開放性和教育者與教育對象之間的動態溝通及價值理解過程,從而使道德敘事陷于被動及僵化的境地。對此,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預見到課堂的所有細節,而在于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巧妙地、在學生不知不覺中做出相應的變動。”因此,道德敘事過程中需保持彈性,既要注意從整體上對敘事及其實施進行勾勒設計,又要注意考慮教育對象認識理解的“前見”基礎及其在教育過程中的主動參與性,在教育者主導性和教育對象主動性、教育預設與品德內在生成之間保持適度張力,以教育機智最大限度地優化教育過程,充分發揮道德敘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和價值。
2.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的有機統一問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教化路徑,其教育內容往往和國家、民族、政黨以及他們的觀念及信仰相關,注重以全知的視角,豪邁宏大的口吻講述著領袖人物、時代英雄、歷史名人以及普通勞動者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無私奉獻”等高尚事跡。這些服務于社會主流價值主題的“宏大敘事”,因為遠離現實生活而為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所質疑和反思。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回歸生活世界本身的過程中,敘事焦點從社會本位掙脫、進入個人敘事以后,生活本身所附著的瑣碎、膚淺、低下和庸俗也隨之而來。如在一些道德敘事中,“宏大敘事”消逝了,看似熱鬧、實則空洞無物的瑣碎敘事,甚至是庸俗敘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變得單薄無力,失去了打動人心的深刻品質。因此,道德敘事必須注意在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之間尋求合適的張力,透過個人敘事貼近教育對象生活,經由個人敘事鏈接拓展至宏大敘事,進而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
3.價值引導與生動敘事的協調一致問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顯的價值取向,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線,倡導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道德敘事,強調通過貼近現實的真實敘事,呈現和敘述生動的自然生活,在一定意義上會使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傾向淡化,趨向中立,甚至可能迷失而成為“單調的事件,無聲的,無感知的,無色的;只是材料的無終止的,無意義的倉促的結合”。那么,這種敘事就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標相悖。為此,在透過敘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時,一定要謹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價值性,在努力呈現故事的生活性與生動性,幫助學生回到生活現場的同時,注意將價值性滲透于敘事的具體語言和故事情節之中,通過故事向學生自然敞開其尚未清楚的價值,并在敘事過程中恰當合理地進行價值引導,聚焦品德提升,啟迪與照亮教育對象未來的生活道路!
作者:潘莉 王翔 單位: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