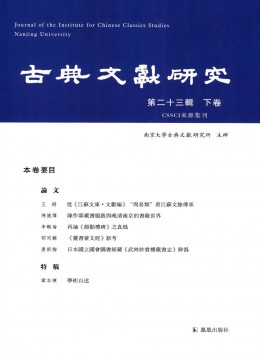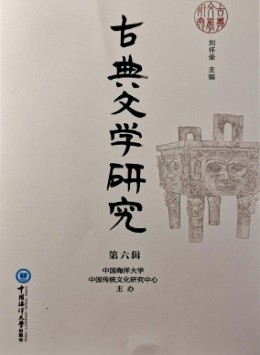古典主義文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古典主義文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文化歸化異化文化負載詞一、引言
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文論研究中發(fā)軔的文化轉(zhuǎn)向也開啟了西方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西方的翻譯理論家們開始關(guān)注文化、政治、權(quán)力關(guān)系、主流詩學等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文化成了翻譯研究的重心,從而使翻譯研究擺脫了靜態(tài)的語言學分析和長期以來的“直譯”與“意譯”,“忠實”與“通順”等無休無止的爭論。文化研究學派在90年代后主導了翻譯研究的潮流。其中,韋努蒂在討論譯者隱身的現(xiàn)狀后,提出了“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開始要解決“翻譯對原作中原語語言和文化汲取的多少和譯作對原作文本差異的保留多少的問題”(Steiner 2001:148)。雖然韋努蒂倡導的“異化”主要用于從弱勢文化向英美強勢文化譯入時英語的翻譯者應采用的翻譯策略。但這也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分析和認識中國古典文學典籍翻譯實踐中“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的運用及其實際效果。本文對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兩種最常見的譯本(楊憲益譯本和霍克斯譯本)中“歸化”與“異化”策略的使用及效果進行個案對比,從而對此類翻譯中的翻譯方法和策略的使用進行有益的探索。
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豐富的文化蘊涵及其翻譯障礙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燦爛的文化積淀從而充滿恒久的魅力,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介紹到世界各國。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所涉及的文化既有共時文化也有歷時文化。所謂共時文化就是這些文學名著成書時的中國文化,所謂歷時文化就是書中涉及與賴以為背景的在成書之前到成書之時的中國歷史文化。這些文化包括姓名文化、職官文化、器物文化、建筑文化、園林文化、醫(yī)藥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語言文字文化、文學藝術(shù)文化、各種宗教文化等。
翻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至少有三大障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shù)和文化。就語言材料而言,《紅樓夢》用的并不是古代漢語材料,嚴格的說,是用淺近的古代漢語寫成的,夾雜著古代漢語成分。盡管如此,它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和現(xiàn)代漢語的語言文字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從而成為翻譯的一大障礙。另外,作者的寫作藝術(shù)手法也是翻譯的一大障礙。《紅樓夢》的寫作藝術(shù)手法出神入化,有時候成為翻譯中不可逾越的障礙。首先,該書采用對稱結(jié)構(gòu),一干多枝的情節(jié)布局,前文伏筆、后文交代的連接方式,人物姓名、語言、詩詞歌賦都與情節(jié)相關(guān)聯(lián)等手法,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演繹歷史事實。從而創(chuàng)下了我國古典小說藝術(shù)手法紛繁復雜之最。其次,曹雪芹筆下的人物的姓氏排行、雅名俗稱、言談舉止、詩詞歌賦、社會交往甚至活動空間都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暗示了人物必然要走向悲劇結(jié)局的命運。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深厚的文化蘊涵無疑成為翻譯的最大障礙。《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集大成者和中國古典文學最高成就的扛之作。《紅樓夢》同樣涉及了成書時中國清代的歷史文化,也涉及清代以前的歷史文化。清代是我國的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由少數(shù)民族滿族入主中原。滿族文化雖然逐漸與中原文化融合,但其本身的文化特色并沒有完全消融。另外,《紅樓夢》還有大量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例如中國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雖從印度引入但已經(jīng)本土化了的佛教文化等。還有對《紅樓夢》成書期的清代康、雍、乾時期的文化研究。康、雍、乾雖是清王朝的鼎盛時期,但由于當時西方已經(jīng)歷了工業(yè)革命和文藝復興的洗禮,中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資本主義萌芽。清王朝已開始走向衰落。《紅樓夢》全書和書中的許多描寫都要結(jié)合這些情況來理解。因此,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翻譯時,譯者必須面對以上所述的諸多翻譯障礙。而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的采用也將產(chǎn)生大不相同的效果。
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翻譯中翻譯策略分析:歸化與異化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翻譯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在當今文化派翻譯理論視角下,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無疑,韋努蒂的歸化與異化論對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翻譯中文化因素的處理有獨特的借鑒意義。
根據(jù)韋努蒂的翻譯理論,《翻譯學詞典》將歸化定義為:在翻譯中采用透明、流暢的風格,以最大限度的淡化譯入語讀者對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譯策略。(Shuttleworth&Cowie,2004:43-44)韋努蒂把歸化看作是英美的主導翻譯傳統(tǒng)。韋努蒂認為歸化是一種對原文文本的種族中心主義刪減以符合歐美譯入語文化價值觀,所以極力反對歸化策略。(Venuti 1995:20)奈達可以說是歸化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最貼近的自然的對等”理論把譯文讀者置于首位。他認為譯文讀者從譯文中獲得的感受應盡可能接近原文讀者從原文中獲得的感受。因此,譯者有責任幫譯文讀者將一些有可能難與理解的信息“改頭換面”,從而使譯文的閱讀與理解輕松自如(Nida,1993:121)。
另一方面,韋努蒂極力倡導異化的翻譯策略。毫無疑問,文化派眼中的異化決不是簡單的直譯。因為異化的概念以遠遠超出了語言的層面,上升到了文化、詩學、以及政治的層次。韋努蒂對異化的定義是: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Venuti,2001:240)根據(jù)韋努蒂的理論,《翻譯學詞典》把異化定義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guī)的翻譯(Shuttleworth&Cowie 2004:59)。韋努蒂認為采用異化策略將呈現(xiàn)“在當今的世界事物格局中的一種戰(zhàn)略性的文化互相認可”。因為異化翻譯將挑戰(zhàn)歐美主流文化的心理,而這種心理傾向與排擠翻譯文本中的“他者”。把異化翻譯看作是一種使目標語種族多樣性的手段,韋努蒂認為它具有“保留原語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把讀者送到國外”的作用。這種策略涉及的不僅是擺脫了對目標語語言和文本限制的絕對遵從,而且可以選擇不流暢的、不透明的風格,以目標語的古文來再現(xiàn)原文的真實。這些方法的使用將會給目標語讀者一種“異域的閱讀體驗”(Venuti,1995:20)。
可以看出無論歸化還是異化,以韋努蒂為代表的文化派已經(jīng)將翻譯中不同的文化差異處理置于相當重要的地位。把對文化差異的削弱或保留看成是文化侵略或?qū)ξ幕致缘牡种啤1M管韋努蒂的歸化與異化的討論是針對弱勢文化向歐美強勢文化翻譯過程。但這種基于文化因素的劃分和界定無疑會對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翻譯具有相當?shù)慕梃b意義。因為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翻譯負載著向不同文化傳播和介紹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使命。我們采用不同的歸化或異化的翻譯策略,也將深深影響這種文化交際的最終結(jié)果。
四、結(jié)語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藝術(shù)魅力絕非僅僅限于語言本身。其豐富的文化、藝術(shù)、哲學、社會學內(nèi)涵更是彌足珍貴的。另外現(xiàn)代西方譯論尤其是近年來的功能目的論、交際功能論、文化學派給我們的翻譯策略的選擇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支持。鑒于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翻譯的特殊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充分考慮:(1)翻譯的目的;(2)譯文的目標讀者群:是普通的國外讀者還是西方的精英讀者;(3)交際功能。運用異化策略翻譯無疑會對中國古代燦爛文化在全球范圍內(nèi)傳播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但同時要考慮到此種策略可能給普通目的語讀者帶來的閱讀障礙。但保留文化的特性應是此類翻譯的主要目的,因此異化的使用應多于歸化。
參考文獻:
\[1\]曹雪芹,高鄂.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程永生.漢譯英理論與實踐教程\[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3\]王東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A\].中國翻譯,2002,(9).
第2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古典歷史主義,在藝術(shù)上主要是指對包含希臘及古羅馬的古典時代文化的高度認同。古典主義將古典時代的品味作為標準,并試圖模仿其風格。古典主義形成和繁榮于法國,隨后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是啟蒙時代、理性時代以及部分現(xiàn)代主義思想所提倡的概念。
17世紀開始流行在西歐、特別是法國的一種文學思潮。這一潮流是特定歷史時期產(chǎn)物,因它在文藝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以古希臘、羅馬文學為典范和樣板而被稱為“古典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古典主義在歐洲流行了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初浪漫主義文藝興起才結(jié)束。它在17世紀的法國最為盛行,發(fā)展也最為完備。法國古典主義的政治基礎(chǔ)是中央集權(quán)的君主專制,哲學基礎(chǔ)是笛卡兒的唯理主義理論。古典主義在創(chuàng)作理論上強調(diào)模仿古代,主張用民族規(guī)范語言,按照規(guī)定的創(chuàng)作原則進行創(chuàng)作,追求藝術(shù)完美。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第3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一、相關(guān)內(nèi)容概述
艾布拉姆斯以構(gòu)建可以統(tǒng)貫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文藝理論體系的范式開始,提出了以文學四要素――世界、欣賞者、藝術(shù)家和作品為基礎(chǔ)組成的范式體系。在這個著名而影響深遠的體系當中,“作品”要素被置于中心,其余三者則在其分別與其成一一對應關(guān)系。根據(jù)這三種關(guān)系,以及作品自身單獨成一論述對象,艾布拉姆斯將自古希臘起至20世紀上半葉的文藝理論概括為模仿說、實用說、表現(xiàn)說與客觀說。
從柏拉圖到18世紀新古典主義批評的主流理論被統(tǒng)籌于模仿說的范疇之下,即主要著眼于論證作品與世界的關(guān)系。模仿說的主要代表就是古典主義文藝理論。其最為關(guān)鍵的論點,就是認為“藝術(shù)的目的是模仿自然”。艾氏援用這一派中一個十分經(jīng)典的隱喻――鏡子,來概括古典主義批評這種模仿和“真實”反映有限的客觀世界的特點。與之相對的則是表現(xiàn)說,其主要代表正是浪漫主義的文藝理論。相應的隱喻是燈――它表明藝術(shù)轉(zhuǎn)變成為藝術(shù)家內(nèi)心的光輝向外部世界的投射。這是西方文藝理論史兩千余年的傳統(tǒng)中,首次將關(guān)注的重點移向藝術(shù)家自身。盡管被劃歸浪漫主義一派的理論家們在主要理論方面往往有所出入,甚至彼此沖突,但是他們的基本觀點即在認為藝術(shù)是作家內(nèi)心的反映這點上是一致的。這正是艾布拉姆斯在劃分作家是屬于浪漫主義還是其它理論的支持者時所依據(jù)的主要標準。
在艾布拉姆斯的闡述中,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代表人物被確定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兩人――被反復引述和提及的英國理論家還包括了雪萊、哈茲里特等人。此二人的理論可謂代表了浪漫主義文藝理論,亦即表現(xiàn)說的典型范式,即主張詩歌(不論是總體概念上的“詩”還是具體的某一詩作)應是藝術(shù)家心靈的反映或表現(xiàn)。華茲華斯的理論,核心在于主張詩歌是詩人情感的表現(xiàn)或流露,并與“科學”相對立。同時他認為,詩源于原始的情感流露,其語言也應自然體現(xiàn)作者的情感,并使讀者的心靈受到共鳴式的感染。與其同時代的柯爾律治除了對他的理論有進一步的闡發(fā)或者反撥之外,最讓我受啟發(fā)的,在于柯氏創(chuàng)立了與機械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造論相對立的有機說,并且以植物生長的比喻對此理論作了形象且讓人信服的闡釋。在柯勒律治看來,植物吸收外界養(yǎng)料轉(zhuǎn)變?yōu)樽陨硪徊糠值纳L過程,正如藝術(shù)家在自己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吸收各種情感的、現(xiàn)實的養(yǎng)分,逐步將其“同化”為自身心靈的一部分,最終又將其經(jīng)過藝術(shù)創(chuàng)造呈現(xiàn)給世界的整個過程。另外,柯勒律治論述主觀和客觀,也就是詩人在詩歌中究竟是呈現(xiàn)自己情感還是“如上帝一樣”隱藏在詩句背后創(chuàng)作詩歌的世界方面,也有著巨大的貢獻。這些理論在隨后為眾多批評家或是理論家們反復引用和論述,因而使得兩人在世界上成為了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讓我不無遺憾的是,盡管本書的副標題為“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但書中對于德國浪漫主義的介紹并不系統(tǒng),尤其是對于其代表人物如施萊格爾兄弟、哥德、席勒等人的理論沒有成體系的闡述。缺少對占據(jù)整個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半壁江山的德國浪漫主義的系統(tǒng)介紹,對于準確理解和認識浪漫主義的歷史,不能說沒有造成一定的困難。
二、關(guān)于浪漫主義理論的源頭
浪漫主義文藝理論與古典主義(尤其是18世紀的新古典主義)在對待藝術(shù)的基本觀點上如此對立,乃至引起了文藝史上著名的“古今之爭”。但是引人注目而且耐人尋味的是,二者都能在古代文論家那里找到相類似的源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兩種相左的理論最終有著同樣的淵源,即都是源自柏拉圖的理念說(或理式說)。只不過,二者在對柏拉圖的闡釋中,為了符合自身理論的要求而側(cè)重于其理論的不同部分,結(jié)果分道揚鑣,及至漸行漸遠,最終才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范式。
應該說,相較而言,古典主義文藝批評的范式是較為忠實于柏拉圖原本的理論的。他們較為直接地承認藝術(shù)模仿的是現(xiàn)象界的自然,是受一定可視法則支配的自然。另外,盡管我們可以說浪漫主義也是源于柏拉圖,但實際上他們采用的是新柏拉圖主義經(jīng)過改造的理念說。新柏拉圖主義者們認為,藝術(shù)并非只能反映現(xiàn)象世界,而是可以直接反映理念。因為經(jīng)驗表明,沒有任何一種人類藝術(shù)是一成不變地再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事物,它們無不加入了作者自身的痕跡。這一忽略理念說中作為中間者的現(xiàn)象世界,而直接將藝術(shù)與理念相聯(lián)系的做法,尚未脫離柏拉圖理念說的框架,卻為浪漫主義文論的合理性提供了經(jīng)典意義上的理論依據(jù)。這一創(chuàng)造性的改變也為其自身在日后發(fā)展成理念在藝術(shù)家心中通過創(chuàng)作得到表現(xiàn)和反映的理論作好了鋪墊。
另一個被艾布拉姆斯反復論及的浪漫主義源頭來自朗吉努斯的《論崇高》。朗吉努斯在他的這篇名作中,對“崇高”的五種來源的第二種――熱烈的、激越的情感的作用作了重點而詳細的闡發(fā)。尤其是他把“狂喜(Ecstasy)狀態(tài)”作為衡量作品優(yōu)劣的標準,這也為新的批評方式和批評理論提供了視角。這一批評范式在被古典主義者們忽視了十幾個世紀后,終于被古典主義的反叛者們發(fā)現(xiàn)并且加以發(fā)揚光大。雖然朗吉努斯本人也許不是一個正式的表現(xiàn)說理論家,但是他對創(chuàng)作情感這一屬于藝術(shù)家自身的范疇的關(guān)注確實使得浪漫主義者們受益匪淺。
至于在浪漫主義詩歌本身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莎士比亞外,表現(xiàn)說的支持者們甚至直接將浪漫主義的傳統(tǒng)上溯到了荷馬身上。這不能不讓我感到驚訝和好奇。因為在我的印象中,荷馬史詩作為西方文學傳統(tǒng)中最早的作品,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文藝理論即模仿說的直接來源,長期被劃歸古典主義文學的范疇。但是在浪漫主義理論家們的眼中,盡管荷馬努力在史詩中隱去自己的形象,他卻通過其主人公阿基琉斯(Achilles)表達了強烈的情感和自身的典型性格――這正是表現(xiàn)說的一種具體體現(xiàn)。這從艾氏將《伊利亞特》和《埃涅阿斯記》所作的比較中可以見到。然而史詩本身并不能嚴格被歸為“古典的”或是“浪漫的”一方。通觀整部《鏡與燈》,也能看到諸如史詩、悲劇這樣在西方文學傳統(tǒng)上長期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學樣式,在歸屬問題上始終在“力量的文學”和“知識的文學”、“理性語言”和“感性語言”這類帶有二元對立色彩的范疇之間徘徊。實際上這些作品在模仿和表現(xiàn)的特點方面,本身或許就兼而有之。問題的關(guān)鍵仍舊在于批評家們所關(guān)注的重點和其闡述所要達到的目的有所不同:持模仿說態(tài)度的理論家強調(diào)的是荷馬史詩中對歷史和自然的反映,而表現(xiàn)說的支持者們則突出了荷馬對超自然的神的呈現(xiàn),以及作者自身借助人物表達自身情感的方面。這種差異其實反而印證了艾布拉姆斯的一個觀點,即批評家或理論家都是從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或者自己的學術(shù)立場出發(fā),來闡發(fā)詩歌等文學作品,從而證明自己觀點的合理性。這一現(xiàn)象不僅僅在浪漫主義者中廣泛存在,實際上在其之前就已經(jīng)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為浪漫主義文藝理論的合理性作了另一個注腳。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在源頭上的相似性,其實也是使一部分浪漫主義理論家在自己的體系或者范式中兼有模仿說(或是實用說)及表現(xiàn)說成分的原因。在這方面,雪萊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一方面,他以柏拉圖式的觀點,認為藝術(shù)應該是對自然的模仿和反映,并且強調(diào)詩歌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從心理學的角度,堅持詩歌是詩人內(nèi)心情感的流露這一表現(xiàn)說的理論。這是因為雪萊持有新柏拉圖主義的觀點,即認為理念不僅存在于“物質(zhì)世界的面紗之后”,而且存在于“人的心靈之中”。這就為他在思想上接近表現(xiàn)說的浪漫主義理論提供了可能。可見盡管承認表現(xiàn)說的基本觀點,并且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也具有更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如其《西風頌》就是浪漫主義詩歌的典型代表),但是根據(jù)艾布拉姆斯的闡述可以見到,雪萊不能算是嚴格的浪漫主義理論家。
第4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摘要〕 近代形式論的主流概念是由審美趣味的主觀化先驗化而形成的康德主義形式與感性形式(感性形象)。準確、透徹地把握它們的本質(zhì)、作用、意義應當立足于啟蒙運動思想的一般精神。康德主義形式的最終確立得益于以人性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和認識論,感性形式獲得主導地位歸功于18世紀的存在大鏈條觀念和學科分化的趨勢。從新古典主義美學的衰落,審美趣味、感性形象的流行,浪漫主義及其哲學化德國古典美學,到形式本體論的興起,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哲學美學的一條主題明確的思想線索,即形式與表現(xiàn)、個性與一般、感性與理性、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及種種解決方案,而形式的賦形超越的強大抵御力量充當了構(gòu)筑藝術(shù)和審美活動的自由王國,恢復人性的原始和諧,從審美自由轉(zhuǎn)入政治自由的理想橋梁。
〔關(guān)鍵詞〕 啟蒙理性;審美趣味;感性形象;形式本體;審美教育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4-0180-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西方美學中的‘形式’:一個觀念史的考索”(04cz013)
〔作者簡介〕張旭曙,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近代美學的形式觀念肇始于17世紀,涵蓋新古典主義、啟蒙運動、德國古典美學、浪漫主義、19世紀這幾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從中我們能發(fā)現(xiàn)催生美學學科“埃斯特蒂卡”(感性學)的酵母因素,追溯現(xiàn)代美學形式本體論的譜系血統(tǒng),它甚至構(gòu)成了理解西方人的新型理智生活——啟蒙精神的歷史和實質(zhì)的重要視角。可以說,探究這一課題具有美學史和一般思想史的雙重意義和價值。
一、美之光:從形式照向表現(xiàn)
在17世紀,古代思想世界中占主導地位的形式概念,即柏拉圖的絕對理式、畢達哥拉斯的比例形式、亞里士多德的整體與部分間的和諧仍然在流行,并給予新的形式概念的確立與展開以各種影響、規(guī)約、推動。與此同時,新的詞語和問題,諸如鑒賞、情感、靈感、虛構(gòu)、天才、想象等出現(xiàn)并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標示著一個新的發(fā)展方向。
我認為,理解17世紀美學的形式觀的精神特質(zhì)、演化軌跡、術(shù)語變換、重心轉(zhuǎn)移,有兩個思想史動力因素最為重要:自然科學的興盛和教會權(quán)威的衰敗,這背后站著兩位思想巨人——牛頓和笛卡爾。
羅素曾指出:“近代世界與先前各世紀的區(qū)別,幾乎每一點都能歸源于科學。科學在十七世紀收到了極奇?zhèn)邀惖某晒Α!豹?〕是的,經(jīng)院哲學(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哲學)用本質(zhì)、目的、原因這些不精確的術(shù)語描述運動此時已遭到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時間、空間、物質(zhì)及力等概念。機械論自然觀讓位于目的論自然觀。伽利略的望遠鏡解除了希臘和中世紀賦予天體的特殊的神圣性質(zhì),牛頓的革命工作則進一步加以摧毀。光不再是神秘的物質(zhì)和上帝的住所,而成了一個物理現(xiàn)象。另一方面,虔信主義和神秘主義解說的柏拉圖主義讓位于一種較合乎理性的柏拉圖主義。“這種柏拉圖主義,經(jīng)過伽利略與開普勒的思想而成為牛頓的數(shù)學體系。它承認內(nèi)在力量或啟示是理性的基礎(chǔ),這個理論于是成了一種唯智主義。它要在宇宙的物理秩序及道德定律中尋找神的自然真理。”〔2〕
柏拉圖主義頑強地延伸到英國經(jīng)驗論精神氛圍中成長出夏夫茲博里及其門生哈奇生。夏夫茲博里接近劍橋派新柏拉圖主義。在他看來,宇宙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宇宙的和諧整體是由天帝這位“至上的藝術(shù)家”造就的,他是使物質(zhì)具有形式的最終因。文克爾曼確認情感與個性表現(xiàn)有損于靜穆美理想,萊辛以精神表現(xiàn)的多寡作為衡量身體美高低的準繩,也顯示了新柏拉圖主義成見的影響。
笛卡爾的新哲學力圖調(diào)和近代科學的機械論和唯靈主義的神學和形而上學,他認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相信理性有能力把握確定的知識。《方法談》規(guī)定的用以指導心智的四條原則是新古典主義美學的哲學原理。對此,埃米爾?克蘭茨有過一句精煉的評價:“十七世紀的文學界,各方面都體現(xiàn)了笛卡兒連第一句話也從未寫過的笛卡兒美學。”〔3〕
第5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關(guān)鍵詞:《熙德》 高乃依 悲劇思想
一、關(guān)于《熙德》
彼埃爾?高乃依是法國杰出的古典主義悲劇大師, 也是法國的古典主義悲劇的奠基人。天資的聰明與后天的勤奮、殷實的家庭條件、良好的教育以及對戲劇的熱愛成就了高乃依,使他一生創(chuàng)作頗豐。高乃依的戲劇創(chuàng)作大概有三十多部, 其中《熙德》、《波里耶克特》、《西拿》和《賀拉斯》被稱為高乃依的“ 古典主義悲劇四部曲” 。在這四部作品中,尤以《熙德》最為著名,這部傳世佳作既是高乃依的代表作,也是法國古典主義悲劇的巔峰之作,至今在法國仍有“美得像熙德一樣”這個成語。
《熙德》是一部描寫責任與愛情、理性和感情沖突的悲劇。男女主人公羅狄克和施曼娜在個人感情、家族榮譽以及國家利益發(fā)生沖突后,毅然選擇拋棄個人,維護家族榮譽,服從國家利益。劇本上演后雖然受到了觀眾的熱愛,卻由于沒有完全遵守“三一律”的創(chuàng)作原則而遭到了法蘭西學士院的抨擊,導致高乃依停筆五年之久。后來重新進入文壇的高乃依向法蘭西學士院屈服,嚴守“三一律”的創(chuàng)作原則,雖然也創(chuàng)作有一些劇本,但是再也沒有《熙德》這樣的成就。《熙德》情節(jié)集中起伏,語言具有雄辯遒勁的陽剛之美,宣揚的是理性對感情的勝利,代表了古典主義的崇高風格,集中體現(xiàn)了高乃依的悲劇思想。
二、高乃依的悲劇思想
(一)超越傳統(tǒng)“命運悲劇”思想
相對于西方古代的命運悲劇,高乃依的悲劇雖然也創(chuàng)造了英雄人物,但英雄的悲劇與命運無關(guān)。高乃依的悲劇作品,主題多為表現(xiàn)貴族的責任與個人感情的沖突,充滿英雄主義激情。這些英雄人物不僅英勇善戰(zhàn)、舍私為公,而且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命運的不公,他們往往就是命運的締造者。以《熙德》為例,悲劇的男女主人公羅狄克和施曼娜原為一對傾心相愛的戀人, 他們的愛情卻因為雙方的父親爭權(quán)而受阻――施曼娜的父親打了羅狄克的父親一記耳光,這是對羅狄克家族的侮辱,按照當時的習俗,為父報仇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但羅狄克卻陷入了痛苦的抉擇中:“我心里的斗爭多么尖銳呀! 要成全愛情就得犧牲我的榮譽,要替父親報仇, 就得放棄我的愛人。這一方鼓動我報仇,那一面牽住我的手臂。我已陷在愁慘的境地: 或是背叛愛情,或是忍辱偷生。”[1]
命運的安排對于羅狄克和施曼娜是不公的,它讓相愛的人痛苦無助,因為不管羅狄克是否報仇都意味著要失去施曼娜――“復仇會引起她的怨恨與憤怒,不復仇會引起她的蔑視。復仇會使我失去最柑蜜的希望,不復仇又會使我不配愛她”。[1]基于家族榮譽高于個人的古典主義原則,羅狄克選擇了報仇并失手殺死了施曼娜的父親,命運再次捉弄了這對年輕人,痛苦的抉擇落在了施曼娜的身上:報仇就是殺自己的愛人,不報仇也會使家族榮譽受損。在兩難的境遇中,國家安全受到了摩爾人的威脅,年輕人放棄自己的私情及家族利益,成全了國家利益。羅狄克雖然深陷失去愛情的痛苦當中, 然而并沒有一味沉淪, 他毅然選擇率兵出征, 英勇殺敵, 最后贏得“熙德”(即英雄)的光榮稱號,成為了真正的勇士,并且得到了施曼娜的原諒。
在這里,高乃依讓主人公完全按照自己的精神路線走下去,而不是出于神或者先知的安排的,更沒有一條命運的必經(jīng)之路,因而高乃依的悲劇并非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命運悲劇。雖然有悲劇英雄的存在,但英雄的悲劇是英雄自主選擇的結(jié)果,是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無論是犧牲愛情成全家族榮譽,還是犧牲家族榮譽成全國家利益),是一種可歌可泣、感天地泣鬼神的壯烈犧牲。所以高乃依所強調(diào)的這種悲劇, 其實是一種行為的悲劇。
(二)嚴肅悲壯的主題
由于古典主義文學以崇尚古典作為典范,因而古典主義的悲劇創(chuàng)作往往也是書寫崇高、嚴肅的主題。高乃依的悲劇創(chuàng)作也借鑒了古希臘悲劇的創(chuàng)作手法,其中最大的特征就是嚴肅性,這一特征在《熙德》中主要體現(xiàn)為:
1.悲劇的主角都是“好人”
黑格爾認為,悲劇就是兩種理想和“普遍力量”的對立沖突,是道德力量的局部的“對”與“對”的抗爭,“在這樣一種沖突里,對立的雙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2]作為古典主義悲劇的創(chuàng)始人,高乃依無疑也受到了古希臘英雄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的悲劇沖突的雙方也都是 “好人”或者“英雄”。《熙德》男主人公羅狄克就是英雄的化身,他英勇善哉,具有強烈的英雄主義思想,既能戰(zhàn)勝強勢的伯爵(即施曼娜的父親),也能夠率領(lǐng)軍隊打敗摩爾人的入侵,拯救國家,成為民族英雄。劇本中的女主人公施曼娜也是個明事理、重情義的好女子。當羅狄克因報仇而殺了她的父親時,她出于對家庭榮譽的維護,要求國王處死羅狄克,這時候的她將家族榮譽看得高于個人感情;當國家出現(xiàn)危難急需用人時,她毅然放棄報仇,讓羅狄克出戰(zhàn)護國,這時候的她將國家利益放在家族榮譽之上;所以不管羅狄克還是施曼娜,他們都是與邪惡勢力勢不兩立的“好人”,是維護國家利益的英雄。
2.具有古希臘悲劇“悲壯”的原則
古典主義文學主要從古希臘吸取藝術(shù)形式。受古希臘悲劇影響,高乃依的悲劇情節(jié)曲折,富有震撼力,風格崇高莊嚴,具有古希臘悲劇“悲壯”的原則。《熙德》中,男女主人公的行為都遵從了理性的原則,羅狄克為父報仇殺施曼娜之父高邁斯并不是沖動的行為,而是內(nèi)心激烈的思想斗爭之后所作出的理智而又慎重的抉擇。施曼娜的選擇更是充滿理性的,甚至有人認為這個選擇比羅狄克還要深沉、理智――羅狄克殺高邁斯后向施曼娜謝罪求死,施曼娜在痛苦中抉擇:她愛羅狄克為保衛(wèi)家族榮譽而犧牲個人感情的理性與英勇,但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榮譽卻不得不請求國王處死羅狄克。男女主人公無論是選擇高貴門第榮譽還是選擇珍貴的愛情都是對的,這種對與對的必然沖突是何其悲壯!不管是羅狄克殺唐高邁斯還是施曼娜要殺羅狄克,以及羅狄克出征殺敵的敘述都具有一種昂揚向上、維護正義的思想,它體現(xiàn)了個人(或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崇高意識,悲劇英雄應該具有可歌可泣的遭遇和堅忍不拔的意志, 并且他的行為應該導致感天地泣鬼神的壯烈犧牲精神。
高乃依在《詩劇藝術(shù)論》中指出:“悲劇的莊嚴, 要求詩人描寫一些重要的國家利益, 一些比愛情更崇高更有男兒氣概的激情。譬如, 雄心壯志或血海深仇,使我們看到比情人之死更重大的不幸。在悲劇中使用一點愛情是可以的,因為愛情往往有影響力, 而且可以作為我所說的國家利益和重大激情的基礎(chǔ)。但是愛情必須居于次要地位, 把首要地位讓給它們。” [3]這就是高乃依悲劇創(chuàng)作的原則,這就意味著高乃依的悲劇必然是要表現(xiàn)與國家、民族及歷史命運相關(guān)的重大題材, 必須表現(xiàn)那些為之而英勇斗爭的氣吞山河的英雄男兒及其激情。在這個原則之下,縱使主人公的命運充滿悲劇,這個悲劇必然是悲壯而非悲哀的了。
(三)榮譽與責任相結(jié)合的悲劇思想
17世紀法國封建制度獲得鞏固,逐漸加強,最后建立了歐洲最強大的君主專制國家,為了進一步加強封建專制統(tǒng)治,專制政體對文學進行有效干預,使作家創(chuàng)作活動自覺受王權(quán)控制,成為對賢明君主的頌歌。古典主義的作品大多表現(xiàn)感情服從責任,個人服從義務的主題。這就要求悲劇創(chuàng)作要同榮譽、責任的觀念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劇中人物思想的斗爭和彼此的沖突也圍繞著這種觀念展開,構(gòu)成了基本的、主要的矛盾。高乃依在悲劇題材選擇上有他自己的一貫原則,他認為悲劇“要以有名的、不同尋常的、嚴肅的情節(jié)做題材”,它牽涉“重大的國家利益,較之愛情更為崇高壯偉的激情”。這句話既體現(xiàn)了他的悲劇觀,也反映了他的悲劇取材原則,這一原則其實是反映了封建社會向絕對君權(quán)發(fā)展的時代要求和精神風貌。
由于高乃依的悲劇主要寫于法國君主專制政體的確立時期, 因而作品大多是歌頌那些克制個人欲望以服從國家利益的英雄的, 高乃依通過劇本宣揚愛國主義、服從王權(quán)、 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思想, 以達到鞏固專制和國家統(tǒng)一的作用。在《熙德》中,維護封建榮譽和社會責任就是全劇的主要內(nèi)容。劇本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作為開始的,但是他們的愛情一開始就受到了責任與榮譽的挑戰(zhàn)――羅狄克要維護封建家族榮譽就要與戀人的父親決斗;施曼娜要維護封建家族榮譽就要殺死戀人;外敵入侵時,羅狄克與施曼娜要維護國家利益就必須拋開家族恩怨。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這兩位年輕人都沒有迷失,他們根據(jù)傳統(tǒng)觀念,服從了國家榮譽與責任的召喚,以行動實踐了榮譽責任放在第一位的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悲劇的最后雖然羅狄克與施曼娜和解也是理性的行為,因為成了民族英雄的羅狄克代表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當然高于家族榮譽,施曼娜站在對國家利益負責的高度與羅狄克和解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結(jié)語
從高乃依的悲劇理論以及悲劇代表作《熙德》中,我們不難看出高乃依的悲劇思想。高乃依站在法國17世紀的社會背景下去歌頌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王權(quán),反映個人的一切利益必須服從國家意志和權(quán)力的思想。他根據(jù)古典主義的戲劇原則進行創(chuàng)作,以理性與感情的沖突為主題,塑造了具有崇高的思想和優(yōu)良品德的時代英雄主義形象。同時他又以古典主義戲劇創(chuàng)作原則為規(guī)范而加以靈活運用,實現(xiàn)對古希臘悲劇思想的繼承和超越,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形式都達到了一個新的創(chuàng)作高度。
參考文獻
[1] (法)高乃依.熙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23,27.
第6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關(guān)鍵詞: 《塔索――哀訴與凱旋》 變奏性原則 奏鳴性原則 曲式分析
一、引言
1849年,匈牙利鋼琴家、作曲家李斯特應邀為歌德戲劇《托夸多?塔索》創(chuàng)作序曲,后來經(jīng)過多次修訂,于1854年定稿成為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
李斯特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是依據(jù)拜倫的詩創(chuàng)作的,是繼《前奏曲》之后李斯特創(chuàng)作的第二首交響詩。
關(guān)于李斯特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曲式結(jié)構(gòu)的分析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搜集了有關(guān)該曲曲式結(jié)構(gòu)分析的相關(guān)資料,觀點大致如下:
1.蔣的《李斯特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音樂賞析》(以下簡稱“蔣文”)指出:“這部交響詩的總體曲式結(jié)構(gòu)是一個以變奏原則為主、帶有大型序奏和尾聲的自由的奏鳴曲式。”其曲式結(jié)構(gòu)如下表所示:
2.董輝《李斯特交響詩〈塔索〉的音樂分析》(以下簡稱“董文”)指出:“整個交響詩,是帶有主題變奏特點的奏鳴曲式,其結(jié)束部分結(jié)構(gòu)特別長大(整個交響詩長585小節(jié),而結(jié)束部就占據(jù)了201小節(jié)),這是作者根據(jù)標題內(nèi)容所需而自由處理音樂結(jié)構(gòu)的結(jié)果。”并且指出了交響詩采用的奏鳴曲式與古典奏鳴曲式的不同之處:“整個哀訴部分包括引子、呈示部、展開部和再現(xiàn)部的一部分,而凱旋是最后的結(jié)束部,把它單獨列出來,是由于其規(guī)模擴充、結(jié)構(gòu)特別長大的原因;在呈示部的主部主題之前運用了較長大的、具有濃縮材料性質(zhì)的引子部分;整個調(diào)性布局沒有遵循調(diào)性回歸的原則,而是根據(jù)表達情感的需要自由處理、靈活運用;各種情緒性格不同的段落緊密相隨,通過主題的變奏、變形達到統(tǒng)一。相同的主題材料,通過配器、旋法、和聲、織體、節(jié)奏、速度、音區(qū)等的不同運用,獲得不同的性格表現(xiàn)力。”其曲式結(jié)構(gòu)如下表所示:
二、《塔索――哀訴與凱旋》曲式結(jié)構(gòu)分析比較
音樂作品合乎一定邏輯的結(jié)構(gòu)形式即為曲式結(jié)構(gòu),音樂內(nèi)容需要依附曲式結(jié)構(gòu)的存在而存在。音樂形式在時間的過程中展開、發(fā)展、結(jié)束,屬于形式范疇。一般意義上講,形式與內(nèi)容是統(tǒng)一的。
維也納古典主義時期的海頓在前輩們奠定的基礎(chǔ)上逐步確立并完善了奏鳴曲式結(jié)構(gòu)。奏鳴曲式是在內(nèi)容上以一對矛盾為基礎(chǔ),在材料上以兩個主題為中心,在結(jié)構(gòu)上以三種功能(呈示、展開、再現(xiàn))為支撐的一種大型的、三部性曲式。奏鳴曲式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呈示部――展開部――再現(xiàn)部。
與古典主義曲式結(jié)構(gòu)的嚴謹相比,浪漫主義的曲式結(jié)構(gòu)是自由的。古典主義以古希臘時代的作品為完善標準,以形式的嚴謹與統(tǒng)一為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因此,這個時期的音樂是追求思想和形式統(tǒng)一的純音樂。在古典主義時期,理性思想占主導地位,一切事物的運動發(fā)展都以規(guī)范為原則,平衡與對稱是這個時期音樂創(chuàng)作的中心。例如:結(jié)構(gòu)的平衡、調(diào)式調(diào)性布局的平衡、內(nèi)容與形式等方面的平衡。顯而易見,古典主義音樂是嚴謹而規(guī)范的,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奏鳴曲式結(jié)構(gòu)上。
在古典主義早期奏鳴曲的典范中,奏鳴曲式在結(jié)構(gòu)方面比較程式化,包括調(diào)性布局相當嚴格,相當于我國的格律詩,用字都有嚴格的“平仄”韻律,都是些“近親”關(guān)系的往來。而從浪漫主義早期開始,古典主義的一些曲式原則漸漸消失。這就好像我國“五四”運動后出現(xiàn)大量新詩一樣,詩人寫詩對韻律的要求不怎么嚴格,詩句的長短依內(nèi)容而定。因此,某些作曲大家的創(chuàng)作都在古典主義奏鳴曲式的基礎(chǔ)上彰顯自己的獨特個性,對奏鳴曲及奏鳴曲式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自由和靈活。
“蔣文”和“董文”在曲式結(jié)構(gòu)分析上有細微的差異,比較二者的曲式結(jié)構(gòu)表可知,他們的不同意見在于:(1)副部主題的位置;(2)奏鳴性和變奏性哪一種原則占據(jù)主導地位。
在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時期,一般情況下,主部與副部的關(guān)系是“近親”關(guān)系的來往,為了突出主部與副部的差別,通常通過近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實現(xiàn),如從主調(diào)轉(zhuǎn)為關(guān)系調(diào)、屬調(diào)、下屬調(diào)等。李斯特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主部主題的呈現(xiàn)是c小調(diào),而如果按照“董文”的曲式結(jié)構(gòu)分析,在第76小節(jié)進入副部主題,但這里并沒有轉(zhuǎn)調(diào),而是從“董文”分析的第二副部主題,即從第91小節(jié)開始轉(zhuǎn)調(diào)至降E大調(diào)。因此,可以看出“董文”在副部位置的分析上不夠準確。
此外,李斯特交響詩《塔索――哀訴與凱旋》這首樂曲用了多次變奏,使得主題材料通過變奏方式貫穿全曲,在中晚期的浪漫主義作品中,文學里的敘事跟奏鳴曲式結(jié)構(gòu)是沖突的,“變奏”反而因為文學的特殊性而處于主要地位。
“蔣文”雖然提到這部交響詩的總體曲式結(jié)構(gòu)以變奏原則為主,但通觀全文,“蔣文”只分析到三次變奏,即從第91小節(jié)開始,是第一次變奏;從第131小節(jié)開始,是第二次變奏;從第165小節(jié)開始,是第三次變奏。另外,“蔣文”對《塔索――哀訴與凱旋》因變奏原則而導致的段落劃分亦不夠準確,如呈示部至哪里結(jié)束,“蔣文”用插部代替展開部的稱謂,等等。“董文”僅僅認為該曲帶有主題變奏特點,而沒有說明變奏性原則為主與否。另外,“董文”用結(jié)束部代替尾聲的稱謂,等等,也存在不妥之處。
第7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拉奧孔,詩與畫,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
《拉奧孔》是18世紀德國戲劇家、美學家萊辛的代表性文藝論著,創(chuàng)作于德國啟蒙運動時期,其主題是論證詩與畫的界限。詩與畫的關(guān)系在西方是一個古老的文藝問題,歷來的文學家和藝術(shù)家都比較注重詩與畫的共同點。如早在古希臘時代詩人西摩尼德斯曾說“畫是一種無聲的詩,而詩是一種有聲的畫”[①];古羅馬時期,詩人賀拉斯的《詩藝》中也包含著詩畫一致的思想;到了17—18世紀,在新古典主義的影響下,德國不少新興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都普遍接受了詩畫同源、詩畫一致說,提倡寓意畫、歷史畫以及描繪自然田園的詩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萊辛以拉奧孔雕像群為論述對象,通過比較其在史詩與雕像中不同的藝術(shù)處理,具體論證了詩(代表一般文學)與畫(代表一般造型藝術(shù))的界限,抽繹出這兩種藝術(shù)類型的本質(zhì)特點,有力駁斥了當時新古典主義者所宣揚的詩畫一致說。一、詩與畫之比較
17—18世紀,在法國和德國不少新古典主義者都極力強調(diào)詩畫一致說,因此在詩中追求描繪、在畫中追求寓意的做法在當時非常流行。萊辛則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沒有根據(jù)的觀點。盡管詩與畫都是摹仿的藝術(shù),但“畫和詩無論是從摹仿的對象,還是從摹仿的方式來看,卻都有區(qū)別。”[②]
首先詩與畫的題材不同。如萊辛以荷馬史詩中潘達洛斯射箭以及眾神飲宴會議的場面為例,說明詩可以表現(xiàn)在時間上先后承續(xù)的事物,即動作情節(jié);畫則宜于描繪在空間中并列的、呈靜態(tài)的物體。再如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由于繪畫是訴諸人的視覺感官,所以畫只宜于描繪美的事物,以美作為最高法則,而應避免描繪丑的以及令人嫌厭、恐怖的對象,因為它們會引起人的反感;詩卻可以描寫丑,因為通過詩人對各個組成部分的先后描寫,丑的效果就會削弱,同時丑與喜劇性相聯(lián)系,對丑的描寫會使對象顯得可笑,起到娛樂的效果。此外,萊辛還舉出詩人斯塔提烏斯和弗拉庫斯對盛怒中愛神維納斯的描寫,說明詩可以表現(xiàn)獨特的個性特征,塑造出鮮明的典型形象;畫卻只能描繪一般的抽象的性格特征。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在題材方面,詩比畫有較大的范圍。
其次詩與畫所采用的摹仿媒介不同。由于詩以時間上先后承續(xù)的動作情節(jié)為摹仿對象,而畫的對象則是空間中并列的物體,所以萊辛認為詩宜于用語言文字符號來敘述,畫則適合用線條顏色符號來描繪。
再次詩與畫有著不同的藝術(shù)理想和審美效果。詩用語言文字來敘述動作情節(jié),重在表現(xiàn)人物情感和個性以及情節(jié)的動態(tài)發(fā)展,因而要產(chǎn)生“真”的效果;畫用線條顏色來描繪物體,主要訴諸人的視覺,所以須追求“美”的效果。在論述過程中萊辛以拉奧孔為例,指出在造型藝術(shù)中美是最高的法則,因此對于雕塑而言,若表現(xiàn)拉奧孔父子激烈的形體扭曲和苦痛的面部表情就會破壞雕像最高度的、整體的美,所以雕刻家把史詩中所描寫的痛苦的哀號化為雕像中的輕微的嘆息。這即是說明了在繪畫等造型藝術(shù)中,表情要服從最高法則——美的規(guī)律——的要求,這是“藝術(shù)家供奉給美的犧牲”[③]。詩則不受這樣的限制,而應該盡量注重表情,并通過語言文字的描繪使之變成真實的、實在的、可認識的東西。
通過史詩與雕塑對于拉奧孔題材的不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萊辛總結(jié)了二者在題材、媒介、審美效果等方面的各不相同之處,由此批評了當時新古典主義者所宣揚的詩畫一致的片面錯誤觀點。
雖然《拉奧孔》的主旨在于論證詩與畫的界限,但是在給二者立異的同時,萊辛并未忽視詩畫之間的聯(lián)系。一方面一切物體不僅在空間中并列存在,而且也在時間中存在;另一方面,動作也須依存于人或物,而不是獨立的。所以繪畫可以通過物體來摹仿動作,而詩也可通過動作來描繪物體。
由題材和摹仿媒介本身的特點所制約,繪畫摹仿動作,須把時間上先后承續(xù)的動作化為空間中并列的物體,所以萊辛主張畫家選擇一個最富包孕性的頃刻,即動作情節(jié)發(fā)展到頂點前的一頃刻來描繪。因為這一頃刻最富于暗示性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既包含著過去也預示著未來,可以讓想象充分自由地活動,所以“最能產(chǎn)生效果”[④]。
同理,萊辛舉出了幾種方法說明詩也可以描繪物體。首先是化靜為動。萊辛以荷馬史詩中借敘述阿喀琉斯盾的制造過程來描繪其形狀為例,說明詩要描寫物體就要把空間中的并列化為時間上的承續(xù),而且這還可以避免枯燥冗長之弊。其次,從對象的效果入手而避免對細節(jié)做描繪。例如荷馬史詩中,詩人通過特洛伊國元老們的私語贊嘆暗示出海倫的美貌絕倫。與此相類似,詩人還可以“化美為媚”[⑤],即把靜態(tài)美轉(zhuǎn)化為動態(tài)美,因為動態(tài)的美比靜態(tài)的美效果更強烈、更生動。后二者以效果來描寫美的人與物,也即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烘托手法,有以一當十之妙。
通過以上的概述,我們可以說萊辛對詩與畫的比較,較之當時新古典主義者的偏頗觀點,則顯得相當全面。他不僅劃定了詩畫的界限,也指出了二者的聯(lián)系,由此體現(xiàn)了詩與畫所代表的兩種不同類型藝術(shù)的本質(zhì)特點。
二、詩比畫高
在《拉奧孔》這部著作中,萊辛雖是詩畫并舉,論述二者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但究其深意,我們不難看出其論述的傾向性在于詩比畫高、詩比畫更具優(yōu)越性。
一方面,詩可以更廣泛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前文已論及詩比畫的題材范圍更廣。畫以美作為最高法則,只宜于表現(xiàn)美;詩卻可以描寫丑的、令人嫌厭、恐怖的對象,所以詩的表現(xiàn)范圍更廣闊,包括整個的世界和人生,同時由于詩重在摹仿人的動作表情和情節(jié)發(fā)展,因而詩人必須重視其描繪的真實性以及動態(tài)地反映活生生的人生畫面。所以萊辛認為“生活高出圖畫有多么遠,詩人在這里也就高出畫家多么遠。”[⑥]
另一方面,詩能夠更全面深入地展示人物的不同側(cè)面。繪畫只能表現(xiàn)人物某種一般的抽象的性格特征,通常在作品中表現(xiàn)為“替人格化的抽象概念找出一些象征符號,使它們成為可以辨認的”[⑦],因而形象往往缺少鮮明的獨特個性;詩卻不然,其中的人物除了一般的性格特征之外,還能表現(xiàn)出隨著情境的不同而具有的更為突出的性格特征,即共性與個性的結(jié)合。因此詩中的人物形象較之繪畫則顯得更加鮮明、豐滿、栩栩如生。萊辛關(guān)于詩畫對人物性格特征的揭示的論述實已蘊含了類型與典型的思想于其中。
萊辛反對當時新古典主義者所標舉的詩畫一致說而對二者作出嚴格的區(qū)分,這就明確了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之間的本質(zhì)規(guī)律和特點,但是萊辛在論述過程中所流露出的詩高于畫的思想傾向則又走向了另一極端。詩與畫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類型,二者雖然在題材、摹仿媒介、審美效果等方面存在著差別,但是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它們都是摹仿的藝術(shù),因此詩與畫只有類的區(qū)別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而沒有藝術(shù)上的高下之分。所以說,萊辛為論證詩畫界限而不自覺地傾向于詩比畫高的思想未免顯得有矯枉過正之嫌。三、對《拉奧孔》主題思想的評價
通過上文的概述,我們清楚了《拉奧孔》的主題思想在于論證詩與畫的界限,并且這一主旨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的。受17—18世紀啟蒙運動思潮的影響,作為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萊辛不滿當時宮廷貴族所崇尚的寓意畫和歷史畫,因為這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大多是象征一些抽象概念或是敘述時間動作,并不是主要通過視覺而引起觀賞者的美感,這就違背了繪畫藝術(shù)的本質(zhì)規(guī)律。另一方面,萊辛也反對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描繪體詩。雖然這類詩以描寫農(nóng)村田園生活為主,反映了新興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diào),但是詩中多帶有感傷色彩,而萊辛強調(diào)詩要動態(tài)地反映現(xiàn)實人生,反對把繪畫中的“靜穆”[⑧]理想應用于詩中。如前文所說的,萊辛給詩與畫兩種藝術(shù)做出嚴格的區(qū)分明確了二者的本質(zhì)特點和規(guī)律,推動了啟蒙主義文藝思想的發(fā)展;同時,萊辛對詩畫一致說的批駁更體現(xiàn)出一種要求積極變革的時代精神。
但不可否認的是,《拉奧孔》這部著作同樣存在著理論上的局限性。首先,萊辛只從詩與畫兩種藝術(shù)本身入手,對其特點、規(guī)律進行比較,而沒有考慮到社會歷史環(huán)境對于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影響。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一個時代的藝術(shù)都會深深打下其所處時代的印記;并且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不僅不同類型的藝術(shù)之間會有鮮明的差別,即使是同一種藝術(shù)在不同的時代也可能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但是萊辛忽視了這一點,孤立地就藝術(shù)來論藝術(shù),而未聯(lián)系社會歷史因素說明詩畫之間的區(qū)別。
其次,萊辛對詩畫界限的區(qū)分過于絕對化,這就難免會使其某些觀點失之偏頗。如萊辛認為美是造型藝術(shù)的最高法則,作品中人物的表情必須服從美的要求,因此對于拉奧孔雕像群來說,雕刻家把痛苦的哀號變?yōu)檩p微的嘆息,以此保持雕像群整體的美感。但是黑格爾則指出拉奧孔雕像群雖然表現(xiàn)出高度真實的表情——“極端痛苦”、“身體的抽搐,全身筋肉的跳動”,然而它“仍然保持美的高貴品質(zhì)”[⑨],達到了表情真實與美感效果的高度統(tǒng)一。再如,關(guān)于詩與畫的題材,萊辛認為只有繪畫才能描繪物體美,而詩人若描寫物體美的各個組成部分則會削弱美的效果。如果照此理解,那么凡是有關(guān)美的題材則都將被排除在詩歌甚或是一切文學領(lǐng)域之外,這就無異于否定了詩歌可以表現(xiàn)“美”這一內(nèi)容意義。
再次,在討論詩與畫的題材時文學與造型藝術(shù),萊辛認為繪畫無法像詩歌那樣摹仿時間上先后承續(xù)的動作。其實,即使有時面對著簡單的物體,畫家也可能難以繪就。如李白有詩云:“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雖然詩人只描寫了湖水、明月、鴻雁等景物,但由于湖西月、江北雁處于不同的空間中,所以畫家面對這樣的題材,往往也會一籌莫展,而無法像詩人那樣把不同時空中的景物明確地、完美地聯(lián)系融合在一起。因此,對于說得出而畫不就的事物,錢鍾書認為其范圍不僅僅局限于先后承續(xù)的動作,而且也包括一些靜止的景物,所以他說:“詩歌里渲染的顏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畫家感到彩色蝶破產(chǎn),詩歌里勾勒的輪廓、刻畫的形狀可能使造型藝術(shù)家感到鑿刀和畫筆力竭技窮。”[⑩]
總體來說,《拉奧孔》這部文藝論著是17—18世紀啟蒙主義運動的時代產(chǎn)物,它對當時新古典主義所宣揚的詩畫一致說以及新興資產(chǎn)階級所崇尚的靜態(tài)的、感傷的文藝觀進行了批駁,取而代之的則是論證了詩畫兩種藝術(shù)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和規(guī)律,以及動態(tài)的、實踐的文藝觀和人生觀。萊辛的這部著作在當時的西方文藝理論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它對詩與畫的比較不僅引導人們對古典文藝重新獲得了正確的認識,由此推動了德國民族文藝的繁榮,而且其鮮明的時代精神也對當時的德國青年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如歌德就曾高度評價《拉奧孔》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要設想自己是青年,才能想象萊辛的《拉奧孔》一書給予我們的影響是怎樣,因為這本著作把我們從貧乏的直觀世界攝引到思想的開闊原野了。”“因此卓越的思想家從幽黯的云間投射給我們的光輝是我們所最歡迎的。”[11]歌德的這段評價也正說明了《拉奧孔》這部著作的偉大意義和價值之所在——它確是近代德國文藝界中的一部轉(zhuǎn)折和奠基之作。
參考文獻:[1][德]萊辛著,朱光潛譯.拉奧孔[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古羅馬]賀拉斯著,楊周翰譯.詩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4]張秉真、章安祺、楊慧林.西方文藝理論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5]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6]錢鍾書.錢鍾書集·七綴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7] 馬奇主編.西方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第8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關(guān)鍵詞:《拉奧孔》;詩與畫;時間與空間;“真”與“美”
17、18世紀在歐洲轟動一時的啟蒙運動以“理性”為核心,是一場資產(chǎn)階級反封建、反教會、反禁欲主義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它繼文藝復興之后,進一步運用人的理性批判封建專制的腐朽與宗教教會的愚昧,肯定人的意識,否定神的權(quán)威。萊辛是德國啟蒙運動的杰出代表,因此,他的美學理論尤其是《拉奧孔》闡明的“詩畫異理”的美學觀帶有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人本主義的實質(zhì)就是讓人領(lǐng)悟自己的本性,不再倚重外來的價值觀念,讓人重新信賴、依靠人本身,消除外界環(huán)境通過內(nèi)化而強加給他的價值觀,讓人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掌握自己的命運,實現(xiàn)個性的獨立與發(fā)展”。[1]
在啟蒙運動前夕,古典主義經(jīng)院式的刻板呆滯的形式主義文風籠罩著死氣沉沉的歐洲文壇。萊辛通過自己的努力,喚起了德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形成團結(jié)統(tǒng)一的民族精神,開辟了德國民族文學自由發(fā)展之路。一方面,萊辛明確了詩與畫的界限,極力反對將古典主義審美標準“靜穆美”作為一切藝術(shù)形式的共同追求,指出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應具備與自身特征相適應的審美理想與美學原則,以正確的價值尺度衡量不同門類的藝術(shù)作品。人應運用自己的理性,對事物加以區(qū)分,不可盲目信從外來經(jīng)驗與宗教神學。另一方面,萊辛對詩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風格與美學理論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釋。萊辛強調(diào)詩應當具備真實的特質(zhì),真實地反映自然界與現(xiàn)實生活,真實地表達人的情感與內(nèi)心世界。萊辛十分欣賞荷馬與索福克勒斯,他們描繪的英雄具備一般人的性情,是“有人氣的英雄”。萊辛不贊同哀號、哭泣、咒罵會影響偉大人物的英勇形象與崇高心靈,相反,他認為這是人的本性、人的正常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拉奧孔可以在詩中盡情哀號,因為詩是表情的,這是人本意識的具體表現(xiàn)。
在對造形藝術(shù)和語言文字藝術(shù)的對比中,萊辛發(fā)現(xiàn),畫受到空間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畫只能從某個角度去描繪某一事物在某一頃刻所顯示的屬性,與此相比,詩顯示出了巨大的優(yōu)勢。詩屬于時間藝術(shù),雖然在描繪物體上與畫存在一定差距,不如畫給人的視覺印象強烈,但詩不受時空限制,可從多視角來描述動作或情節(jié)發(fā)展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萊辛認為詩與繪畫的審美理想與美學原則不同,造形藝術(shù)的最終目的是“美”,詩歌藝術(shù)的最高原則是“真”。萊辛在《拉奧孔》中談論了美丑問題,指出畫只能摹仿美的事物,丑不能入畫,因為這樣會令人反感,而詩不會給人帶來像畫一樣強烈的畫面感,因此美丑皆可入詩,且丑也是對現(xiàn)實的真實反映,這與詩所具備的“真”這一最高美學原則相一致。“詩比畫大,每一幅畫面都可以入詩,而并非每一句詩都可以入畫”。[2]可見,詩與畫相比,在表現(xiàn)題材上更加廣闊,在藝術(shù)手法上更加靈活多變,更重要的是詩可表達抽象的人格、精神與情感,可使讀者自由馳騁在想象與聯(lián)想的世界中,因此,詩是最自由的藝術(shù)形式,自由是詩最重要的特質(zhì)。
雖然萊辛明確指出了詩與畫的界限,但并沒把這兩種藝術(shù)形式絕對對立起來。早在我國古代,就有了詩、樂、舞三位一體的說法,這說明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內(nèi)在的相通性,舞蹈便是將視、聽這兩種感官有機地結(jié)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所以,萊辛認為:“把多種美的藝術(shù)結(jié)合在一起,以便產(chǎn)生一種綜合的效果,這種可能性和難易程度就要隨這些藝術(shù)所用的符號的差異而定。”[3]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詩與畫的界限,更不能將一種藝術(shù)形式的審美規(guī)范作為欣賞與評價一切藝術(shù)形式的統(tǒng)一標準。正確把握詩與畫的美學原則,使詩與畫這兩種古老而又常新的藝術(shù)形式在對立中實現(xiàn)諧和統(tǒng)一。
萊辛的文學理論沖破了古典主義“靜穆美”的束縛,使人性的光輝透過重重陰霾,照亮了德國黑暗的現(xiàn)實,德國民族文學由此誕生。俄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在評論德國文學時講到,“德國文學的革命不是由一個偉大的詩人開始,而是由一位聰明而又有魄力的批評家來完成。”[4]由此可見萊辛與他的《拉奧孔》在德國文學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地位。
注釋:
[1] 胡經(jīng)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2] 董學文.西方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 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 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三卷).滿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參考文獻:
[1]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2]董學文.西方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胡經(jīng)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第9篇:古典主義文學范文
“湖畔派”詩人的代表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出生在英國坎伯蘭郡的一個律師家庭。中學時期他常常前往學校附近的大自然中嬉戲游蕩,結(jié)識農(nóng)夫與羊倌。這一時期的生活對其日后文藝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后在劍橋大學期間,他在盧梭“回歸自然”思想的感召下,游歷了歐洲各國的山區(qū),進一步深入到大自然中去。他所生活的時代,社會政治正經(jīng)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英國產(chǎn)業(yè)革命到法國大革命,所形成的社會巨變對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強烈而深遠的影響。
一、《抒情歌謠集》的創(chuàng)作
同住在英格蘭北部湖區(qū)的華爾華茲與柯勒律治文學志向極為相近,兩人希望以全新的方法來創(chuàng)作詩歌,用清新的風格來傳遞他們對時代的理解。于是1798年兩人共同創(chuàng)作的《抒情歌謠集》問世了。《抒情歌謠集》的出版在文壇猶如晴天霹靂一樣,使所謂的文人雅士極為震驚。此詩集中以柯勒律治的著名長詩《古舟子詠》為開篇,其它大部分為華茲華斯所作。其中著名的有《我們是七個》、《丁登詩》、《早春》等。這些詩作大多選取下層民眾的生活為選題,挖掘人們內(nèi)心的世界,歌頌大自然。這些詩歌以其真實的情感,淳樸的語言和清新的風格,開創(chuàng)了英國詩歌浪漫主義的一代新風。自此華茲華斯逐漸形成了自己浪漫主義詩歌理論及特點。華茲華斯的創(chuàng)作思想與理論體系集中展示在1800年《抒情歌謠集》和1815年再版時所寫的序言中。
二、詩的本質(zhì)與目的
在序言中華茲華斯對于詩的本質(zhì)問題與目的議題,給出了很明確的見解。在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家崇尚情感抒發(fā)的時代里,華茲華斯也不例外的,重視人性中的情感元素,認為詩的本質(zhì)為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看來,情為詩的本源,自詩存在以來,所有成名之作,都源于詩人的真情實感。在他看來,詩歌的創(chuàng)作可謂是由現(xiàn)實生活所引發(fā)的沖動使然,所有詩歌的語言都是情有所感的產(chǎn)物。詩歌與情感不可分割,人們真摯而強烈的情感需要一種渠道來抒發(fā),正是詩歌的誕生使得情感得以宣泄。而且,在華爾華茲的詩中,他把詩歌的選題集中于微賤的田園生活,這完全符合詩歌本質(zhì)要求。他認為,純樸單純的田園生活才是人們情感萌生的最佳土壤,這里有別于充斥著虛情假意的工業(yè)文明環(huán)境。華茲華斯對于詩的目的的理解可以歸納為“真理”兩個字。對于其準確的含義,華茲華斯在序言中并沒有特別明確的界定。以至于理論界對它有較為廣泛的討論。而大多數(shù)學者始終認為“真理”學說是對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提出的:“詩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學意味的”理念的一種肯定與繼承。他認為詩歌所表達的應為社會生活的普遍規(guī)律。通過對個性事物與個人情感的描述,實現(xiàn)揭示事物本質(zhì)與規(guī)律的哲學高度。其實,華茲華斯是在詩歌應該表達出事物的普遍性與必然性方面繼承并發(fā)揚了亞里斯多德關(guān)于詩的理念。所以,華茲華斯的“真理”的定義應相近于亞里斯多德提出的“哲學意味”,其中心實質(zhì)為詩歌表現(xiàn)的真理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而是普遍的有效的。
三、詩歌應采用日常語言
對于華茲華斯而言,為了實現(xiàn)詩歌的本質(zhì)與目的,去描寫“真理”,他就必須更新詩歌的表達方式——語言。在《序言》中,他反復強調(diào)詩歌應采用真實的語言,合情合理的語言和自然的語言,而且多次強調(diào)詩歌語言除韻律和節(jié)奏以外與散文語言無本質(zhì)差別。他本人強烈反對以高雅綺麗,矯揉造作為特征的古典主義宮廷語言,反對脫離生活實際去編造出華而不實的辭藻。由于華茲華斯選取平凡的日常生活或田園生活作為描寫對象,來抒發(fā)人們真摯的情感、熱情及天性,那么詩歌所應用的語言就應順應題材的本質(zhì),選取人們?nèi)粘I钫鎸嵉恼Z言,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主題內(nèi)容與語言載體的一致。而且,詩歌的閱讀受眾也使得詩歌需要采用日常語言。在華茲華斯看來,詩歌絕不僅僅是寫給詩人自己的。他是在為人們寫詩。其實詩人是以一個個體的身份在向人們傳遞一種感受與情感。但這并不表示華茲華斯認為日常生活中的通俗語言可以不經(jīng)加工與選擇直接寫入詩歌。他提倡的理論需要對詩歌語言進行“篩選”,也就是加工提煉刪除其中的不宜之處。只有這樣的語言才是真正的詩歌語言。
總之,華茲華斯的詩歌語言理論倡導詩歌語言的清新、自然、純樸、通俗化及口語化,批評并修正了之前古典主義文學藝術(shù)文體中語言應用的各種缺點,對于英國文學體系中詩歌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客觀的來講,他對于詩歌語言改革的主張,在理論與實踐上存在一定的過激之處。華茲華斯太過強調(diào)詩歌語言與散文語言的相同之處而忽略了兩者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差異的,這樣的后果就是會造成詩歌語言的過分散文化。一些文藝學家指出,他過度的把某一階層或某一群體使用的語言絕對地定義為詩歌的標準語言有些不夠嚴謹。對于某種形式的過分刻意強求,很容易使得其不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