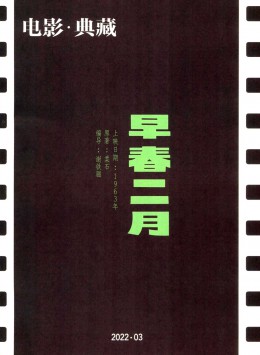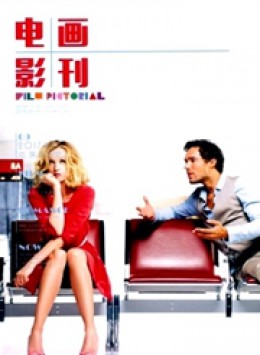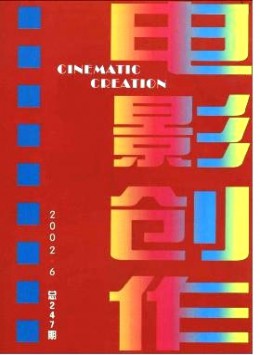電影導(dǎo)演管虎創(chuàng)作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電影導(dǎo)演管虎創(chuàng)作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摘要】管虎是我國第六代電影導(dǎo)演的杰出代表之一,其電影作品個(gè)性鮮明、風(fēng)格獨(dú)特,聚焦底層人民真實(shí)的生活面貌、社會(huì)環(huán)境、心路歷程,因此其作品情感真摯,情節(jié)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文章以電影導(dǎo)演管虎創(chuàng)作的“底層意識(shí)”為切入點(diǎn),結(jié)合管虎導(dǎo)演的電影作品探析其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與底色。
【關(guān)鍵詞】電影導(dǎo)演;管虎;創(chuàng)作;風(fēng)格
隨著我國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公眾對(duì)于電影的需求顯著提升,電影也成為公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娛樂、精神享受與文化認(rèn)知形式。在競(jìng)爭(zhēng)愈加激烈的電影行業(yè),電影導(dǎo)演們不得不尋求新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點(diǎn)與發(fā)展契機(jī),越來越多的商業(yè)片出現(xiàn)在公眾的視野、進(jìn)入到公眾的生活,加之公眾審美素養(yǎng)、文化素養(yǎng)的提升,其不禁會(huì)思索,是否我國電影藝術(shù)已經(jīng)走向了“下坡路”?實(shí)際上電影藝術(shù)的商業(yè)性是電影市場(chǎng)化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即使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也需要經(jīng)濟(jì)的支撐,因此商業(yè)片的井噴式增長(zhǎng)有其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必然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當(dāng)前公眾并非反對(duì)電影藝術(shù)的商業(yè)化,而是抗拒一味追求票房、粗制濫造、文化內(nèi)涵淺顯、庸俗甚至低俗的電影,究其原因在于電影創(chuàng)作中將“票房”這一要素?zé)o限擴(kuò)大化,忽視了觀眾的情感體驗(yàn)、忽視了電影藝術(shù)的價(jià)值、忽視了意識(shí)的滲透與彰顯,導(dǎo)致電影內(nèi)容平平無奇、電影類型同質(zhì)化問題嚴(yán)重。如何平衡觀眾、票房以及導(dǎo)演意識(shí)三大要素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電影導(dǎo)演共同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管虎作為我國第六代電影導(dǎo)演的杰出代表之一,在此方面進(jìn)行了有益的嘗試,并為電影界同仁做出了表率,即使其有時(shí)也難以正確處理觀眾、票房與自我個(gè)性的關(guān)系,但從其現(xiàn)有的、深受公眾青睞的電影作品來看,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理念依然值得借鑒。
一、管虎創(chuàng)作的“底層意識(shí)”
管虎成長(zhǎng)于充滿煙火氣的北京胡同,胡同文化的浸潤(rùn)、市井氛圍的熏陶、人生百態(tài)的影響鑄就了管虎的“底層意識(shí)”,其關(guān)注社會(huì)最底層的小市民、樂于描繪游離在體制之外、在大城市奔波勞碌的人物,致力于用電影鏡頭反映社會(huì)底層生活面貌、記錄底層人物的艱辛與掙扎,但其情感基調(diào)卻不卑不亢,即使底層人物生活艱辛,但其迸發(fā)出的生命力、頑強(qiáng)的精神卻令人為之動(dòng)容[1]。從管虎電影的取材來看,他的電影很多都以平民視角進(jìn)行敘事,這樣的“底層意識(shí)”使他的電影有血有肉、真摯飽滿。例如《頭發(fā)亂了》這部電影以“”時(shí)期為背景,為人們呈現(xiàn)了在城市快速發(fā)展之中外企的生存狀況、城市拆遷的場(chǎng)景、城市的變化等。從當(dāng)前社會(huì)環(huán)境來看,城市化進(jìn)程不斷推進(jìn),城市面積顯著增大,鄉(xiāng)村的城市化發(fā)展使原本在小城市、鄉(xiāng)村中謀生的青年人群不由得產(chǎn)生一種焦慮感、不安感、迷茫感,未來將何去何從?城市可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是否能找到正確的道路?此部電影將當(dāng)代青年無法宣泄的不安、焦慮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人們?cè)谟^看這部電影時(shí),或多或少都能從其人物的境遇、波折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觀眾的情感與電影的情緒交織在一起,正是“底層意識(shí)”引發(fā)的觀眾情感共鳴[2]。例如《浪漫街頭》這部電影,聚焦處于社會(huì)底層的出租車司機(jī),用電影語言再現(xiàn)了出租車司機(jī)的一天。“一天”這一短暫的時(shí)間限制,與電影中處處存在的情節(jié)沖突產(chǎn)生極大的矛盾,觀眾在“一天”時(shí)間內(nèi)感受到出租車司機(jī)生活的艱辛,體會(huì)到人生百態(tài),看似矛盾的事物在這部電影內(nèi)達(dá)到了完美的協(xié)調(diào),體現(xiàn)出拼命想要融入社會(huì)的底層人物的“力不從心”。再如《老炮兒》這部電影塑造了一個(gè)與時(shí)代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他有血性、講道義、講規(guī)矩,雖然他的思想看似與時(shí)代相背離,但其有自己的尊嚴(yán),為了維護(hù)自己的尊嚴(yán),他敢于與時(shí)代抗?fàn)帯T跊坝康氖浪咨钪校卸嗌偃耸苌畹摹懊{迫”丟掉了自己的底線與血性?又有多少人起初敢于與生活抗?fàn)幍詈罄硐肫茰纾罱K還是困于現(xiàn)有的生活狀態(tài)?管虎的電影流淌著底層小人物的反抗精神,不管在何種境遇、時(shí)代與生活狀態(tài)之下,底層小人物依然有尊嚴(yán)。與其他導(dǎo)演不同,管虎即使在創(chuàng)作歷史題材電影時(shí),也保留其“底層意識(shí)”,諸如《再見,我們的1948》《斗牛》等電影,均以小人物反映大時(shí)代的變遷,這種“大主題,小切點(diǎn)”的創(chuàng)作方法需要導(dǎo)演將人物的情感放在首位,深入認(rèn)識(shí)到人物命運(yùn)與時(shí)代的必然聯(lián)系,并運(yùn)用極高的電影藝術(shù)將人物刻畫得惟妙惟肖、將情感表達(dá)得更為飽滿。
二、管虎電影中非線性敘事體現(xiàn)的主題意識(shí)
“現(xiàn)實(shí)問題”是管虎電影亙古不變的主題,也是管虎電影鮮明個(gè)性與獨(dú)特風(fēng)格的來源。管虎在選擇敘事方式時(shí)皆以此主題意識(shí)為核心[3]。現(xiàn)實(shí)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時(shí)代性、波動(dòng)性特征,從不同層面來看待現(xiàn)實(shí)問題,則會(huì)得出不同的解讀與認(rèn)識(shí),如何將現(xiàn)實(shí)問題這一主題完美地融入到電影中,如何以更為藝術(shù)化的方式呈現(xiàn)現(xiàn)實(shí)問題,管虎選擇了更具有隨意性的非線性敘事方式,例如倒敘、先果后因、現(xiàn)實(shí)與記憶交織等。管虎善于交錯(cuò)使用這些手法,通過電影鏡頭編織龐大、看似毫無章法甚至混亂的敘事網(wǎng)絡(luò),而現(xiàn)實(shí)問題在這一敘事網(wǎng)絡(luò)中穿插、聯(lián)結(jié),逐漸形成情感連續(xù)遞進(jìn)的事件[4]。例如在《頭發(fā)亂了》與《上車,走吧》這兩部電影中,管虎選擇了旁白輔助的敘事手法,采用第一人稱旁白的方式統(tǒng)一整部電影的情感基調(diào),而電影中零碎的、分散的畫面,人物的情感與情緒,人物的狀態(tài)在深情、憂傷的情感主線的串聯(lián)下變得系統(tǒng)、飽滿與立體。在《頭發(fā)亂了》這部電影的開始,管虎運(yùn)用了現(xiàn)實(shí)與記憶交織的敘事方法,回憶中的美好如過眼云煙轉(zhuǎn)瞬即逝,現(xiàn)實(shí)的悲涼與挽傷充斥在人們心中,給人以一種物是人非的悲涼之感。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第一人稱旁白輔助敘事手法具有極強(qiáng)的文學(xué)色彩,在渲染氣氛、烘托情感上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這種敘事手法逐漸被更加多元的敘事手法取代。從管虎電影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其敘事方法的轉(zhuǎn)變從《西施眼》這部電影開始,不再以第一視角表現(xiàn)電影情節(jié),而是從多個(gè)角度進(jìn)行切入,對(duì)于同一個(gè)事物,管虎一般從多個(gè)視角予以呈現(xiàn),這些視角又具有極強(qiáng)的隱性關(guān)聯(lián),使電影達(dá)到了意味深長(zhǎng)的審美效果。不僅如此,電影《西施眼》的敘事方法還包括多敘事線路同步。同一空間下,三個(gè)女子雖素不相識(shí),但她們的煩惱具有共通之處,管虎在揭示三個(gè)女子的境遇時(shí)采用了交-分-交的敘事主線,三個(gè)女子相互補(bǔ)充,在時(shí)間與空間上存在重疊,但是轉(zhuǎn)眼之間三個(gè)人的人生軌道又各自分開,最后三人相聚在戲臺(tái)。或許是宿命,或許是偶然,三個(gè)女子的相聚讓人們懂得了惺惺相惜的價(jià)值。
三、管虎電影中鏡頭語言彰顯的主觀情緒
鏡頭語言是電影創(chuàng)作的重要元素之一,考驗(yàn)著一名電影導(dǎo)演的綜合素質(zhì),用鏡頭語言表現(xiàn)人物的個(gè)性、表達(dá)人物的情感與情緒是每一名導(dǎo)演的“基本功”。我國第六代電影導(dǎo)演有一個(gè)共同的特征,即具有高度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致力于用鏡頭語言反映時(shí)代風(fēng)貌、記錄時(shí)代的變遷與輝煌成就。其中一些導(dǎo)演不愿在電影中融入過多的主觀因素,而是追求一種較為客觀、平和的敘事方式,其要義在于調(diào)動(dòng)觀眾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對(duì)時(shí)代的認(rèn)識(shí)等使公眾構(gòu)建屬于自己的審美空間。而從管虎早期電影來看,其鏡頭語言帶有極為強(qiáng)烈的主觀情緒與情感色彩,他想要用最為真實(shí)的鏡頭語言呈現(xiàn)平靜生活之下的波濤洶涌[5]。例如被稱為“情緒電影”的《頭發(fā)亂了》中包含了大量的搖滾元素,在調(diào)動(dòng)著、激蕩著觀眾的情緒。不僅如此,除了搖滾元素以外這部電影還充滿了晃動(dòng)的手持拍攝鏡頭、MTV式拼貼構(gòu)圖、對(duì)比鮮明的冷暖色調(diào)。在鏡頭下,每一個(gè)人物像是真真切切的存在一般,每一個(gè)場(chǎng)景都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每一個(gè)畫面都體現(xiàn)了主觀的情緒與情感,但這并非管虎情感與情緒的宣泄方式,而是管虎站在人物的視角,思考如何用鏡頭語言更好地表現(xiàn)出人物的特點(diǎn)、人物情感的變化與波動(dòng),因此這部電影中每一個(gè)鏡頭都與電影主題、敘事結(jié)構(gòu)相對(duì)應(yīng),不顯突兀,不浮夸炫技,這便是生活的原貌。
四、管虎電影由張揚(yáng)到平穩(wěn)狀態(tài)的轉(zhuǎn)變
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人們的審美觀念也隨之改變,管虎電影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也發(fā)生了變化。從管虎早期的電影來看,不管是被稱為“情緒電影”的《頭發(fā)亂了》,還是“荒誕恣肆”的《殺生》《廚子戲子痞子》等等,這些電影都體現(xiàn)出管虎張揚(yáng)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比如看似雜亂無章的敘事手法、主觀色彩濃厚的鏡頭語言。但管虎的電影《老炮兒》則采用了清晰流暢的敘事方法,平鋪直敘的敘事讓公眾能夠更好地代入到故事情節(jié)當(dāng)中,也能給觀眾帶來更好的審美與情感體驗(yàn)。這些都表現(xiàn)出管虎電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由非理性轉(zhuǎn)變?yōu)槔硇裕蓮垞P(yáng)轉(zhuǎn)變?yōu)槠椒€(wěn),由恣意宣泄轉(zhuǎn)變?yōu)槔潇o克制。有學(xué)者認(rèn)為,管虎的電影創(chuàng)作游離徘徊在藝術(shù)“叛逆”與生存“脅從”之間。實(shí)則不然,管虎電影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變化,其實(shí)與其長(zhǎng)期所處的胡同環(huán)境改變相關(guān),《老炮兒》與《頭發(fā)亂了》兩部電影故事地點(diǎn)均為胡同,但前者的“胡同”是精心搭就的場(chǎng)景,時(shí)過境遷,胡同已經(jīng)變了模樣,隨之改變了的還有作為資深“胡同人”管虎的電影創(chuàng)作觀念與風(fēng)格。
五、結(jié)束語
電影是生活的藝術(shù),管虎的電影為人們呈現(xiàn)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tài)、時(shí)代與人物命運(yùn)的關(guān)系、以人物反映大時(shí)代的變遷。這種電影創(chuàng)作的“底層意識(shí)”“主體意識(shí)”值得借鑒。隨著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人們對(duì)電影的訴求也隨之改變,實(shí)踐證明,回歸生活、聚焦底層、內(nèi)涵深刻、情感飽滿、立場(chǎng)正確的電影更能獲得人們的支持與喜愛。管虎電影創(chuàng)作注重底層人物的刻畫,善于運(yùn)用個(gè)性化的敘事手法與鏡頭語言,體現(xiàn)出當(dāng)代電影導(dǎo)演的素養(yǎng)與社會(huì)責(zé)任感。
參考文獻(xiàn):
[1]王霄昱.管虎的電影創(chuàng)作歷程探析[J].戲劇之家,2019,(27):81-83.
[2]張芃.作者底色下的風(fēng)格轉(zhuǎn)向——管虎電影導(dǎo)演創(chuàng)作分析[J].藝術(shù)評(píng)鑒,2018,(04):160-161.
[3]任梓茹.宏大敘事的解構(gòu)與個(gè)人情感的內(nèi)斂[D].太原:山西大學(xué),2017.
[4]宋奕晗.管虎電影美學(xué)思想研究[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xué),2014.
[5]李濤.游走在藝術(shù)“叛逆”與生存“脅從”之間——試析管虎電影風(fēng)格[J].藝術(shù)教育,2013,(10):99-100.
作者:郭天毅 單位:清州大學(xué)